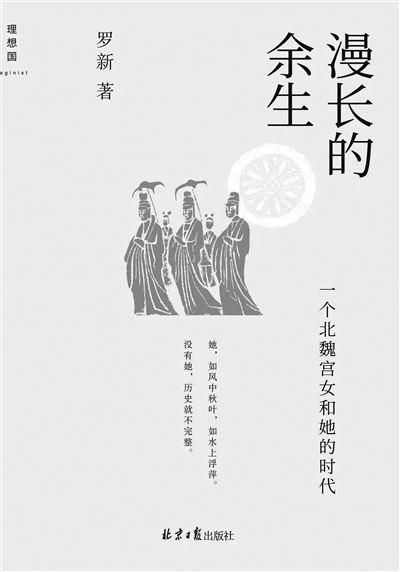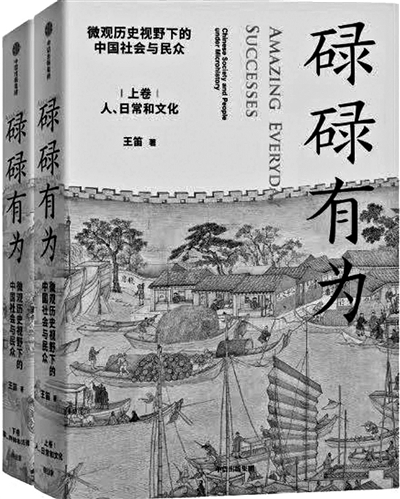●主题:走进历史的潜流——《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新书分享
●时间:2022年11月12日
●嘉宾:王笛 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罗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办:中信出版集团
反思过往,回归普通人、日常的历史
主持人:两位老师今年都有新作出版,且都是以微观史视角切入。请两位聊一聊,为什么对微观视角情有独钟?
王笛:我们过去的历史写作,过于钟情宏大叙事、重视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普通人在历史上几乎是缺席的,以至于鲁迅都说“所谓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家谱”。这种史观对我们的影响,不仅见于历史写作和阅读,也见于公众心态。普通人觉得,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重要,因为我们在历史上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什么贡献,正所谓过去经常说的“碌碌无为”——每天日常周而复始,早起去上班、下班后回家。
而我恰恰觉得这很重要。所以《碌碌有为》这个书名一提出来,我就觉得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大概就是500多位,当然还有各种英雄,加起来在整个人口中也只占非常少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历史写作、历史记载几乎都放在这些人身上。广大的老百姓在历史上起的作用,他们对文明走到今天做的贡献,实际上是被忽略的。
罗老师的新书《漫长的余生》中有一句话——“这一年前后,从政治史来看,萧梁平平淡淡,没发生特大事件,显得没什么可记。这意味着社会安定、政治平稳。”当历史没有什么大事件记载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社会安定、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时候。罗老师接着讲的北魏故事,就有许多大事件发生,充满着腥风血雨。当帝王和英雄想要创造历史时,谁在这些大事件中做出了牺牲?当然是老百姓,但是我们却看不到历史对他们的记载。所以,回归日常、回归普通人的历史就特别重要。
罗新:《碌碌有为》是很“大”的书,刚开始读不知道到底在写什么,跟前面已经熟悉的王老师的作品有点不一样。
以王老师自己的专长,他是详近略远、详今略古,明清以后特别是清代中晚期后的历史写得更多一些。但是这一次,王老师没有按照典型的断代史、王朝史来书写,而是彻底抛弃了那种历史认识、思考和叙述的方式。《碌碌有为》在这个意义上很了不得,它不止一般意义上的通史而已。
我们一般说“通史”,通常就是把王朝史给简略一下,按照时间先后来说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这是编教科书的写法。而王老师是以社会结构各方面,比如物质生活等来描述中国社会,从近代之前、现代之前,一直写到现在。这让我很震惊,显得有很大的野心和掌控力,同时需要有非常细致的、对各方面的思考。
王老师不是写了十几年、二十年、几百年,而是涵盖了至少近一千年的历史,这是非常惊人的。我觉得在体例、写作形式和思考方式上,都是非常有原创力的工作。我想,今后会有人跟着王老师的做法来写新的历史。王老师说自己写的只是社会史,《碌碌有为》其实超越了这些内容。特别是其中有许多对历史的反思,是让我感到很震惊和佩服的方面。
用新的中国史写法
重新格式化我们的文化记忆
罗新
罗新:《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这本书在两个方面让我很震动:
第一,在体例上,好像过去没有这样的书,很有“野心”,希望给出一个新的中国史。
另一方面,王老师讨论这么大时间、空间的历史,可是每一次都落实在很小的东西上,就像他倡导的微观世界研究一样,都落实在细微的具体问题和故事上面,这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
我们抽象地说一些关于过去的事,引用几条材料来证明,不是太难。但是在每个细节上,几乎都能够用非常细微的小故事来支撑,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而王老师做到了。
更奇特的是,他在开拓史料方面,也是值得同行们学习的。过去,近代史开创者们倡导“史学就是史料学”,所以对史料非常讲究,知道哪些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因此形成了非常规范、严格的对于史料的筛选和规定,造成很多人用材料很小心。而在王老师的新书里,他使用材料真的是信手拈来、左右逢源,而更宝贵的是他突破了狭义上的史料,真正拓展到“无所不可以用”——不用说古代的四部典籍,现代文学的小说甚至当代文学的小说作品他也用,比如说《子夜》《白鹿原》等,我觉得是罕见的突破。
在这件事上,只有魄力是不够的。材料用坏了怎么办?但是王老师的控制力可以把材料用得恰到好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也是有巨大的成就。这对历史学来说,至少在中文历史学的写作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创造。王老师到这个年龄还有这么强、这么大的创造力是比较罕见的。王老师这些年出的著作,每本都有新的尝试,在材料上、写作方法和思想上,都有崭新的探索。这些都是很让人佩服的。
我倒不愿意把《碌碌有为》归纳为微观史,我觉得用微观史不足以概括王老师在这方面的努力。也不能简单说是社会生活史,因为书里不止涉及社会生活。我觉得应该称作“新的中国史”,我认为这就是新的中国史的写法。在《碌碌有为》里,看不到我们常见的皇帝们、王公大臣们,看不到重要的战争、政治事件、政治制度,但也是历史,甚至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更重要的历史。
就像王老师所说的,一向以来我们的历史都是别人讲给我们听的,都是皇帝让人写给我们看,让我们记下来,让我们理解的。历史几乎是人类共同的思维基本素材和思维方式,我们怎么理解历史,就怎么理解这个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已有的中国文化,实际是已经被我们过去的历史叙述格式化了,我们现在需要重新格式化。
用不同的方式讲述过去,才有可能想象一个不同的未来
罗新:王老师这种努力,让我想到了一个很棒的例子。有一位去年去世的年轻学者,在英国工作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他与人合作出版了一本书《万物的黎明》,讲到文明发生之前的人类本来存在多种选择,不一定要走今天看到的极端不平等的文明道路。大卫·格雷伯一再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去写历史?就是因为对现实非常不满意,所以要改变和制造一个我们想要的不同的未来。但是从哪里开始呢?答案就是从改变过去开始,要描述、给出一个不同的过去,这样才能想象一个不同的未来。如果我们只是像数千百年来人们规范好的那样理解过去的话,我们是无法想象出一个不同未来的。
所以我觉得王老师的书,可以放在我们当代一个伟大的历史努力中,就是用不同的方式讲述过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想象一个不同的未来。
王笛
王笛:很感谢罗老师对这本书的评论,我真的没有想到罗老师会把《碌碌有为》说得这么重要。实际上我没那么大野心,就是要讲述社会的历史。当然罗老师的反馈让我更有信心,就是继续探索不同的历史角度和历史写作方法,还有历史的思考。实际上,我们过去怎么样,关系到我们怎么创造未来,这个非常重要。
从微观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做出了我们的贡献。我们不渴望做惊天动地的事业,从一定意义来说,我们也不渴望别人做惊天动地的事情。日子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就是我们的幸福。我们作为普通人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
现在大家都有一种焦虑,特别是家长对子女的焦虑。我们自己焦虑没有做出成绩来,没有达到期望的高度,而不甘心于现在所处的地位。我觉得这种焦虑,其实不是我们努力不够,而是社会和一些其他的因素制约了我们。我们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我觉得我们对自己要有这种认可。就像我们可能挣钱不多、社会地位也不高,但是我们每个人生存在这个社会,就有自己的尊严和自己的人格,以及对自己的认可,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替“没有声音”的人发声,讨回一点公道来
主持人:两位老师的新书,不约而同选择了普通人作为作品的主角。《碌碌有为》中,民国时期普通的纺织个体户“杜二嫂”的人生经历贯穿全书;《漫长的余生》中,书写了一位北魏普通宫女被时代裹挟的一生。当初选定两个人物样本时有什么初衷和渊源吗?比如说,都是选择普通的女性作为主角,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罗新:我的这本书不适合跟王老师的书放在一起来说。《漫长的余生》是一本小书,内容很简单,书写了一个普通的故事。但是,我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因为唐代之前的历史,研究者能够使用的材料很少,而且过去的研究又很多。总之想有一点不同,每一代人都在努力做一点不同的东西。我自己从史学观念来说,受到来自西方学者的影响,愿意替“没有声音”的人发声。
当然,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就已经成为史学界的一个共识,只是我们这边接触到这种想法还是比较晚。我有这个想法,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物或故事,找不到切入点。后来就想,干脆写一位墓志里面的人物。我有意识地去寻找这样的女性,因为女性是更加难得见到书写的人物,材料是非常罕见的,稍微丰富一点的史料类型就是墓志。墓志里面女性所占比例要比正史中多得多,生活当中女性没有那么少,只是历史记录,多把这些女性从记录中去掉了。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觉得帝王将相在社会中已经很享受了,他们享受了权力,享受了统治的快乐,享受一切物质上的好东西,这是我们不能改变的。在看得见的人类时间里,无法改变有权有势和占有社会财富的人享受这一切的现实。但是我觉得,我们学历史的人,有责任讨回一点公道来。这个公道是什么呢?就是不能让他们把什么都占了——不能在活着的时候占有一切,死了还占有一切。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1%的人占了人类99%的财富,等到这些人死了,他们更占有百分之百的财富——就是记忆。人类最重要的财富就是记忆,他们又占全了,使得99.9%的人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如果侥幸,我们从古代出土的档案材料里面瞥见这些资料的话,我们不能放过这些机会,我们要把这些人揭示出来,讲讲他们的故事。这就是我做这个事情的动机。但非常残酷的是,材料很少,几百字的墓志,写也写不出什么来。最终讲的故事还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普通人在书中和现实中仍然是很不重要、很不起眼的、没有力量的边缘角色。我想写,可是对历史学家来说,史料几乎就是你所有工作的范围,也不能超脱这个范围,没有材料也不能多说、不能猜测。所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勉强的工作,口号很响亮,理想很高远,可是能做到的很不够,没有办法做到跟王老师的《茶馆》《袍哥》一样,但这是努力的方向。也许未来的材料多一些,未来学者写作能力、研究能力强一些,也许能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古代史资料稀少
更考验挖掘和解读资料的能力
王笛:罗老师太谦虚了,其实我读过《漫长的余生》后,由衷地佩服他。其实我也做过尝试,比如《袍哥》,我能用的资料比罗老师的资料多很多。罗老师的资料是几百字,我有两万多字。这两万多字资料写成书,受到很大的关注。但是也有人批评,两万多字一下变成二十多万字,有“注水”的感觉。不管这种评价对不对,不管是否我认可这种评价,至少有一些读者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罗老师《漫长的余生》出版后,我没有看到任何人这样说。
我在想,为什么罗老师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就是写作的技巧,这个技巧有时候说不出来,需要自己仔细去揣摩。但是我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说,由于资料少,要以宫女王钟儿为主角写一本书是非常困难的,罗老师想了各种办法,使王钟儿在整本书中存在。比如说,罗老师写到“张谠何时入朝不见于史,估计也在几个月之内”,接着马上说“张谠到平城拜谒北魏献文帝时,王钟儿已经在平城宫里了”。实际王钟儿和这件事情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罗老师用语言来回穿梭,不断提醒我们王钟儿的存在,我觉得这就是写作的技巧。在整本书中罗老师都是这样做的,成功地让我们的读者一直在潜意识中感觉到王钟儿的存在,这个是需要相当技巧的。
还有就是编辑资料的功底,我要好好向罗老师学习。刚才罗老师讲,比起我们研究近现代史,研究古代史本来资料就少,而且很多资料是大家都已经用过的。但是怎么个用法,我觉得需要挖掘和解读资料的能力。我在《碌碌有为》这本书中,也是通过一个小人物来切入,这个人物样本来自1944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杨树因的本科毕业论文《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杨树因在石羊场考察了一户手工业家庭,主事的是一位40多岁的女性——杜二嫂。这和王钟儿有一点接近。我觉得,一位女性在乡村手工业家庭中扮演主要的角色,这是我们过去不重视的。她四十多岁,通过经营手工纺织业,使一个比较底层的家庭,步入到有一定财富。我觉得这份调查报告不仅仅涉及她的个人、家庭生活,还涉及很多方面,比如宗教、家庭关系,以及石羊场的人口结构、经济状况、自然环境等一系列的问题,甚至还要涉及她的穿着、衣食住行、住房情况。虽然这份调查报告集中在一个家庭,但相对来说,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家庭各方面的情况,而这个家庭,实际上代表着中国农村千千万万的人口。他们个人的故事可能不同,但是很多方面,包括衣食住行、生产、生活、家庭、家族等,在相当程度上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决定让杜二嫂的家庭成为两卷书的切入点,以她的故事进行展开。
但是,我读了罗老师的书以后就在反思,杜二嫂的故事相对《碌碌有为》整本书的字数来说,占比是比较小的。而王钟儿的墓志铭只有差不多几百字,《漫长的余生》有十几万字,但是不感觉王钟儿的缺席。我自己感觉,还是可以以罗老师的这种方法,随时把杜二嫂“请出来”。如果早一点读罗老师的这本书,可能就会早一点弥补《碌碌有为》的这个缺陷。
只有平等描述过去的人
才有可能平等看待自己身边的人
主持人:两位老师刚刚都有提到,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有一些边缘性的人物或群体,比如王老师在《碌碌有为》其中一个章节,特别描写了社会中的一些边缘群体,比如妓女、乞丐、镖师和传统的手艺人;罗老师写到的宫女也是不太被提及的边缘角色。想问一下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而言,这些比普通百姓还要更加边缘化的小人物承载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
罗新:我们也不必去夸张边缘人对历史做了更大的贡献、有更大的意义,当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要从某一个具体的方面讨论历史,比如说科学的发展,当然是科学家们做了更大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位置上,都是有不同的被描述的必要性。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关注普通人呢?其实从一般意义来说,普通人是不被关注的。日常生活当中,今天有各种公益组织、慈善机构来关心这些人。
我们人类社会之所以是人类社会,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会关注所有的人。电影里说,我们是人,我们会埋葬我们的死者,而不是像动物一样死了就不管它。死了的人,对我们生活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可是我们会很认真对待那些人,就是所有人,只要是人。我觉得树立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很重要。
而要树立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很大程度上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在道德意义上提倡这一点好像不是很难,但是在观念深处、内心深处、文化深处接受这一点、理解这一点,使之成为我们价值中的一部分,并不容易。我们就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过去的人,那些存在过的人,在历史当中留下姓名以及没有留下姓名的人。因为太多人没有留下姓名,只是数据。我们说汉代有五六千万人,可是留下名字的有几个?即使是留下名字的人,也被分成三六九等。有些人是第一等,有些人是第九等,还有一些普通人连名字都没有,在九等之下。我们只有平等看待、描述过去的人,才有可能平等看待自己身边的人,以及要求别人平等地看我们。
当然,很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被别人平等对待,别人没有认为我们值得尊重。我们对抗、我们批判、我们否定这个现实唯一的方式就是平等对待死者,平等对待我们的先人和过去的人,关心那些人就是为了未来和现在。这是一个价值意义上的说法,还有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怎么理解历史,怎么理解现实。
我不认为同行都能够理解或者接受这一点,因为历史学是一个专业工作,有些工作显得非常专业,好像不经受很多年的训练和努力,要读懂他做什么都比较难。越是做比较专门的工作,比如说做古典的经学研究、古老的文献研究、文字研究等等,都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做技术上的培训。这些工作本身不是史学,但这是史学的基础和前提,要花很大的精力。但是说实话,我接触过很多做这样工作的人,他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却很少反思自己的历史观念。你跟他说历史观念变化的必要,他不大知道你说什么,也不太在乎你说什么,他们更在乎自己在技术方面的训练,认为那些更重要,好不容易训练到那一步。我也觉得技术很重要,但是历史观念才是真正的目标,才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