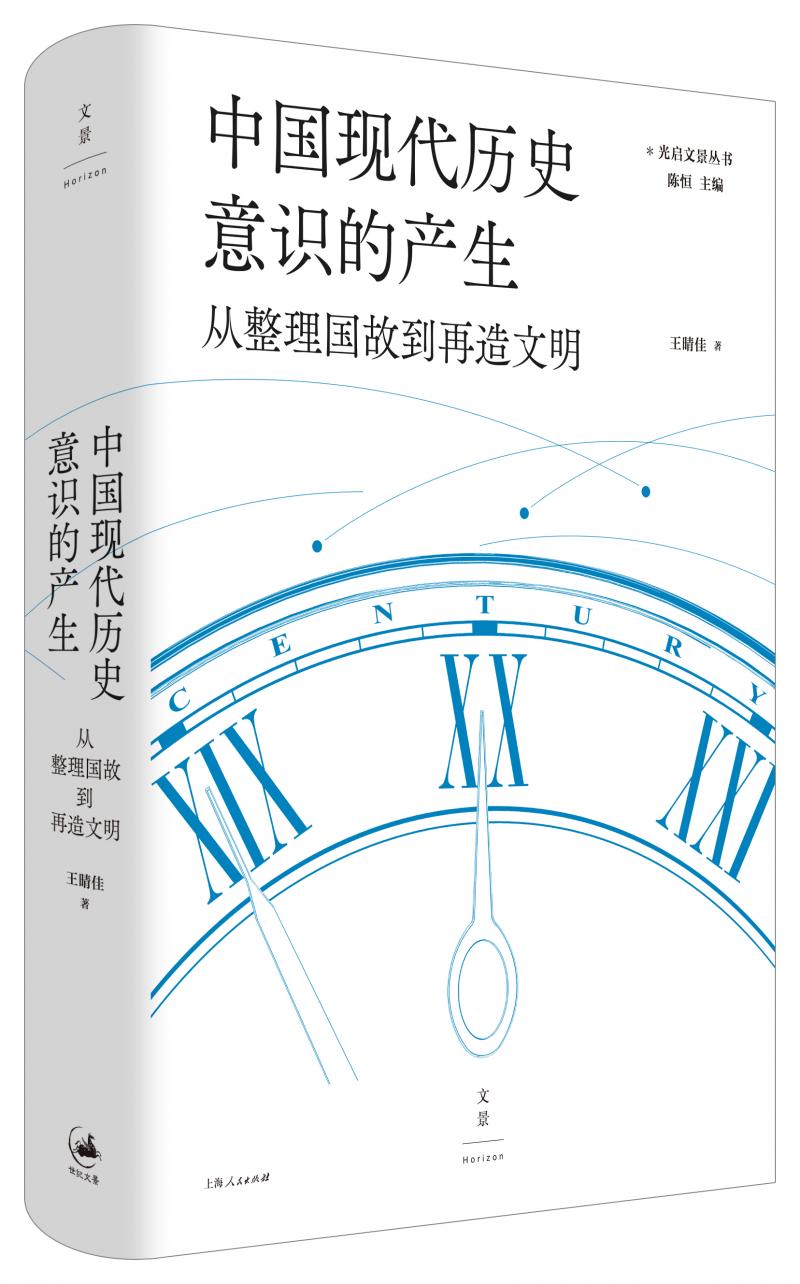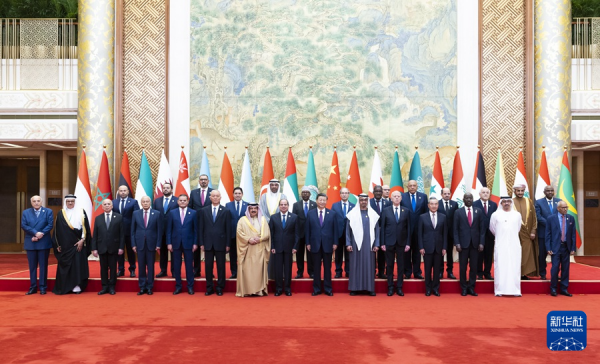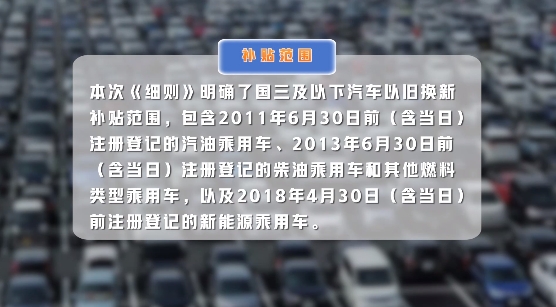1930 年代后期,钱穆、张荫麟写作中国通史的时候,正是民族危难、生灵涂炭的全面抗战时期。全民抗战的结果,使得民国史学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折。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注重史料考证和扩充的学者,渐渐无法继续他们的研究,如那时轰轰烈烈的殷墟考古发掘,到了1937 年卢沟桥事变时,也只得停止。胡适、傅斯年他们从学术的象牙塔里走了出来,编辑《独立评论》,为抗战出谋献策。要想继续学术研究,已经没有以前的环境和心境了。张荫麟对那时的情景有一段很好的描述:
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如其不致停顿。“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英贤,固尚有之;然而他们生产的效率和发表的机会不得不大受限制了。
事实上,能够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其治学方法也不得不有所改变。如擅长以多种语文证史的陈寅恪,在从北京撤退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后,显然也由于资料的限制,开始写作通史性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其所用材料,大多取自常见的正史。因此,像张荫麟那样从考证转到通史的写作,应该说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个趋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专注史料的历史研究方法,与当时民族危机的局势,似乎也相隔太远。当时人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从历史中寻求中华民族生存的力量与精神,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中国历史的长短,或某些史书的真伪。于是,自“古史辨”以来所掀起的历史研究法的热潮,逐渐冷了下来。原来站在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派”对立面的钱穆、柳诒徵等人,以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坚定信仰,而开始有了壮大的声势。他们一个写了轰动一时的《国史大纲》,另一个出版了《国史要义》。他们在“国将不国”的年代使用“国史”一词,充分表现了他们力图重振民族国家史学的用心。
1943 年,钱穆借悼念张荫麟之际,写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一文,间接质疑胡适等人的“新史学”,而提出自己的“新史学”。在钱穆眼里,所谓“新史学”,无非是司马迁的“通天人之故,明古今之变,此即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故曰,述往事,思来者。惟昔人虽有此意,而未尝以今世语道达之,今则姑以名号相假借,曰此新史学也”。钱穆对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批评,显得比较委婉。他不以对方为攻击对象,而是以陈述的形式,表达自己心目中的“新史学”,但他的批评之意,明眼人可以一目了然。
钱穆很早便对胡适、傅斯年等人专注史实考证、发掘有所不满,尽管他早年也是一位考证史家。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便“填补了顾颉刚1926 年开始研究的新历史中的空白”,因此得到顾的赞赏,受邀到北大讲课。但是,钱穆对顾的“疑古”思想却不愿“同流合污”,而是借开设“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机会,批评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和疑古思想。但不久傅斯年的史语所殷墟发掘成功,使得当时的人对史料的考证与扩充产生了更大的兴趣。钱穆有感于这种状况,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课程,谈论中国历史的“独特的规律和模式”,力图纠正当时人的历史观念。
1930 年代,对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史学实践不满的还不只是钱穆、柳诒徵等思想传统的人物,还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当时掀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因此,可以说胡、傅是受到了两面夹攻,无法再占据主导的地位。民国的史学界,因而形成三足鼎立的状况。如果用不精确的政治术语来表达的话,胡适、傅斯年代表的是自由主义的史学流派;钱穆、柳诒徵代表的是传统主义的流派;而郭沫若等社会史论战的参加者代表的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后两派的历史观念自然十分不同,“但对历史学家来说,无论他们的观点如何,首要的任务就是对中国历史的规律作出一个新的叙述”。
抗战爆发在民族危难之际,如何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暂时的失利,从而相信中华民族不朽的生命力,变得更加必要。中国通史的写作,因此成为一时之需。钱穆对如何展示历史的连续性,用历史来激励民众,十分清楚。他说:
当知甲午一役,中国虽败,日本虽胜,然不得谓其事已属过去。甲午一役之胜败,仅为中日两邦开始斗争之第一幕,其事必有持续,而于持续中又必有变动,故绝不当竟目日本为胜者,中国为败者。……故凡一历史事件,莫不有其相当之持续性,而其间复有积极消极之分。积极者,乃此历史大流之主潮。消极者,乃此历史大流之漩洑,更有泡沫浪花,虽本历史大流之一相,而实无当于大体。
显然,他希望读者能把中国抗战初期的失利,视为“消极的”历史事件,不会对中国历史的“大流”产生根本的影响。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写作《国史大纲》的用心了。
钱穆的《国史大纲》,前面有一篇长序,其中既有他对中国史学在近代变化的追述,又有他对历史的功用的解释。他将中国近代的史学,分为三派,“传统”、“革新”和“科学”,对这三派都做了批评。但从其行文来看,他对“科学派”(胡适)的批评,远甚于对“传统派”。譬如,他说“传统”与“科学”两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它们的毛病是“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但是,“传统派”仍有其好处:“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而“科学派”则罪过很大:
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无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钱对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史学,批评得简直一无是处。而他本人,似乎有志于改良章太炎的“革新派”史学,重振国史。他认为,“革新派”的史学,其主要缺点是“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但在使史学与现实相结合,掌握历史的连续性,对民族文化的评价等方面,则有其功绩。因此,新的国史应该扬其长,避其短,所谓“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具体说来,新的国史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由此可见,钱穆之写作《国史大纲》,力求以一种新态度出发,站在一个新的高度通览中国的“全史”,即所谓“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但是,要做如此的综合,并不容易。张荫麟没能做到,钱穆就能做到?
事实上,钱穆之写作,既带有抗战时期的民族义愤,又掺杂他对胡适等人“科学史学”的不满,根本无法做到“客观求证”,展示“国史真态”。他对中国历史自始至终有一种主观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在他一生中,都没有丝毫改变。
在他眼里,所谓的“国史真态”或“动态”,就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和活力。而展现这种活力,正是他写作《国史大纲》的动机。他写道:
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趋,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眵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围之釆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可见,钱穆已经对国史有一主观的认识,即“管弦竞奏,歌声洋溢”的别有洞天,而且具有独特的精神。这一所谓“独特的精神”,就是与西方相比而成立的。钱穆认为,西方历史看起来活力四射、跌宕起伏,而中国历史看起来一潭死水,都是由于其不同的内部精神所决定的。
然中国史非无进展,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精采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这些话,与其说是分析、解释,毋宁说是描述、想象。钱穆的《国史大纲》的主观色彩,比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还要浓厚。但是,在当时《国史大纲》的成功,恰恰靠的是钱穆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坚强信念。虽然钱穆个子瘦小、操一口吴侬软语,但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却能沉潜于历史,从中发掘出当时的人急需的精神食粮和文化信念,殊为不易。钱穆的《国史大纲》,只有从民族史学的角度来评估,才显其价值。余英时在一篇纪念钱穆的文章中,用“一生为故国招魂”为题,实在非常恰当。余英时在文章中,提到这种为民族搜索灵魂(钱穆改用“中国历史精神”)的做法,在近代德国史学中也有前例。
留学德国、对德意志历史主义有研究的台湾学者胡昌智在其《历史知识与社会变迁》一书中,也以《国史大纲》为例,来分析钱穆历史观念与德国近代史学的暗合之处。这一暗合,主要表现在钱穆对中国历史精神的强调。在《国史大纲》中,钱穆花了不少篇幅,讨论学术思想的变迁与社会演变的关系。虽然他没有界定“精神”这一概念,但像黑格尔一样,钱穆使用“精神”一词,是建立在一种先验的基础上的。饶有趣味的是,钱穆的“精神”,正是建立在区别于西方的基础上的。易言之,他之所以强调中国历史的精神,恰恰是为了突出中国历史的独特性。
在钱穆眼里,学术思想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主要原因,而其演变的方向,是走向一个“合理的政府”。具体说来,就是中国的统一和建立一个有权力和效率的中央政府。但从钱穆的儒家思想出发,这一政府要真正做到合理,又必须让平民充分参政,使政府与民众紧密结合,以民为主。因此,钱穆的历史观念,既有政治的一面,又有道德的一面。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对王朝的统一,一般都持肯定的态度,特别是所谓“平民的统一政府”。如对秦汉的统一,他这样评价:
经过战国二百四五十年的斗争,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灭六国,而中国史遂开始有大规模的统一政府出现。汉高称帝,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的统一政府。武帝以后,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社会文治思想的统一政府。中国民族的历史,正在不断进步的路程上。
这里有一些问题,汉朝是否就代表平民,尚难确定,而将汉武帝视为代表“平民社会文治思想”,只能说明钱穆想对那位“独尊儒术”的皇帝,多加几句赞语而已。
汉朝的衰亡,自然使钱穆十分伤感,特别是因为汉朝灭亡以后,儒家学说也随之衰落,要过好几百年以后才会重新兴起。他的分析是:
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需依赖于某一种理论之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于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否则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暗根本无存在,必趋消失。
钱穆用学术思想、道德理念来解释历史变化,这里表现得十分明白。
无独有偶,钱穆那种以儒家学说解释历史的做法,在柳诒徵的《国史要义》中,也有详尽的论述。与钱穆《国史大纲》不同的是,柳诒徵的《国史要义》,主要是一部中国史学史的著作,不是中国通史,但其指导思想和历史观念,则大同小异。柳著虽然迟至1948 年才出版,但作为一部讲稿,柳在1942 年在为中央大学的学生讲授“中国史学原理”时已经写就。因此,柳著与钱著可说是同一时代的作品。
比钱穆年长十五岁的柳诒徵,早年曾有机会赴日本考察,得以见到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为其体裁所吸引,改编而作《历代史略》,很早便尝试用章节体写作中国通史。因此,在采用新的体裁写作中国通史方面,柳诒徵是一位先驱。以后他又作《中国文化史》(1925 年),一方面用进化论的观念贯通中国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力图展示中国历史有异于西方的地方,注重“民族全体之精神”。因此,钱穆《国史大纲》中的观点,如历史的整体性、中国历史的独特性等,在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中,已呈端倪。
在对待胡适等人的“疑古”史学,柳诒徵的态度,也自然与钱穆十分相似。在东南大学任教时,他在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批评“新文化运动”。在顾颉刚的“古史辨”讨论中,他也参与其内,与顾争辩。他指出,科学史学家用西方的方法治中国史,固然有成绩,“但是有一种毛病,以为中国古代的许多书,多半是伪造的,甚至相传有名的人物,可以说没有这个人,都是后来的人附会造作的。此种风气一开,就相率以疑古辨伪,算是讲史学的唯一法门,美其名曰求真”。他对“疑古”史学的批评,并不是因为他有更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古书的真实,而是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出发,认为古人、古事不容怀疑。
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坚强信念,在《国史要义》中,多有表现。比如他所谓“由天下之观念,而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之观念。又有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之观念”。既强调了天下之一统,又强调这一统一的道德性,与钱穆的理想,如出一辙。对于史学的功用,柳诒徵的态度是,历史必须促进道德,仅仅能“疏通知远、属词比事”还远远不够,还要比较“流失”,得其长而祛其失,则治史而能明德。“故古人之治史,非以为著作也,以益其身之德也。”而将这一道德放大,那就是正义,由此,柳诒徵重提中国传统史学的“正统论”,认为其基础在于正义。所谓正义,指的是:
疆域之正,民族之正,道义之正。……疆域不正则耻,民族不正则耻。惟此二耻之所由来,则自柄政者以至中流士夫、全体民众,无不与有责焉。吾史之不甘为偏隅,不甘为奴虏,不甘为附庸,非追往也,以诏后也。
在民族危难之时,以历史为救国之法,柳诒徵的用心,可谓良苦。
在战争的年代,如何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的危机,也有不同的路径。钱穆、柳诒徵等信仰中国文化的学者走的是回归传统的路子,而受到西方学术训练的雷海宗、林同济等人则从西方的哲学思想中寻找激励人心的力量,用以解释中国与世界历史,帮助人们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们用的是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文化形态学说,把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化比拟为生物的生长繁殖和衰老。因此,他们的史学,也是用科学方法探讨史学的一种。
有所不同的是,雷海宗、林同济根据时代的需要,对文化形态学说在性质上做了某些改造。文化形态学说的首倡者斯宾格勒在1918 年发表《西方的没落》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正面临深刻危机。他将历史的演变比喻为生物的生长,表达了一种悲观主义的论调,认为所有的文明,不管在某一时代如何凯歌高奏,到最后都难逃衰亡的命运。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基本上承袭了斯宾格勒的理论,但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命运,寄予了一些希望。但是,雷海宗、林同济在引入文化形态学说时,又夹杂了尼采的学说,推崇权力意志、赞美武力,力图在当时抗战的严峻时刻,给国人一点精神的力量。
因此,林同济、雷海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持的是一种批评的态度,虽然他们的目的与钱穆等人一样,是为了激励民众起来奋发抗战。请看林同济的《力》一文:
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已是人类历史上对“力”的一个字,最缺乏理解,也最不愿理解的民族了。这朵充满了希腊之火之花,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中,竟已成为一个残暴贪婪的总称。“力”字与“暴”字,无端地打成一片。于是有力必暴,凡暴皆力。……
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力即是生,生即是力。天地间没有“无力”之生;无力便是死。
因此,他们谈论“意志”、人的本能(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讨论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强调“英雄崇拜”的必要。目的都是为了激励人心,应对艰苦的抗战。
而他们最有效的武器,莫过于提出一种新的历史解说,来帮助人们认清中国面临的局势。这一历史解说,就是所谓的“形态史观”或“历史形态学”(Horphology of History)。对于这一史观的阐述,林同济说:“雷先生较偏于‘例证’的发凡,我较偏于‘统相’的摄绎。”雷海宗、林同济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分析解释文明发展的各个时期,然后将当时的中国与世界都定位在“战国时代”,认为是文明发展和能否再生的一个关键阶段。由此他们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又被称之为“战国策派”。
他们提出这一理论,有一个方法论的目的,意图超越胡适的考证派史学与当时已经形成气候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林同济写道:
关于方法论——一个根本又根本的问题——我以为中国学术界到了今天应当设法在五四以来二十年间所承自欧西的“经验事实”与“辩证革命”的两派圈套外,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
从理论上来看,他们的“形态史观”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历史发展的宿命论,用一种既定的模式,来概括历史演变的路程。比如林同济就写道:“在过去历史上,凡是自成体系的文化,只须有机会充分发展而不受外力中途摧残的,都经过了三个大阶段:(一)封建阶段,(二)列国阶段,(三)大一统帝国阶段。”而雷海宗则谈得更为具体:“在一个文化的发展上,第一个阶段就是封建时代,前后约六百年。”“历史的第二个阶段。可称为贵族国家时代,前后约三百年,是一个以贵族为中心的列国并立时代。”“文化的第三个阶段,是帝国主义时代,前后约二百五十年。”“文化的第四个阶段是大一统时代,前后约三百年。”“第五个文化阶段,最后的时代,是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时间不定,可长可短。这是三百年大一统时代后无从幸免的一个结局。”雷海宗不仅将这些阶段的更替,视为必然,所谓“无从幸免”,还规定了各个阶段所须经历的时间。林同济所谓雷海宗注重“例证的发凡”,想来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学说的第二个特点是,提出历史循环演化的可能性。这是他们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的改造。这一改造,显然是与当时中国的情势有关的,也是许多借鉴西方历史理论的学者在解释中国历史所必须处理的问题。因为那些根据西方历史得出的理论,往往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历史。于是做一点削足适履的工作,就成为必须。但是,一旦认为历史的演化有可能循环,便与他们上面所强调的文明发展的阶段论、“宿命论”有所矛盾。因此他们在论述时,显得有点小心翼翼,没有像赞颂“力”和“权力意志”那样意气轩昂。
雷海宗写道:“中国文化的第二周在人类史上的确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没有其他的文化,我们能确切地说它曾有过第二周返老还童的生命。”在他对中国历史的第二周,也即从魏晋南北朝至中华民国的时期做评估时,也没有像分析第一周历史(殷商到东汉)时那样充满信心。比如他谈到盛唐时代时说,那个“伟大时代前后不到二百年,安史之乱以后不只政治的强盛时期已成过去,连文化方面的发展也渐微弱”。接下来的宋朝,只是“一个整理清算的时代”,而宋代理学的兴起,在他眼里,只是“一种调换招牌的运动”,“其结果的价值难以断定”。明代虽然政治上一度强盛,但很快坠入“一片黑暗,只有一线光明,就是汉族闽粤的向外发展,证明四千年来唯一雄立东亚的民族尚未真正地走到绝境”。而“晚明盛清是政治文化完全凝结的时代”,乾嘉的考证学,不是“一种创造的运动;任何创造似乎已不是此期的人所能办到”。这里的原因是,雷海宗认为这历史的第二周,必然走向衰落。西方强权的冲击,起的是一种近似摧枯拉朽的作用。
既然那中国文明的第二周没有多少创造力,那么在这第二周结束以后,能否有成功的第三周,便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雷海宗在写作时,用的都是疑问句:
中国文化的第二周显然已快到了结束的时候。但到底如何结束,结束的方式如何,何时结束,现在还很难说。在较远的将来,我们是否还有一个第三周的希望?谁敢大胆的肯定或否定?
对于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即有这种历史重复、循环的现象,雷海宗是既喜还忧。他用了一个比方,那就是“喜的是年迈的双亲仍然健在,惧的是脆弱的椿萱不知何时会忽然折断”。在已经有了第二周之后,能否再创佳绩,把中国文化推向第三周,是雷海宗对当时国人的期望。
为什么说是期望,是因为在雷海宗和林同济的眼里,中国文化的“士大夫”气非常之重。林同济歌颂“力”,雷海宗的书以《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为题(其实里面的内容并不完全切题),他们又把那时的年代视为“战国时代”,都是为了发掘中国文化中的阳刚、尚武的因素,在那个战争年代加以发扬光大,抵抗日本的侵略。
正如上面所说,虽然林同济、雷海宗与钱穆、柳诒徵一样,想用历史来激励民众抗日,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钱穆等人所推崇的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是论证中国文化不会绝灭的根据。而对林同济、雷海宗来说,战争的取胜靠的恰恰不是这种人文精神,而是与之相反的、准备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可惜在他们眼里,中国文化缺乏这种精神,雷海宗论“无兵的文化”,林同济论“士大夫”和“大夫士”的区别,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他们对“力”的歌颂,对战争残酷性的强调和对“战国时代”性质的分析,也是为了激励民众,指出除了“战”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日本这次来侵,不但被侵略的国家(中国)生死在此一举,既是侵略者(日本)的命运也孤注在这一掷中!此所以日本对我们更非全部歼灭不可,而我们的对策,舍‘抗战到底’再没有第二途。”用“战国策派”来为他们的理论命名,实在非常恰当。
傅斯年在抗战开始时曾激动地问道:“书生何以报国?”上面我们所谈的这两派,就是书生报国的例子。他们的学说对实际的抗战到底有多少贡献,无法评估,但书生意气,溢于言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不断科学化的过程。抗战的爆发与深入,使得两者之间产生激烈的互动,甚至对抗。上面的两个例子,正好是这一复杂关系之极端表现。我们便以此来结束我们对民国时代史学的讨论。在这以后,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将是另外一番面貌。
(原为《论20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第六节“科学、民族史学的消长”,标题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