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郊发生了一起造成三人死亡的交通事故,现场有一辆电动三轮车、一辆摩托车、一辆自行车,三名死者没有任何交集,且没有第四个参与人。难道是三辆车相撞导致三人死亡?三名死者又该分别对应哪辆车?自行车到底是推行还是骑行?事故到底是谁的责任?案件遇到瓶颈。
“清华大学博士后交警”张雷来到现场直接找到疑点“自行车的位置距离中心现场太近了”,他对三辆交通工具和三名死者又进行了复勘,通过组织开展多轮的检验、分析和模拟试验,推断出最终结论:这实际上是一起双方事故,自行车是搭放在三轮车上的,并没有参与到道路行驶过程中。

根据这一判断,属地交通支队沿着张雷给出的方向,开展扩线调查,为明确事故责任方奠定了基础。
现任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事故处理支队交通事故鉴定中队警务技术三级主任的张雷,日常工作就是根据现场遗留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来确定事故的发生过程,进而查明事故原因,还原案件真相,为后期的责任认定和经济赔偿提供依据,是交警中的“刑警”。
拒绝“诱惑”克服“阻力” 清华大学博士后当交警
2008年,北京迎来了举世瞩目的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北京市公安局也乘势而为,面向社会全面引进高学历人才,而张雷就是这批人才中的一员。
那时,作为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博士后,张雷曾经与北京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有过多次事故鉴定和科研方面的合作,他发现,一线的鲜活案例、丰富数据是院校和书本上所没有的。出站前,张雷就下定决心,“到基层去,在实践中形成经验、发现问题、总结规律、研发技术,从而反哺给社会,减少事故的发生。”
回忆起出站时的那段日子,张雷面对各种“诱惑”和“阻力”,有高校邀请他当导师、建实验室,有汽车企业聘请他做高管、拿高薪,他都一一婉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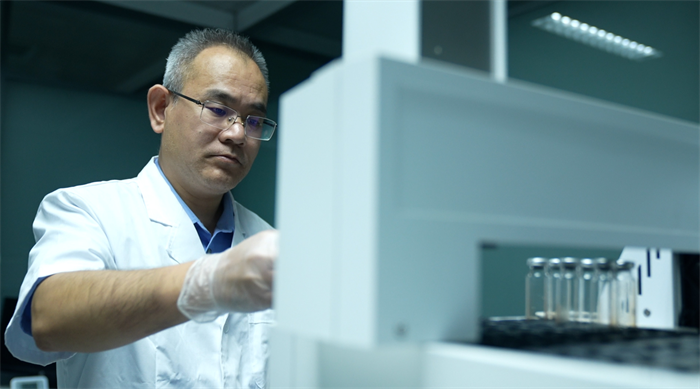
“当时我始终关注北京市公安局在交通管理工作方面的发展,了解到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成立了当时全国唯一一家省级公安交通中心,我想去那里。”张雷说,当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才引进的工作人员找到他时,自己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张雷说,对于自己这一选择,包括妻子在内很多人并不理解,觉得搞交通事故鉴定“庙小”。不仅夫妻二人激烈讨论过好几次,张雷的导师也觉得他是做科研的好苗子,应该去国家重点实验室搞研究,才算得上是“人尽其才”。面对各种质疑,张雷还是觉得“这个领域大有可为”。
当得知张雷这个清华博士后选择成为交警之后,曾有人为他惋惜,而张雷却说:“我自信满满而去,才发现自己所学的知识,根本不够用,还要学。”
交通事故现场情况复杂,事故鉴定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宽泛,包括法律、医学、理化、刑事技术等。同时,由于交通事故产生的机理与运动相关,还需要掌握力学、图像学、统计学,甚至还包括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数据分析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为尽快适应岗位,张雷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新知识,甚至冒出过重回学校攻读相关专业的念头,奈何时间不允许,“只能在实践中通过搞案子恶补,哪不行,就抓紧学。”
张雷在不断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中,养成了用哲学思维去全局性、系统性、动态性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创新形成了多学科、多领域交叉融合的综合调查取证模式,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17年里 出具3万余份各类鉴定文书无一错漏
2009年,京郊发生了一起造成人员死伤的交通事故。前期,属地交通大队在发生事故的电动车驾驶座上,提取到了一处血痕,经鉴定属于死者,据此推测事故发生时,驾驶人可能就是这位死者,但又无法排除昏迷伤者驾驶的可能。工作推进不下去,属地交通大队报请事故处理支队介入,张雷被指派前去开展复勘工作。
那时的张雷加入交管队伍不足一年,主办民警对他的能力有所怀疑。张雷经过细致的分析,判定驾驶人是那位正处于昏迷状态的伤者。面对主办民警各种疑问,这位“初来乍到”的新警从容地解释道:“交通事故现场是运动的,血痕的形态也要充分考虑运动过程中血液和车辆的相对速度、运动方式。”张雷用现场重现和模拟实验两种方法进行验证,科学地解答了那处血痕的成因,又根据死者的落地位置、人体损伤特征、地面痕迹、车体痕迹、微量物证以及人与车辆的相对运动,反推死者生前并不在驾驶位。那一天,张雷的解释和推理通俗有力,列举的证据和鉴定结果客观确凿。随着伤者从昏迷中苏醒,其叙述也印证了张雷的判断。
此后,张雷的名气在北京公安交管部门甚至全国公安交管系统迅速传开,他凭借自己广博的知识储备、系统的思维能力和科学的分析方法,让一起起原本扑朔迷离的事故最终清晰明了。
17年里,他承担过30余例全国重特大交通事故的调查和认定工作,参与调查3000余起全市各类交通事故,参与1800余起全国重大疑难交通事故鉴定,出具3万余份各类鉴定文书更是无一错漏。
而除了交警职业身份之外,张雷还担任中国合格评定认可委员会技术专家,科技部和公安部科技兴警智库专家,公安部部级专家人才库首批入选专家,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能力验证技术专家。
“知识和技术只掌握在自己手里怎么能行,要将它们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科技装备,才能解决问题、提升效能,从而惠及更多方面、更多人。”这是张雷始终坚持的观点,更是他开展创新研发的动力所在。

拆掉技术操作“门槛” 现场拍照后系统可自动生成所需的勘验要素
在一起发生在外省市的特大交通事故中,张雷作为国务院特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专家,承担了该起事故复勘的主要工作。面对大面积、不规则、相互叠加作用、无法有效剥离的痕迹,有什么方式可以将这些痕迹分离出来?曾经在国外学术期刊上了解过三维扫描技术的张雷,一下子就想到可以把三维扫描技术应用于交通事故现场勘查,他将三维扫描工具、拍摄设备进行了实战优化,将现有的勘查鉴定系统进行了适用性升级,创新构建了能应用于交通事故痕迹鉴定的系统。
由于采取整体、密集的方式收集勘验对象的特征点,检验的准确性大大提高,加上使用的是激光技术,保持了所有痕迹的完整性,实现了交通事故痕迹物证信息采集、比对和判定的全程无接触、无破坏和数字化,有效解决了传统检验方法难以实现的复杂痕迹的分析和场景复现等问题。这一创新技术在该起事故调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查清事实、确定原因、认定责任提供了核心证据。
“但考虑到系统操作门槛高、配套系统数据存储要求高,对于大部分交通事故和基层单位来说并不适合,这项技术后来只在重特大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工作中得以应用。”他说,“好的装备,要能解决普遍性问题,得让基层民警上手就能用,而且实践效果得好、应用范围得广。”循着这样的思路,张雷很快寻找到了新的研发方向。
经过大量实践和深入思考,张雷认为现场勘查最为耗时的地方,在于使用传统工具对痕迹的大小、位置进行记录,绘制现场图这些环节上。
张雷从这一点入手,借鉴测绘摄影技术,将传统直线型标尺改良为平行四边形的标尺,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只需把标尺摆在痕迹附近,用相机进行拍摄,将照片上传到其研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置系统”内,系统可自动生成所需的勘验要素,从而有效缩减现场勘查的时间。
一次,北京环路上发生了一起情况复杂的交通事故,当时正值晚高峰,交通压力不言而喻。张雷带队运用这项发明,将现场勘查时间压缩到12分钟即全部、高效完成。他说,“在以前,这样的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最快也得用时1个小时,很容易造成大范围拥堵,间接造成数以百万计的经济损失。”
这项发明后来在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工作中被广泛应用,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创新装备一个接着一个,张雷始终不满足。在他看来,新装备要跟得上时代的发展,满足新形势、新要求。

参与完成15项科研项目 有效解决我国交通事故处理重大关键性技术难题
在一起危险驾驶案中,现场公共图像显示,撞车瞬间的车速很快,可它究竟有多快,成为了司法审理过程中的一项需要着重考量的因素。但由于事故现场痕迹过于复杂凌乱,使用传统的痕迹计算方式无法对车速进行测算,张雷决定利用视频图像对车速进行鉴定。综合视频显示时间、画面参照物、帧数、运动轨迹等一系列因素,他算出车辆肇事时的车速在110.6至121.7公里/小时之间,远超70公里的限速,为案件定罪量刑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此案的基础上,为了适应道路公共图像设备和车载录像设备广泛应用的新形势,张雷及时将上述鉴定方法进行固化,主持制定了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基于视频图像的车辆行驶速度技术鉴定》并于2014年正式颁布实施,成为全国交通事故车速鉴定的主要手段。

从警17年,张雷准确把握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处理国际前沿发展趋势和我国实际需求,开展系统性的警务装备、警务技术创新,不仅先后主持和参与制定了包括《道路交通拥堵经济损失评估指南》《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箱通用配置要求》《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鉴定机构建设规范》《道路交通事故涉案者交通行为方式鉴定规范》在内的涵盖公共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驾驶、事故鉴定领域的18项行业标准,让通过这些鉴定方法形成的结论成为司法过程中的有效依据,让相关领域企业更加注重产品安全性能的提升,从而保障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特别是,作为科技部和公安部科技兴警智库专家,他率先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生产规范和准入制度等领域开展系统性研究,承担并完成了多项公安部相关科研课题,参与了公安部《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研究制定工作,推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交通事故鉴定效能提升和行业规范化发展。
参加工作以来,张雷累计参与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5项,有效解决了我国交通事故处理的一些重大关键性技术难题,为规范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办案和司法鉴定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浩雄
编辑/胡克青
校对/葛冬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