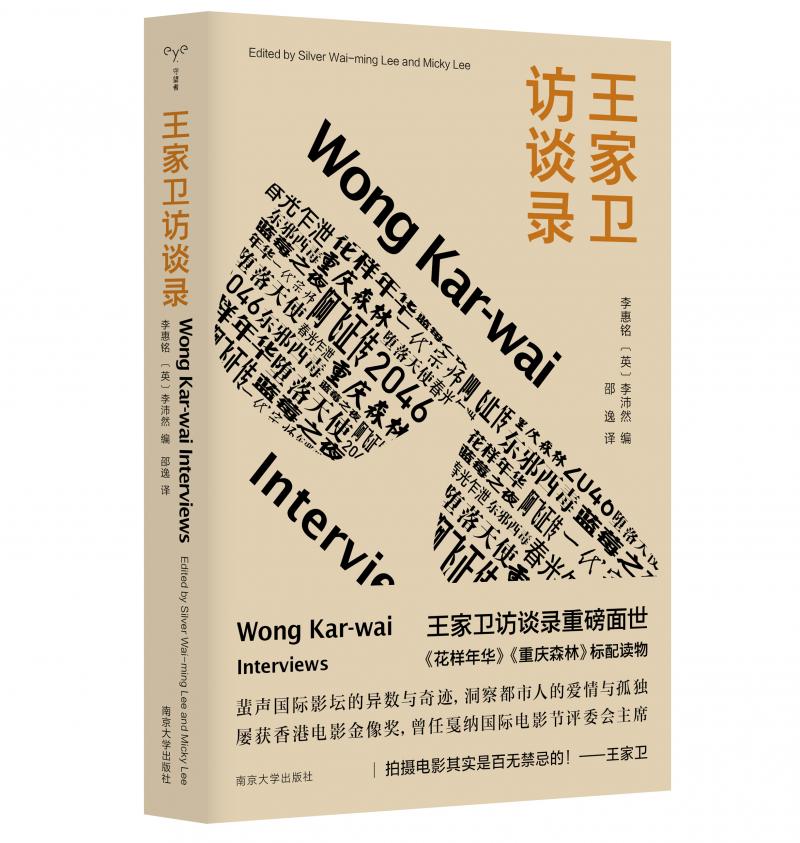采访者:在你的电影中,对白往往能够精简地刻画人物的个性和感受。
王家卫:我自己觉得其实不算是很好的,真正好的对白就是戈达尔的对白。我们的对白只属文艺腔,戈达尔的才算是poetic(有诗意)。
……
采访者:知道你拍《重庆森林》时用了即兴手法拍摄,有些导演用这方法来保持real time(实时),你的用意又何在呢?
王家卫:就像放假一样,人轻松起来。要训练返回自已的instinct(本能)、直觉的反应。我们平日生活,每一步都考虑得很清楚,所有事情都要安排得很精密、严紧,渐渐我们便对事物没有即时的反应,也就是失去了直觉。拍《重庆森林》就像突然推你出街,你只能做出直觉的反应,也让自己有番energy(活力)。
采访者:为何你的电影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剪接上呢?
王家卫:我通常会找一个我信赖的朋友替我剪片,然后我便可以用较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其实,《阿飞正传》不是剪得很久,谭家明只用了三个星期便剪完了。《东邪西毒》之所以剪那么久,是由于故事结构始终未搞得掂(定)。《东邪西毒》有很多零碎故事,如何将它们组成整体的意念,是我们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直至最近才能解决。《重庆森林》也不是剪了很久。
采访者:但见你剪来剪去都像不合心意。
王家卫:最大问题是我的电影不是由故事出发。若(从)故事出发,必有起承转合,一定是一场接一场,但我的戏是(从)人物出发的,容许很多possibilities(可能性)出现。
采访者:可能是这些possibilities和那非主流的叙事方式,令人讨论你电影时总离不开时空问题。
王家卫:现在大家讲戏,只是借戏来说自己的taste(品位)和看法,他们的讲法便变得完全与我无关。我开始觉得自己是object(对象),让他们借我这个object去讲自己的想法。
……
采访者:但你的电影确是文化界争论的焦点。
王家卫:可能我的电影里有太多线索,让他们develop(发展出)一套说法。
采访者:你的电影没有惯常的叙事方式,结构较散乱,而人物往往很有疏离感,于是有人说你的电影是解构主义。
王家卫:我的戏和解构主义是没关系的。可能你在里面找到蛛丝马迹,但我从来不是从这点出发的。我唔系大卫·林奇(David Lynch)。
采访者:香港大学里有某些课程很喜欢讨论你的电影,多是与后现代主义、香港文化、怀旧意识扯上关系。
王家卫:后生仔应该不要听那么多别人的话,这样会变得老气横秋,后生仔应该可以好直接,自己多看些电影比听人讲好得多。很多人将理论放入电影里,渐渐便会发现看电影看得很无瘾(扫兴),变成一条formula(公式)。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开始中意睇戏(看电影)时,你会睇很多影评,就像玩紧(在玩)一个游戏,看到些线索,便对号入座。其实我觉得这又怎样?有人说个(这个)form(形式)要这样,个structure(结构)要那样,结果又如何呢?我只想问:“你想点先(你想怎样)?”
采访者:你是否很抗拒理论?
王家卫:我觉得人总系会经历这个阶段的。只不过你要有一日跳出这样嘢,不要沉迷下去,否则真的会老气横秋。如果一个“靓仔”走来同我讲一大堆道理,我真会瞓低(晕倒)!其实这个问题在台湾是更明显的,他们十来岁的青年便成个学究,不如经历多些、创作多些更好。
采访者:有人说《重庆森林》给人的感觉像村上春树的小说给读者的感觉。
王家卫:可能是用号码和时间这些地方相似吧。当然,村上春树对我有影响,但若说我受村上影响不如说是受加缪影响。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说村上春树呢?可能只是借我的戏谈谈村上春树吧。
采访者:会否因为你和村上的作品都爱描写感情中那份机缘呢?
王家卫:我和村上春树唯一的共同点是,大家都是一个有感情的男人。
采访者:《重庆森林》中的林青霞一角,有人说她戴了假发和黑超(墨镜),又只是行来行去,根本不用找林青霞来做。
王家卫:我有时想:如果这个金发女郎不是由林来演,而是找个普通演员来做,大家又会否有这感觉呢?
采访者:我想大明星都建立了自己的某些形象,观众对他们有expectation(期待),看见某个明星,便想见到某些既定形象。
王家卫:正如有人问刘德华:做差人(警察)为何不打、不开枪呢?就因为是刘德华做行行企企(走来走去)的差人才有impact(冲击力)。大家认为那个演员有某些image(形象),当他不再是那些既有形象,观众便有惊喜。
采访者:有人说《重庆森林》中,林青霞与王菲擦身而过一幕很突兀。
王家卫:大家不容许有这个空间啫!
采访者:有人觉得前面有些引子会流畅一点。
王家卫:很多人会觉得有前面一段才会真实一点。加上香港电影要求有嘢发生,事件接事件一直去(进行)。可否事件之间角色坐下来饮杯茶?唔得(不行)。但饮杯茶那段才是真实时刻。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