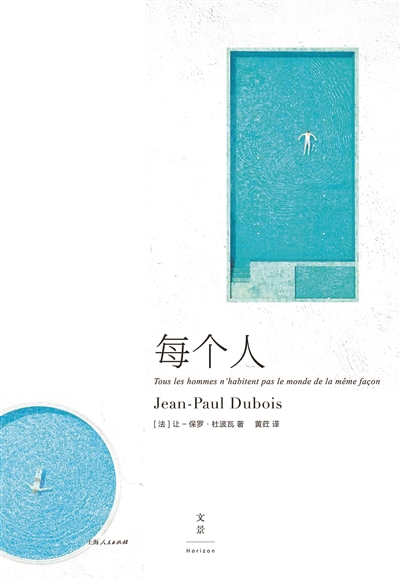“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不仅仅是对我的译作《每个人》的肯定,更是我30年来热爱法国文学、坚持文学翻译的最好见证。”2025年11月,在获得第十七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文学类奖项后,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这样说。
《每个人》译自法国2019年龚古尔奖获奖作品,法语原版书的书名为《并非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栖居于世》,直译是“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的方式都不同”,这是主人公保罗的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可以译得更像谚语:“人生在世,各有各的活法。”
黄荭最初就是被法语书名吸引,之后是那个动人的关于已逝幸福的怀旧故事。“正如潘多拉魔盒的隐喻,作者让-保罗·杜波瓦在冷静而反讽地揭示世界的残酷与荒诞之后,仍为我们保留了一缕希望与温情的微光。”中文译名《每个人》更简洁、更含蓄,更容易让每个读者在这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产生共情。
日前,黄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她与法国文学及文学翻译的故事。
从文学爱好者到 杜拉斯研究专家
作为苏教版、作家版、译林版和立体书《小王子》的中文译者,黄荭从小的阅读兴趣就很广泛,属于见到什么书都会随手拿起来翻翻的那种。“毕竟上世纪80年代在浙西南群山围绕的小镇上,书籍对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来说还是某种精神上的奢侈品。”
黄荭说她的父亲就爱读书,印象中他曾连续几年订一本外国文学杂志。当时她还在上小学,那种囫囵吞枣的阅读应该算是外国文学对她最早的启蒙。中学时,黄荭分别办了小镇图书馆、父母工厂工会图书室以及自己学校图书馆的借书证,什么书都看。上大学之前,她对外国文学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法国文学名著的中译本也已经读过不少。
报考南京大学法语系时,黄荭和多数同学一样并不很清楚学校和专业的具体排名,就是一门心思要考上重点大学,再加上喜欢法国文学。但大一时,主要课程是基础语言知识和法国概况,黄荭觉得颇为枯燥无味。她形容当时的失望:“就好像本来做好了拥抱整个法国文学无比丰盈的世界,结果却只塞给我一本干巴巴的法语入门书。”她因此甚至有一段时间产生了厌学情绪,“主要是受不了都德所说的最美的语言下那套复杂的语法体系,例外的情况比规则还多,尽管规则就已经是一套又一套的了。”
直到二年级的课程中渐渐增加了文学内容,黄荭才逐渐对所学专业有了兴趣和热情。再之后,热情越来越高,她顺势走上了从小就梦想的文学道路。“不过在文学的前面多了一个形容词‘法语’,在文学的后面经常还拖着一个‘翻译’的尾巴。”黄荭笑着说。
黄荭是杜拉斯研究专家,她的博士论文做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杜拉斯的东方情结,另一部分是杜拉斯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这么多年下来,杜拉斯早已占据了黄荭书房的整整一个书架,黄荭对她的研究还一直在继续。她牵头翻译了大部头的研究著作《解读杜拉斯》,译过她的传记《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杜拉斯和媒体的访谈《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甚至还有一个加拿大粉丝致敬她的法国偶像的《写给杜拉斯的信》,2014年杜拉斯百年诞辰的时候她出了一本文集《杜拉斯的小音乐》,2024年增加了新的内容更名为《我们仍在谈论杜拉斯》。
谈到自己对杜拉斯的兴趣,黄荭说源自1997年夏天本科刚毕业时,“当时蒙许钧老师推荐,和袁筱一一起为漓江出版社翻译‘杜拉斯小丛书’中的《外面的世界》。或许是‘外面的世界’让我看到杜拉斯的很多触角,或许是她打开的无限可能性和她作为知识分子的姿态吸引了我,之后的研究,是自然而然的。”
谈到被国人广泛关注的杜拉斯的小说《情人》,黄荭认为在这部作品的身上可以明显看出杜拉斯作品通俗化的一种倾向,这也是这本书在法国和世界各地拥有大量读者和拥趸的原因。“但在一个畅销书——用杜拉斯自己的话说是‘车站小说’——的外表下,《情人》其实是一本很好的探索写作和内心的书,是印度支那系列《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成天上树的日子》《伊甸影院》和印度系列《劳儿之劫》《副领事》《印度之歌》的内容和风格上的延续。杜拉斯的作品之间,作品和她本人的生活之间都有很强的互文关系,我觉得《情人》是这种互文网络中很重要的一个结点。”
被称为“最会生活的翻译家” 做翻译像栽培植物
黄荭被朋友们称为“最会生活的翻译家”,她也形容自己的生活是“无事花草,闲来翻书”。花草对于黄荭来说,和阅读、写作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名字‘荭’就是植物,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说的‘此蓼甚大而花亦繁红,故曰荭,曰鸿。鸿亦大也。’”
黄荭家有一个露台,她精心养护的花花草草在这里迎接朝晨日暮。最多时能结200多个果子的柠檬树已经陪她十几年了,还有玫瑰、绣球、爬山虎、络石、野蔷薇等等。
黄荭的“花缘”极好。有一株朋友送的苣苔,本来担心过冬养不活,结果第二年朋友的苣苔香消玉殒,她的却在春暖花开时长了好几盆。每年她都会从花市买各种花草,她认为“花儿是转瞬即逝的”,所以不要有“养不好”的思想包袱,“因为总有一些植物会水土不服,就像总有一些书翻了几页就读不下去,所以不必纠结。”
“花为媒”,黄荭因花草结识了许多同好,大家经常线上线下交流自家花园露台的消息。“我们也经常互相赠送花草,你给我木茼蒿,我还你迷迭香,就像你出了一本诗集送我,我译了一本小说赠你。”
黄荭曾翻译过科莱特的《花事》,中文首版里面的每一张插图都是手工贴上去的。她说:“最美的花就是亲手栽种的,因为在它身上倾注了时间。去年年初,我的老朋友陈卫新在小西湖堆草巷设计了一家书店,书店做的第一场活动就是‘《花事》——小巷里的森林’。因为《花事》,我也认识了厦门酷爱花草的作家苏西、书评人沈胜衣。其实不仅是通过书,植物也是,我身边喜欢植物的朋友很多,我家里很多植物就是亲戚朋友送的。你家的植物来了我家,我的植物去了你家,就跟翻译一样,如果没有翻译的话,很多语言死了就死了。文学湮灭了就湮灭了,但是因为有翻译,在这里消隐的文本因为流传到了别处在别处生了根,延续下来发扬光大了。”
黄荭形容做翻译像栽培植物,可能会让一本书重焕生机。“有的书,比如《小王子》,用毕飞宇的话说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但像这样老少咸宜的书还是难得一见的。也有一些书在原来的文化语境中已经不再被关注了,可能去到新的土壤里能收获新的读者群,产生神奇的化学反应。”黄荭回忆起大四的时候,曾经翻译过一些罗曼·罗兰的作品,她说罗曼·罗兰跟中国的相遇就是很奇妙的,“二战之后,他在法国渐渐被淡忘,但是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跟中国新文学的相遇开始,到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再度进入中国人的阅读视野,先后激励了几代人。我书房里还有读中学时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当初读就觉得很励志,很澎湃,专门包了牛皮纸封面,几次搬家都一直留在身边。”
黄荭的家里有满屋子的法国文学书籍和《小王子》的周边。她的朋友们知道她喜爱《小王子》,总是会带给她世界各地与《小王子》有关的东西,她也乐意与人分享这些书籍和周边的来历。
与马振骋先生的交往
傅雷翻译出版奖创立于2009年,是国内翻译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以纪念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而得名。此前,已有多位南京大学法语系毕业生的译著入围并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体现了南大法语系在翻译实践、翻译研究与翻译人才培养方面的优良传统,及其在中法文化交流中做出的贡献。11月17日安详辞世的知名法语翻译家马振骋先生不仅是南京大学外语系首期法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还是第一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文学类得主,获奖作品是他用十年时间潜心打磨的三卷本《蒙田随笔全集》。
黄荭是2008年认识马振骋先生的,“因为家中收藏的最早的一本签名本是他的《我眼中残缺的法兰西》(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何家炜特约编辑)。他在自序的开篇提到《东方早报》记者石剑锋对他的一篇采访中说,‘马振骋为法国文学而生’,他换了两个字,改成‘马振骋以法国文学为生’,说‘这才更符合实际’,这既是马老师的自谦,也是他的幽默和机智。”
因为都热爱法国文学,都翻译过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和杜拉斯的作品,都喜欢美食、花草和艺术,马振骋成了黄荭拜访次数最多的老一辈翻译家。“每次我去上海出差,若得半日清闲,就和张玉贞、林岚、段晓楣、刘苇、袁筱一等友朋三三两两相约去看望他。坐在他家19楼毫无遮挡、视野开阔的客厅,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自在从容,就着上好的咖啡或红茶,几盏精致的小点和糖果,围坐聊文学和艺术,聊作家和做人,聊日常和八卦。”那时候70多岁的马老师还经常骑自行车出门,乐于参加各种读书会和文化活动,打扮得很绅士,待人接物更绅士,温文尔雅,冷不丁冒出一两句金句,举座皆欢。
黄荭最后一次见马振骋是去年夏天,“那时他已经步履蹒跚,不再下楼,说脑袋多数时间昏昏沉沉的,容易疲累。”知道黄荭和张玉贞来,马先生在长袖T恤外面套了一个马甲,还打了一条同色系的小丝巾,“我们夸他‘老帅了’,他说想拍几张好看的照片留念。生死他已经看得很通透了,但很快,他又说,这个话题还是不要谈了。”
那天马振骋给黄荭和张玉贞都准备了礼物。黄荭收到的是一本Maja Destrem写的《圣埃克苏佩里》,是“巨人传”丛书中的一本。黄荭说:“作为国内翻译法国飞行员作家作品最多的译者,马老师在圣埃克苏佩里身上显然找到了某种深切的契合。这本传记不少地方他用不同颜色划了线,有的句子尝试做了翻译,有几处标注了相关参考文献的页码。还有几处他在页边上写下了阅读体会,未尝不是他自己对人生的感悟。比如:人只有在孤独中才找到自己,找到大写的‘人’,找到与人的联系;又比如:怀旧,莫名怀念比当前年轻的东西,剔除过去中一切不幸,负面的东西也成了愉快的回忆。”
面对语言平庸化的潮流 我们绝不能沦陷
作为一名女性,黄荭自然对女作家、女性书写更加敏感,能够产生更多心灵上的契合和共鸣。“像《花事》的作者科莱特,她给我更大的启迪就是对自由的向往,想做什么就敢做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读书,一定要读好书,因为一本好书带给你的真的不只是消遣了几个小时。”在黄荭看来,看一本书,如果真正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它的养分,那就像植物吸收了阳光和水分,“阅读其实就是植物的生长,人是需要阅读的。”
从事翻译工作多年,黄荭对翻译的认识和翻译风格也有变化。“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文字优美的文学,翻译的时候也会尽量去追求文字上的漂亮。但随着阅读量的增加,对文学的理解更加多元化,在翻译的过程中就会尝试更多的风格。觉得某种程度上,直白朴素的语言,会更加打动读者。”
老一辈翻译家对年轻一辈翻译家有所批评,认为有的译者语言拖沓啰唆,对此,黄荭认为:“老一辈翻译家往往具备古文功底,语言更加简洁凝练,而自媒体时代和快餐文化把整个社会的语言水平都拉低了,写作、出版、发表的门槛越来越低。虽然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学和语言平庸化的时代,但以文字为生,甚至以文字为使命的作家和译者应该对语言和风格有所追求,因为如果连我们都沦陷了,连文学都沦陷了,我们要去哪里寻找诗意的栖居呢?”同时,黄荭也强调:“古文能力是语言训练的一个方面,多读古今中外的经典,对一个人语言和风格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
在黄荭心中,阅读经典是一种回望,回望曾经有过什么,才知道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或者说看到以前的高峰在哪里,才会知道现在的低谷在哪里。她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阅读经验定格了她对人、对事、对生活的看法,“而我居然也在别人的故事和文字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书。说到底我只是一个跟在作者身后亦步亦趋的读者:作者创造,我再创造;作者思想,我再思想。自以为是‘我注六经’,殊不知多的是‘六经注我’。”黄荭说:“我努力让自己学会谦卑,对所读的每一本好书和坏书都心存感激。”
教职之余,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的黄荭仿佛永远在忙。目前,她正在对法国女性出版社联合创始人安托瓦内特·福克的《孕育》进行校稿。另外,也即将翻译加缪的《第一个人》和纪德的《窄门》。
每当书读累了,翻译倦了,黄荭就会走出书房“浅草居”,去露台上透透气,修剪修剪花草,她说:“那是我的B612小行星。”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