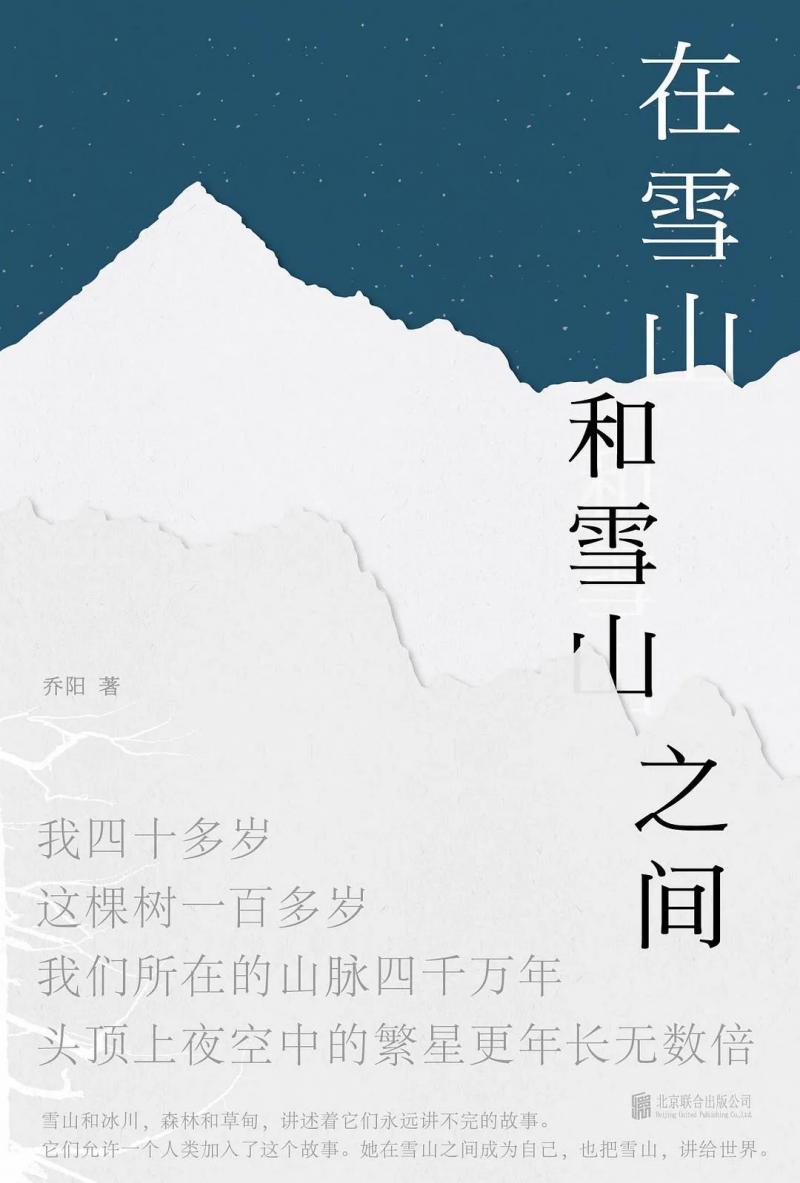乔阳,70年代生人,成长于四川小城。少年时,她在父亲的引导下打开《中国地图册》,看到了山脉、高原、极地,以及无尽蓝的海洋。成年后,乔阳开始自己的游历,走进滇西北的世界,穿梭于雪山和雪山之间。
如今,乔阳的儿子六岁,已经由她带着在海拔5000米看过花、抓过石子,他们未来还会继续奔赴森林与冰川,认识蚂蟥、羚,也许还有熊。“我四十多岁,这颗树一百多岁,我们所在的山脉四千万年,头顶上夜空中的繁星更年长无数倍”,“我希望他开始学习,并且在日后的成长中不要断绝与自然的来往”。
《在雪山和雪山之间》一书是乔阳对自己生活的记录。翻开这本书,雪山独有的凛冽扑面而来,松鼠的偶现又彰显了生命的灵动。“这不是从城市逃离而与城市相望的大自然,逃离是不彻底的胆怯,这是自然的自然,本来就在。”
1
山脉的伟大无可比拟。从山峰到冰川,林间溪流,湖泊与大河,布局巧妙合理。在我看来,三江并流区域是“山川”两个字在大地上的真实缩影—尽管我不太喜欢“山川”“山河”这样人文气息的词语,却不得不用它来表达多数人理解的情绪。
我总是想象自己在高空中俯瞰,我不需要羽翼,峡谷的上升气流足以带着我越过雪山,再往上,从更高处俯瞰大地的纹理。我想让我的老师来这里,他在我年少的时候为我介绍德沃夏克,喜欢音乐的人都应该来听听这自然的乐章,相比词语,音乐就真实得多。
当我站在云岭山脉时,在更远的青藏高原,山脉的源头,大气正在高空转换。低处的冰川,在阳光升起的瞬间,开始滴落一颗颗透明水滴,水滴从冰原开始汇集,在草甸和森林间逐渐聚成溪流,集合、奔腾。
同样发生着这些的,是江河源流沿途的山脉,我身边的梅里雪山、白马雪山、碧罗雪山、高黎贡山,在自然之力统一的指挥下,纷纷参与。融雪汩汩地在山间流淌,从高山草甸的灌丛,到杜鹃林下,谢绝古老的暗针叶林的挽留,一路从雪线之上速降4000米,汇入几条大江。
高原冰雪融水的河流接纳沿途的雨水,一路远去直至遥远南方深深的海洋,再由每年的西南季风带回到这些高山上,完成雨、雪、水的循环。季风沿途的植物以森林、草甸和河谷植被的不同形态,吸收、蒸发,参与这年复一年的回旋曲—如果没有它们,水汽在到达内陆600公里左右的地方,就会偃旗息鼓—这是美好的配合与真正的谐和。河流自北方来,风带着水汽从南方上溯,也带着花事,回馈远方。
阳光从另一个星球洒落下来,没有了之前我家乡盆地的阴霾。即便不从高空俯瞰,我也能看到这平行的山脉和河流,了解到垂直方向和水平纬度不同的热量、水分以及信息的交流。地球内部力量带来板块的撞击和山脉隆起,外部的力量—阳光、水、风、河流、植被以及人类深刻了这里的地貌。几千万年以来,每一刹那的变化累积到我们现在看到的伟大景观,一切都在流动,流动是伟大的力量。我在这力量的核心中。
在雪山与雪山之间,河流从高往低,从北往南;森林沿着山脉流动,我可以清晰看到林线的蜿蜒,季风在峡谷流动,它带来的雨滴从树冠落下,被土壤下方的根系吸收,流动到树干和枝叶。水在叶脉间流动,水雾在林间流动,苔藓吸饱了水从枯黄变成青绿,挽留住水分在土壤表层流动,暗流在冰川下流动……
我的血液在流动,如同江河,我思绪流动,如同云雾,这一切之上,阳光带着热量在流动,从星球之外穿梭而来,在冰川上,在森林间,在每一片草叶,在飞鸟的羽翼与走兽的脚步上,在我的眼睛里。
2
在飞来寺居住的时候,俗世的尘埃还不能到达神山的高度,我伸手出去就能牵回来几朵峡谷里闲荡的棉花云。天地洁净,卡瓦格博神端坐在云层之上,晚霞满天是他在巡游。
在他的目光下,藏人从澜沧江源头而来,云雾的幕障因他们庄严的祈祷而缓缓打开。他们的骨节粗大而扭曲,一路风尘,在雪夜里用羊皮囊燃起明明灭灭的篝火,他们唱起古老的歌谣赞美大地。
我无法忘记但永远不能复述那样纯真的歌谣,不曾经历风雨,不曾有过摇动的思绪。是不曾照过影子的小溪,飞鸟尚未飞过的天空。我看到自然的规则,大地和天空向我印证,山脉正直进取,与河流、与森林一起细细阐述,人类与动物安然生活,从未在其中凸显。
旅游发展后,我搬到更宁静的雾浓顶村。村子坐落在白马雪山山脉上,我的屋子坐北朝南,北面和东面是山林、松树和栎树,南面是雾浓顶村的田野,田野后一道小小的山梁,东头是松,西头是白桦。我从窗外望出去,是澜沧江河谷的一道道山脊,正西面是梅里雪山,它的南端是碧罗雪山。
早上迷离的光线从窗帘缝隙透进来的时候,常有山雀“笃笃笃”地敲击玻璃窗,急促地唤我起床。我拉开窗帘,它们惊魂不定地瞪着我,再嘻嘻哈哈迅速落跑,隐没在栎树林间。
运气好的时候,松鼠会晚些叫醒我。它一大早就来来回回地在屋顶和平台的栏杆上跑着,捡一些无用的果壳。我的房子是传统夯土藏房,屋顶是泥顶,承托泥顶的是椽子和很厚的“薪”,老鼠和松鼠都在里面做窝。“薪”是我根据德钦藏话选用的字眼,意思是柴火,细直的“薪”也用来盖屋顶。
我不太介意和老鼠松鼠们共生,这儿原来是它们的地盘。低海拔的朋友们送来河谷生产的核桃和板栗,高地的朋友送过来松子,大家都张一张嘴靠自然。半夜里听它们滚核桃,便感觉到它们的满足。
最好的时候,可以等到九点,牛上山吃草,叮叮当当的牛铃铛叫醒我。9月之后,牛从牧场搬迁回村庄,每天早上挤完奶,再放到周围山坡上吃草。牛铃铛据说有七种尺寸,我至今不能分辨,大约只能知道是老牛或小牛。走在前面浑厚的声音是成年的牛,它们走得很有节奏,偶尔齐刷刷停下来,集体仰望雪山。丁零当啷打破节奏的是乱跑的小牛,它们春天出生不久就被带到牧场,回到村庄,对一切都新鲜好奇。
大多数时候,不要任何事物叫醒我,我自己醒来,在天黑尚未转明时。几颗残星,山林黝黑,隐约可见山脉的走向,白马雪山,碧罗雪山,梅里雪山,善于夜飞的鸟群停止了穿越,一点躁动都没有,风在未生起处,河流缓缓,西边是澜沧江—湄公河,东面是金沙江,世界巨大、宁静,包容一切又空无一物。
如果天色阴沉有雾,那就起一炉火,窝在屋子里,还可以咕嘟咕嘟熬一锅玉米粥。如果天气好,往哪走都可以,看起来都很美。背后的山林是原始栎树和松树混交林,有偶尔的红桦。云南杜鹃和亮叶杜鹃混迹在其中,比低海拔的同品种晚大半个月,等到6月初才会开花,热烈地开放直到6月底7月初的第一场暴雨,或者某一天黄昏突如其来的冰雹。低矮处以小檗为主,其中一种当地人叫三根针的,可以替代黄连药用,另一种金雀花在雨季初来时开花,可以用来炒鸡蛋。
3
我喜欢坐在枯木上面晃悠,看向周围更深的林间,蔷薇科的植物很多,绣球藤和山梅花,它们白色的花朵像悬空一样,飘浮在浓重的绿意中。林下有野生菌,松茸、牛肝菌、一窝菌都长在这里,雨季的午饭很好打发,焖上饭,再去林子里找几颗菌子回来炒琵琶肉。有时我走得高一些,去到白腹锦鸡喝水的池塘,再高一些,直到看见西面的梅里雪山,以及猛禽迁徙的河谷。
往南走,越过村庄与田野。春天最早出现的是碎碎的荠菜花,以及蒲公英。早间气温太低,蒲公英也要等到近中午太阳热烈才会打开花盘,五月中下旬,桃花、野樱桃花开了之后,田野里逐渐看到明确的绿意,是冬麦和青稞,之后是紫色白色花的洋芋,田埂上逐渐换成了粉紫的紫菀和黄色鼠麴草,开小白花的接骨草大片的在路旁,必须凑近了,才能细细地看清它们每一个美丽无比的小骨朵。
小麦青稞收割之后的蔓菁还绿绿的,它们持续到冬季来临。深秋,接骨草结出红色小果果的时候,紫蓝色的翠雀和倒提壶蔓延霸占了田边。尼泊尔香青透明的纸样花瓣开在坡地上,火绒草更加干燥和严肃地站在一旁,这是我喜欢的两种。冬天啥也没有,风毛菊属的植物一团凌乱,要看到它的美需要晨昏的逆光。
大多数时候,在田野里看不到人。播种只要几天,拔草只要几天,收割只要几天,积肥只要几天,其余时候,人们到地里来做什么?
田野南面的山梁,树林里有煨桑台和经幡,放生的鸡在林间阔步。我也喜欢坐在这里,小松鼠清理了煨桑洒落的青稞和小麦之后,偶尔会跳到我的腿上。松和栎高大绵密,大部分时候,只能听到风从顶端的树梢经过,只在需要的时候,它才吹向林间,掠过松萝,郑重地吹起经幡。白桦林五月新绿,秋天金黄,在那之间的雨季,浓荫的林间,阴湿处是齐膝高霸气的黄花杓兰,以及秀美的紫点杓兰。
4
午后的时光大都无聊而懒散,每个季节都一样。日光太高,从半夜里就拼命生长的植物,在午后都开始疲惫,抓紧时间吸取太阳的力量,好筹备一个完美的睡眠,我也一样。风从峡谷里起来的时间,也是在两三点之后,早上峡谷吸取阳光的热量,一切逐渐升腾,上升的气流到了最高的极限,饱满和虚空同时存在,生成了风。风忙忙碌碌,它是喜欢平衡的事物。风起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我就待在家。
屋外的平台有两棵树,东面大一些的是黄背栎,西面小一些的也是黄背栎,它们穿过我平台的地板,嗖嗖地长高长胖,几年后争相触到屋顶。大一点的栎树下,我放了一张旧餐桌,小一点的栎树下,我胡乱钉了一张茶几,村民不用的藏房里拆下的承托,每两个叠在一起正好是凳子,极美的流线造型。有的时候,就算没有风,我也哪里都不去,我在这两棵树下来回,栎果嗒嗒掉落,我听着,看它们果实上可爱的小帽子,鼹鼠和小老鼠喜欢的那种。我们喝茶,吃饭,看书,烤太阳,打瞌睡。
有时候我走得更远些,带上简单的午餐,去到澜沧江边陡直的山脊。峡谷的气流回旋不定,流云聚散。忽然出现的阳光,一会儿打在峡谷的村庄,一会儿打在雪峰下的冰川。
我无事可做,背靠松树打盹,想象着对面的冰川巨人,它们穿着小砾石的溜冰鞋前进,轰隆隆地在森林间清除出一条路,边跑边抛弃异体。当阳光忽然打在冰川上的时候,我正睁开久闭的眼睛。一下子灌进来的阳光及反光的光海,宛如流星忽然陨落的强烈光线,用力冲进眼中,这一幕天真又强烈,是极为炫目的打击。等我闭上眼的瞬间,一切又迅即退让到灰白色中。睁眼,再等,也无任何提示。整个景象很肃穆。云不动,没有预示任何确切的信息,不知道风雨是否来临。
这样温和的阴天,正是我喜欢的。一切足以令人动容。我总是喜欢坐在半山腰同一块窄窄的石头上,来面对这些事物,脚下不远是往下的峭壁,直直插到澜沧江边。这个世界很安静,用不着交谈。雨季到了,秋天也很快,过几个月就要进入冬季。事物千头万绪的不确定中,有另外的一种笃定。
“大部分自然现象……是我们毕生无法见到的。我们所能看到的自然之美,只是我们愿意欣赏的那一部分,分毫不差……人们只能看到自己关心的事物”,梭罗的话一点不假。
无论物质或精神的体量上,雪山太大,以至于前些年我只看到雪山,后来才逐渐看到其他事物,比如植物。我惊喜地发现一个未知世界,立刻抽出大量的时间在这些山脉间行走,尤其从春季到秋季,我认识了很多以前我从未见到的植物——“认识”这个词微微让我有些胆怯。因为学习——包括植物分类学和民族植物学,都仅仅是业余。
我看到更多的植物个体、植被形态、植物和人、人和自然、自然的力量,这个由植物引出的、我之前未知的世界如此美妙绝伦,它们以个体和整体的语言论证世界的法则,我将在这本书中尽我所能讲述其中的一些片段,但无论怎样,它都是浅薄而片面的,不过是个人经验。
5
这中间我生下可爱的儿子。他的降生在一个短时间内改变了我的生活秩序,但很快我们就一起回到原来的方向。比较重要的改变是,我从独自的个人主义,变成一个“希望成为好人”的人。我关注周围,希望以一己之力,许给他一个更好的世界。
我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未来也将如此。他七个月上到5000米海拔和我一起看花,扭着他的胖屁股爬在高山上,抓起石子来看,抓起草往嘴里塞。高山小溪边的水木耳黑黑的,又有点晶亮,他发现这和石子不同。龙胆花更奇怪,手掌慢慢伸过去,还没有碰到,花朵关了,等一等,又开了,他不明白是阳光的原因,以为魔法了。
大狗陋陋是他的朋友,还不会走的时候,他俩在青稞地里呆着。大一点会跌跌撞撞地走了,他们喜欢去山上。小檗科的灌丛长满刺很不友好,对成人很麻烦,但孩子和狗在低矮处进出自由。沿着一条只有他们才看得见的秘密通道,嗖嗖地很快可以直达半山的一棵高大栎树下。那棵栎树真美啊,在茶马故道的玛尼石边,挂满松萝,巨大的树冠如同屋顶一样,松萝垂髫直达树下的大白花杜鹃丛。
我有时直接去大栎树下捕获他们,看他们一前一后摇摇摆摆地走来,把他放倒在肚子上,胳肢他,令他大笑,指给他看随风飘荡的松萝,看,是风。转过来趴着,可以找到林缘草地刚冒出来的,小指头一样高的矮紫苞鸢尾,湿润的角落,有一朵两朵直距耧斗菜,看,阳光的紫色。他不停地滚来滚去,听,枯叶还咔嚓咔嚓,它们在诉说去年的时光。
儿子稍大些,我有了相对多一点的时间。我逐渐关闭掉大部分的书籍,增加我在自然中的停留。人类的著作在自然这部大书的面前显得有些可怜,我为这里的历史、苦难与欢欣而叹息,但也深知这不过是过眼烟云,深沉美好的事物从来不曾失落。意想不到的生命的力量会在最衰弱的时候出现,就像如今当悲伤成为世界的情绪时,即使人所不知,大地也会促动生命力量的再度蓬勃。因为这是宇宙的大规律,一切相互关联和制约,趋向谐和与完善,它会促使灵魂清醒。
我看到的自然至今仍然是残缺的,我完全不懂的众多动物与鸟儿定会嘲笑我。在知识的学习和经验的获取同时,我同样也谨慎地不把“我”的一切已有的带入自然中,我聆听,赞赏它,静下心来,不带任何思绪和急切的主张,仅以纯净把自己委托于它。
因为儿子读书的原因,三年前,我们从雪山脚下搬到大理。我们在乡村的老院子里居住,朝南的土地有梨树、桃树、缅桂花,我又种了冬樱与木槿,树下是菜地。我们住在田间,但儿子和我都还是觉得大理太吵,而且总不能真正天黑,我们回到了算得上城市的地方,但是显然这带来了其他的困窘。
我们坐在四方天空下的石阶上聊天,有时候我忙,他就自己找块纸板铺在院中,躺在地上看云。月亮从洱海升起来,之后会经过我们的院子上空。燕子在他身后的廊檐下搭巢孵卵,他提醒爸爸不要开灯,也不要盯着它们,因为“就算只看,它可能也会害怕”,我也不知他何时参与了燕子的交谈。最近他开始学写字,坐在窗前写着写着就发呆,我质问他,他就笑,“妈妈,不是我,是风”,而风就在梨树和樱花树间哗哗作响,回应他。
海洋、高山、沙漠、草原,他走过很多地方,最多的还是在滇西北,两岁多他在白马雪山徒步;三岁多翻越碧罗雪山,从怒江来到澜沧江。他随他父亲在海上看星,小手穿过洋流的方向;他随他母亲在流石滩上看花,溪流边见冰凌,林深处看雾。今年他六岁了,我们计划暑期再去森林与冰川,有蚂蟥,有羚,也许还有熊。我希望他开始学习,并且在日后的成长中不要断绝与自然的来往。
6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常常处于杂乱与困顿中,在我最困顿的时候——这是感知恢复的最好时机——我习惯在自然中获得支持。在城市的周边寻找可以十几公里徒步的山野,既不属于来处,也不属于去处,只在当下的行走中,阳光、风雨、些许植物的照拂,就能在忙乱的生活中长长地喘一口气,获得精神的恢复。
在我离开雪山后,每年仍然拿出几个时段回到森林与牧场,在那里安静生活一阵子。人类侵入的地方已经太多,这里是我认为的,中国目前尚存的、少有的仍然具备并彰显着自然伟大力量的地方之一。这是相比城市郊野更为珍贵有力的能量。
我的手机里有密密麻麻的航程图,有的区域已是密而不分的色块,这是我部分的生活,虽然我所珍爱的人们都在这里,但我仍然要说,这可能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手机图库里,是自然的那些片刻,绿色江水边桃花灼灼,报春花瑟瑟站立在冰雪融水中,白腹锦鸡悄悄踱步走出树林,我在草甸上睡觉,跷起二郎腿,突来的暴雨、瞬间的冰崩,季风正吹过暗针叶林,一朵白云在山头追问静寂……
我向自然寻求,它提供给我隐秘的支持,让我毫无惧意,以它的恒常和变化,以及其中蕴含的丝毫不被打乱的和谐,带给我深度的休憩。这不是从城市逃离而与城市相望的大自然,逃离是不彻底的胆怯,这是自然的自然,本来就在。
我深察自己,是否因外界制约而虚化了一个内心世界,并杜撰出巨大的热情,我鄙视虚假的热情。而一朵普通的雪花,融为掌心一滴普通的水,至少多次化解了我的疑惑——虽然我还未知晓我的核心,它也许在未来某个时刻。
自然于我,不是风光、景物,不是田园,不是旅行,不是艺术与情感的自然,也不是民族的、宗教的、哲学的、科学的自然,或者说,不仅仅是这些。有的时候,我会停留在这些片段中漫步,更多的时候,我必须像箭一样、像光一样穿越这些人类的“自然”,回到荒野,回到最初的那个自然,在开始时就存在,自身独立存在,并在一切事物中起作用的能量。在这样的行程中,我谁也不带,也不带我自己。而自然接纳我本身,无须动作,毫无声息,好像一束光回到光之中。
本文节选自《在雪山和雪山之间》作者: 乔阳;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品方:乐府文化;出版年: 2020-7
来源:凤凰网读书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