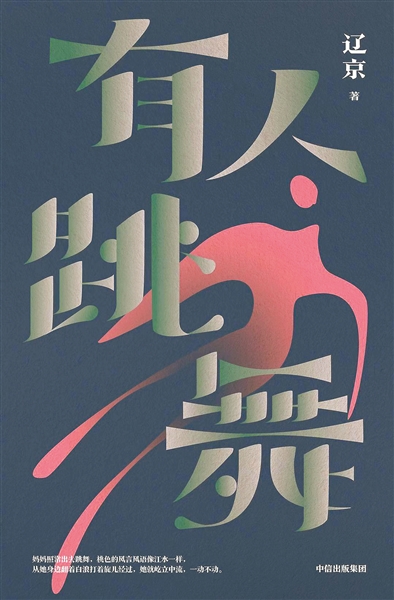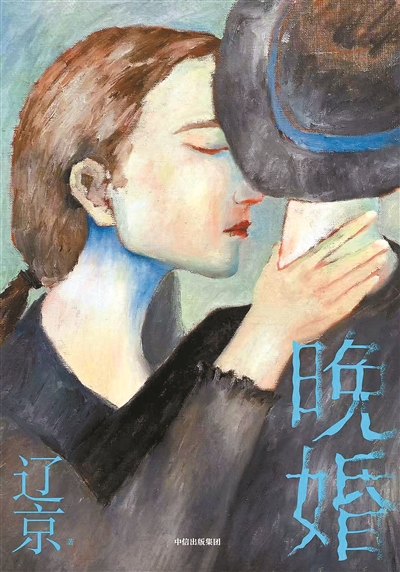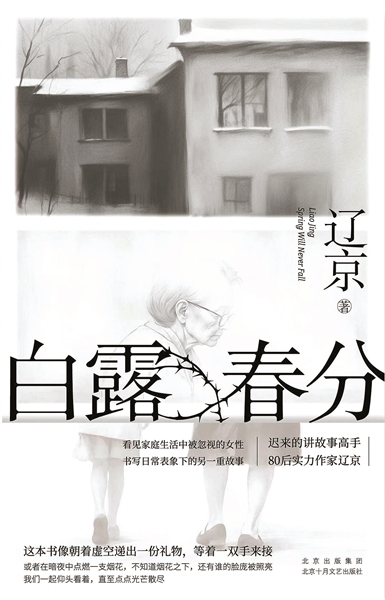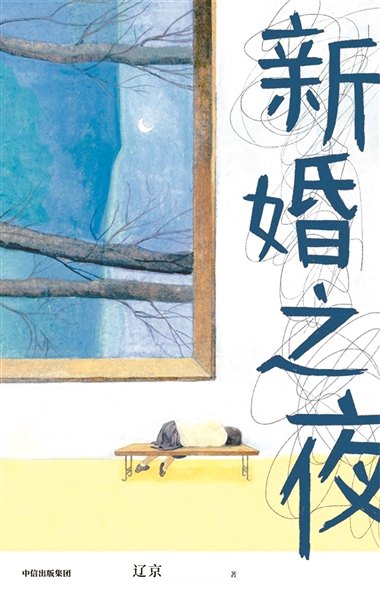作家辽京近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新婚之夜》《有人跳舞》,长篇小说《晚婚》《白露春分》等,在当代青年文学创作中引起重要反响,她也凭借《白露春分》荣获了2024年度刀锋图书奖“年度青年小说家”,并入围了2025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
辽京年少时在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长大,那里也是北京猿人的发现地。
她是被奶奶带大的孩子,六七岁时才回到父母家中。她的爷爷奶奶都是一家水泥厂里的职工,她就住在厂区家属院的平房里,爷爷在她四岁那年就去世了,奶奶家里挤着小辽京、辽京叔叔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辽京从小就在学习做一个懂事的孩子。据辽京自述,她的父母都在银行工作,在养育子女上较为生疏,因为常常加班,陪伴女儿的时间也不充裕,有一次临近年底,妈妈很晚了也没回来,辽京以为自己被抛弃了,在家大哭。大部分时候,她跟爸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从爷爷奶奶家到父母家,也许是因为切身感受到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让辽京在书写家庭时得心应手。
你呼呼大睡的夜里 妈妈开始写小说
辽京1983年生人。当韩寒、郭敬明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炮而红时,她刚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毕业,做过两年翻译,后来转行去门户网站和杂志担任记者,做了五年,虽然没有很喜欢,但也培养了自己的选题意识和观察人物的能力。步入婚姻之后,她做了一段时间全职主妇,生育和带娃的繁琐日常,让她很难有整块心无旁骛的时间来进行创作。
在一次采访中,辽京说:“那几年有一种很急切的想法,写小说成了我一个很重要的愿望。带完小孩儿写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经历过那种24小时身心都被一个孩子占据的时光后,你会更投入、认真,因为知道这个时间来之不易。”
2017年,当辽京终于把一些作品修改完毕,她决定先在豆瓣试水看看。
早期的辽京是一名比赛型选手,在她的豆瓣阅读主页里清晰地标注着:“2017-09-25 发表第一篇作品。有时候粉饰太平,有时候危言耸听。”
她在豆瓣阅读发表了20部作品,第一篇叫《夜的井》,那是一篇28000字的中篇小说,讲述一个年轻人在两段感情之间的摇摆,没有得奖。当时的豆瓣阅读征文大赛还没有完全倒向便于影视改编的类型文学,而是各种类型的作品都有一些,譬如风格偏荒诞主义的《春节就是一场疯人秀》,写青春期的性、暴力与死亡的《吃麻雀的少女》,像石黑曜、慕明、魏市宁、朱一叶、兔草等作者都是征文比赛的常客,在2016—2019年期间,日后被人熟知的班宇、林棹、魏思孝等作家也在豆瓣发表作品,辽京也是其中一员。
在赛博网络世界做一个文字学徒,步入婚姻的辽京用文字为自己打开另一扇窗。早期的她没有定型的风格,似乎仍在摸索何种叙事语言自己最有把握。比如《漓滋水怪》是淘气孩子般的散漫活泼,遮住作者名字颇有点王小波门徒的趣味;《人世的细雨》是灵巧的青春小品,宛如一段段夏日的白噪音,不求多大意味,自有俗世中青春的趣味;《巫山一梦》结构松散,语言不够省净,但已然可见作者善于描摹都市亲密关系的暗流;散文《买包记》语言平实轻盈,写一个婚内女性对购物、着装的思索。
辽京写作生涯的第一部关键作品是短篇小说《模特》。这篇小说获该年豆瓣阅读短篇小说比赛“戏剧时刻”的“中年风暴 最佳作品奖”。
《模特》体现的是一个作者对分寸感的把握。它不是一个新的故事,如果你读完全文,你会发现这样的故事已经被书写太多,这个男主人公会让你忍不住皱眉头甚至感到厌恶。但辽京的能力就在于,她能让一个陈旧乃至略显狗血的故事仍然富有回味,她在每一个容易失控的点都刚好刹住车,用细腻的人物心理挖掘、有分寸感的戏剧转折,让这个故事稳稳地落了地。
《模特》之后,辽京又陆续发表了《看不见的高墙》《新婚之夜》《我要告诉我妈妈》《星期六》《默然记》等小说,其中若干篇目继续赢得豆瓣阅读征文大赛的奖项,这些小说大部分也收录进她的纸质作品。到了这一阶段,辽京在创作风格上趋于成熟,她惯于写孤独与婚姻、女性心理、中年人进退维谷的生活状态。她的文字像冷水浸纸,能不动声色地写一个人灵魂的暗面,也能刻画都市常人在意气风发的阶段过后那冷暖自知的余生。
2019年,辽京首部小说集《新婚之夜》出版,在这本书的扉页,她写道:“送给陈静川小朋友,你呼呼大睡的夜里,妈妈开始写小说。”
用“反类型”的笔法经营故事
从2019到2024年,辽京先后出版了三本书,其中《晚婚》是她的首部长篇,《有人跳舞》《新婚之夜》收录了她创作于2017—2022年的中短篇。
辽京爱用短句,语言错落有致,语调清冷、凌厉、绵里藏针。譬如《名字》这一段:“那些温存的夜晚像一摞圆润的白瓷盘子,洗得干干净净,闪闪发光,整齐地码放在桃子的记忆中,于是她常做梦,梦见那些甜美和温柔。房子倒塌的时候,她甚至都没有惊醒。”
她喜欢写厨房,写房间和女人的关系,用物的解构来营造女性的处境。
“她喜欢买厨具,漂亮的锅铲、外形奇怪的烧水壶、很贵的铸铁锅,冰箱上盖着钩花罩子,拉得平平整整,窗台上一排小盆绿植。”
她留心女人常去的空间。写菜市场:“迎面一堆小山似的红灿灿的蜜桃、粗而长的青杧、玻璃球大小的紫葡萄,无穷无尽的色彩和甜美,李子的颜色那么端庄好看,使她看了以后,很想去买一件李子色的毛衣。”写家里的房间:“待在整洁明亮的家里,她觉得自己毫无用处,只能出去买菜。”
如果将《新婚之夜》视作婚姻故事集,或许低估了辽京的叙事用心,在我看来,这部小说集最有巧思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叙事”,故事说来道去,都是那些个故事,可是怎么讲一个故事,才是业余作者和成熟小说家之间的差异。《新婚之夜》里的多个故事都带有“叙诡”的,作者用侦探小说的方式将读者引诱进来,但层层递进的却是反类型的写法,作者在不厌其烦地进行一种尝试——怎么用类型文学的笔法开场,用纯文学的方式收尾?
这么区分其实也是简单的,因为文学显然不是类型文学与纯文学的二元对立,更准确的表述是——辽京从侦探、科幻、推想小说等类型中拾到了不少武器,但她在意的不是讲一个无懈可击的类型故事,而是怎么用类型的武器,传递严肃的关于人生况味的表达。
在辽京看来,创作就像是一次次建造房子的过程:“建一所房子,天冷的时候,路过的人可以自由地走进去取暖,休息然后离开。那里炉火总在燃烧。”当小说家盖这座房屋时,重点不在于一个故事是否真实,是否一定要有现实来源,而是它的内在逻辑是否自洽,它整体营造的氛围能否打动读者。
“放弃对孩子的控制 也是给自己卸下枷锁的过程”
写作之于辽京,既是一次次对关系、权力、性别等议题的凝结探索,也是运用虚构这尊陶器,对记忆中难以忘却的“一瞬”进行封存。
譬如小说《星期六》关乎的是一段童年记忆。小说中兄弟的原型是辽京奶奶家的邻居,其中哥哥因罕见的疾病而瘫痪在床,因此这家才要了第二个孩子。哥哥的瘫痪直到成年后也没有治愈,辽京曾听奶奶说起这家人,奶奶关切地说,那孩子长大后谈女朋友是个问题。到后来,辽京也没有遇到那对兄弟,但对于他们生活的想象,长长地萦绕在她心里,于是有了《星期六》这篇小说。她试图从生活逻辑出发,而非采用强烈的戏剧冲突来编织这个故事。
类似的,《娃娃》是关于做母亲后对孩子的爱与恐惧;《晚婚》糅合了一部分北漂的生命记忆;《雪球》从自己与身边人的母女关系入手,描绘两代女性的冲突与和解,探索母女之间更加解放、理解彼此的相处方式。辽京在谈论《雪球》时说:“放弃对孩子的控制,也是给自己卸下责任、卸下枷锁的过程。”
在小说集《有人跳舞》中,辽京也在尝试其他之前很少涉足的写法。比如《名字》是通过一只猫的视角来写故事。《前夜》的主角则是一个仿生人银行柜员,她在逐渐觉醒期间遭遇了行长的性剥削,在明白“性剥削”意味着什么之后,她做出反抗,在逃亡期间偶遇隐藏在人类社会中的同类,她才知道,自己并不是第一个觉醒者,只不过先前的觉醒者都蛰伏起来,他们没有立刻发起革命,而是小心翼翼地潜藏在人类社会之中。所谓“前夜”,既是指仿生人因觉醒而对自我、对整个地球社会将会引发的质变,也暗示着当作为服务者、工具的仿生人出现反抗意识,也意味着他们对性、权力、主体的认识将会有整体性的翻新。
因此,我们固然可以说辽京是一个通俗小说家,但如果此处的通俗代指“她的小说缺乏对小说语言和结构的探索”,或“她只是延续了业已证明成功的叙事模式”,下此定论者很可能因此错过辽京小说的许多巧思。作为对比,我更愿意将辽京视作蕾切尔·卡斯克、艾丽丝·门罗那样写女性俗世生活的作家,她们从生活的细节处入手,嫁接类型小说、其他学科的元素,以小见大地反映了权力、爱欲、自毁、自由与秩序之辩等议题。这些小说关于女人眼中的自己、他者、职场、家庭,女人活在这个世界潜在背负的种种代价。在辽京的小说里,写作是一次次对他人生命的西西弗斯式寻找,俗语说“人与人的悲喜并不相通”,而小说家能做的,大概就是建立这种抵达,让我们发现——宇宙中不同房间都有连通彼此的密道。(阿尼亚)
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