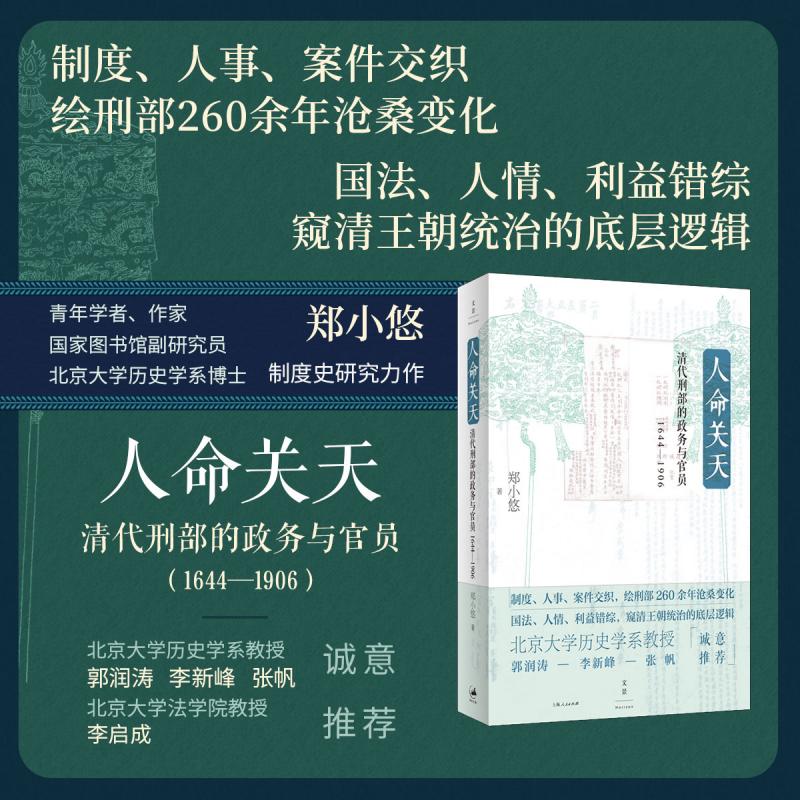雍正帝直到临终前,仍然念念不忘刑部的问题,屡次向嗣君谈论“近来各部皆有章程,惟兵、刑二部办事多有未协。兵部尚书高起性情乖张、怀私挟诈。刑部尚书宪德识见卑鄙、昏愦糊涂”,然而未及降旨更换,自己就骤然离世。乾隆帝对此记忆颇深,一经即位,即将二人解任,并继续致力于刑部的改革,使之在专业化道路上大大推进,得以与“天下刑名之总汇”的地位名实相符。
乾隆朝刑部的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秋审的强化与秋审处职能的改变。康熙十二年(1673),刑部开始接替各地督抚主导秋审。其时,秋审事务由各司核查,归政务最简的四川司汇总,京师朝审则独归广西司办理。雍正年间,四川地区移民涌入,户口充盈,各类治安事件激增,刑部四川司也由简转繁,无力承担秋审重任。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刑部奏请在刑部内盖造房屋,专门设立一“秋审处”,由各司派出总办秋审满汉司官各二员、笔帖式四员、书办二名、贴写四名,负责办理秋审文书档册的刊刻印刷等事宜,但覆校案情的工作,仍由各司处理。
雍正末年的秋审处,主要还是承担秋审事务性工作,直到乾隆七年(1742),其职能才发生质变。乾隆中期的刑部侍郎阮葵生在《秋谳志略》一书记载,在这一年,秋审处增派了满、汉司官各二人,且开始针对秋审案件本身展开工作,即核定情节、分别实缓,目的是防止各司办理过程中有畸轻畸重之弊。
根据清代的法律,斩罪、绞罪的条文大都只规定到是立决还是监候而已,至于监候者最终如何处理,非成文法所能解决,全靠秋审主持者根据具体情节及旧有判例处理,故有“秋谳衡情”之说。康熙年间的秋审分为情真、缓决、可矜可疑三等,雍正时改为情实、缓决、可矜、独子承祀留养四等。情实者请旨勾决,缓决者仍行监候,可矜及独子承祀留养者则可以马上减等发落,差之毫厘即谬以千里。既然没有统一的条文标准,刑部各司各办各事,不能在短时间内逐案讨论沟通,自然容易出现同罪异罚的情况。
乾隆二年(1737),因为雨泽愆期,乾隆帝下旨将雍正十三年(1735)以前秋、朝审未经赦免,但尚有一线可矜的缓决人犯具奏减等发落,刑部各司按照秋审的核查程序将这些人犯分为缓决、可矜两等,送九卿科道会议讨论。会后,御史谢济世上奏,连举刑部文稿中畸轻畸重之事若干例,严厉批评刑部“不取大同小异之案比其轻重,而漫议矜、缓”。那么要想解决这一问题,组织精干力量,在各司基础上对当年所有秋审案件统一尺度、整体考量,是唯一办法。而将这个任务放在负责办理秋审事务性工作的秋审处身上,对其进行功能升级,也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到乾隆中期,秋审处承上启下,握秋审之总纲,其重要性已经显露无遗。秋审处的总办、协办之名是差遣而非本职,有着相当的灵活性,所派司官不但通晓律例、才具出众,且必定与堂官关系密切。乾隆中期以后,秋审处总办等司官逐渐拥有了很多特权,如“保举京察多系总办秋审之员;既派总办秋审,复令管理赎罪处、督催所、律例馆、司务厅、饭银处、赃罚库,以及清、汉档房诸务”“各司签分现审稍涉疑难之案,堂官专派总理(秋审处司员)会审”“当月司官收管各处文移、现审案犯,倘遇奏事之期各堂不能进署,伊等即代堂掣签交司”等等。秋审作为国家大典,向来受到皇帝的重视,秋审处司官也往往能突破品级所限被皇帝认识,从而获得极好的前程。
秋审处职能的转变,不但促进了秋审制度的完善,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刑部的人事管理模式。秋审处司官的仕途宽广,刑部新进司官无不以派办秋审为荣。秋审处司官的选取以“通晓律例,善于属稿”为标准,新司官凡有上进之心,自然要努力钻研律例。加之此后的管事堂官亦多系秋审处老司官出身,感情使然,亦对秋审处新进多有培植,带动部内良性的读律风气。
其次是律例馆的归属变化和律例修订的规范化。清廷自入关之初,即听从汉臣建议,于顺治二年(1645)开馆编修《大清律》。新律告成后,律例馆并未解散,始终设在内阁,因时因事增修条例。康熙、雍正年间,清廷皆有大规模修律之举,皇帝临时指定大学士、部院大臣等充当总裁,并从在京各衙门中抽调通晓律例的官员充任提调、纂修官,到律例馆集中工作。乾隆元年(1736),皇帝再次下旨增修律例,八年(1743)刊刻完成。时任刑部尚书的来保提出建议,将律例馆全部馆务移交刑部管理,所有提调、纂修、收掌、翻译、誊录官员,改由刑部司官、笔帖式拣选兼充,毋庸专设。[1]因为此前设在内阁时,律例馆除了纂修刑部律例,还有纂修吏部铨选、处分则例之责,此后亦行剥离。改为刑部内设机构后,律例馆每五年一次,增删、修订刑部新例,其总裁及提调、纂修官不必另派,只需由刑部堂官奏请,交本部司官办理即可。
清代律例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继承前代遗留;二是由刑部及内外大臣官员奏请增改修订;三是由已办成案奏准通行,五年一次纂入律例。后两类是乾隆以后条例的最重要来源。律例馆既然承担修律之责,就必须大量掌握刑部办理的成案,否则既不能在修律时提出恰当的意见,亦不能将奉旨通行的成案准确上升为法律条文。是以律例馆在归入刑部后,逐渐兼有了部内“档案室”兼“研究室”的功能。乾隆四十年(1775)左右,刑部将所谓“积年成案”的文卷都放到律例馆[2],各司在办案时如果遇到“例无专条、情节疑似”的疑难案件,从原来的“堂、司确商面陈”,改为由主稿司官拟好一个草稿,即“说帖”,呈给堂官,堂官批交律例馆覆核,律例馆司官根据律例、成案权衡轻重,再拟具“说帖”,呈堂定夺,交本司照办。
换言之,律例馆改归刑部之后,清代流刑以上重案在经过由州县到督抚的层层审转后,在刑部内又增加了一个核查环节。律例馆的提调、纂修官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馆内保存的大量律例、成案资料,为疑案的审核再次把关,以减少冤假错案的出现。归于刑部后的律例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修订律例、保存档案机构,而成为比十七清吏司更权威、更专业的疑难案件再覆核机构。
律例馆和秋审处一样,都是刑部储材之地,总办秋审处与提调律例馆有互相兼任者,亦有独任者。除办理秋审和修订律例的本职外,秋审处司官更多承担本部现审案件的派审任务,而律例馆司官则更侧重各地上报刑名案件的覆核。由于本部现审多有涉及官员的大案,而地方上报以一般刑名案件为主,是以秋审处司官在北京官场中影响更大,扬名超擢的机会也更多。但以律例精熟、经验丰富论,二者不相上下。吉同钧评价光宣年间的律例馆司官时说“盖律例馆为刑部至高机关,虽堂官亦待如幕友,不以属员相视”[1],可见其地位之高。此外,收藏有大量档案的秋审处与律例馆是乾隆以后案例集和律学著作的主要来源。取材于前者的“秋审文类”,与取材于后者的“说帖”“驳案”“通行章程”等刑案汇编,或由刑部官方编纂出版,或由本部司员随身抄录学习,外任后经幕友等协助刊刻。到同、光年间,已经蔚为大观。这些案例集成为各级政府的办案指南,以及民间学幕、学讼的主要教材。
乾隆初年方兴未艾的秋审处与律例馆,在此后的百余年里,不但是刑部法律专业化的枢纽,也成王朝法律知识传播的源头。
来源:文景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