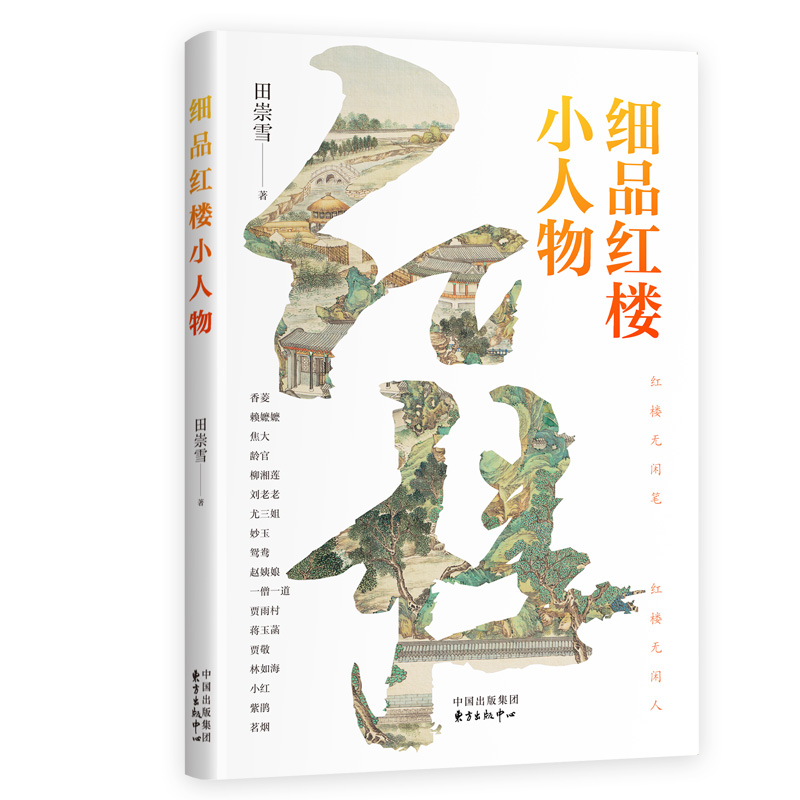他是《红楼梦》中被读者严重高估了的男性形象,尤其是被女性读者严重高估了的男性形象。他的出身被高估了,其实没有那么高;他的性情被高估了,其实没有那么酷;他的才能被高估了,其实没有那么专业;最重要的是,他对待人生的那种游侠态度也是被高估了,其实没有那么严肃、认真和成熟。
他其实不过是个经常活在自己为自己设定的角色里不能自拔,连自己都被自己骗了的英俊少年。
扮酷少年
《红楼梦》中的男人多半龌龊,柳湘莲却翩若惊鸿。其虽出场不多,但却如电光石火般,被我们永远记住了。这当然有赖于曹雪芹的笔力,但更有赖于柳湘莲本人复杂而独特的个性魅力。
柳湘莲貌似走错了小说空间,他应该是活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你看他容颜的俊秀、神情的冷漠,腰系长剑的洒脱,衣袂飘飘,江湖浪迹,萍踪侠影,更兼快意恩仇,仗义疏财,随兴随性……有个特别现代的词非常适合他:“高冷”。对,就是“高冷”。
他的身上,有着太多令少女少男着迷的光环和气质。生活中的登场恐怕亦如他在舞台上的客串亮相,一个闪身就会博得满堂彩吧?
我们且看曹公如何描绘他——
那柳湘莲原系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已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第四十七回)
这是原著中作者的介绍。
一贫如洗,家里是没的积聚的;总几个钱来,随手就光的。 (第四十七回)
这是柳湘莲的自我标榜。
天天萍踪浪迹,没个一定的去处。 (第四十七回)
这是青春好友贾宝玉的介绍。
大匠运斤,就这么三斧子,曹公就在形象、做派、风格上为我们“砍”出来这么一个“奇男子”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亦足够惊艳了。
然而,很多事情,换一个角度去看,就大相径庭了。尤其是经典的阅读,一大忌讳就是轻率和草率。必须细读、精读,甚至不仅要读文本之内还要读文本之外。因为曹公毕竟是“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其春秋笔法比比皆是,其草蛇灰线伏笔千里,横云断山丘壑满布,不写而写互文见义……几乎中国文学史上所有的写作手法都被他用了个遍,而且是非常娴熟,几近出神入化之境,因此,一不小心就会被其瞒过。
是的,少读红楼,就被他这样瞒过。
暴打薛蟠,我以为是柳湘莲的精神洁癖;施救薛蟠,我以为是他的肝胆侠义;非“绝色”不娶,我以为是他的风流高格;诺婚赠剑,我以为是他的君子一言;遁入空门,我以为是他跟贾宝玉一样,把红尘看破;甚至他的赖婚食言,我也能找到理由为他开脱。现在看来,少读红楼,匆忙结论,也正如这柳湘莲本人,处处显出轻率和草率来。
腹内草莽
再读红楼,便越发觉得,这是一个既有些不太靠谱,又有些许复杂难言的人物。我们试着再做分析。
对友情,他很轻率,但似乎又精致利己。
他暴打薛蟠,如果说是出于精神洁癖;他施救薛蟠,如果说是出于侠肝义胆,那么,救了薛蟠之后立马与他结为生死兄弟,就有些匪夷所思了。从最初的厌恶痛打到后来的施救、结拜,虽说是不打不相识,但这画风转得有点太快。从已有的描绘来看,柳、薛终归不是一路人。这种结拜,如果不是出于过于天真的轻率,就是出于过于精致的利己。毕竟,从前文的三段介绍来看,他不但是一个败落了的已无恒产的世家子弟,还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浪子,又惯于结交各路豪杰兄弟。现实的问题是,钱从何来?除“做强梁”之外,无非就是朋友的施舍。那么,像薛蟠这样的未曾败落的皇商子弟,应该是很好的金主。如此看来,在为人上,这柳湘莲越发连薛蟠也不如了。薛蟠的确不堪,但他不装,是真流氓,但这柳二呢?想想都有些恐惧。
对婚姻,他很草率: 既草率允婚,又草率赖婚。
有观点认为,看一个男人,就看他如何谈论女人;看一个女人,就看他如何谈论政治。也就是说,一个男人,他的女性观对评价他本人来说,是个非常关键的尺度和标划;一个女人,她的政治观对评价她本人来说,同样是个非常关键的尺度与标划。曹雪芹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的女性观是超越了他的同辈作家和前辈作家的,既是超越流俗的,也是非常现代的。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把女人当人去写、去看、去爱,这是前无古人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即便是在今天,芸芸众生不说,就是那些行走中西如履平地、满口洋词风流自认的所谓学者,仍然坚持着前现代的女性观者大有人在。
我们来看看柳湘莲的女性观。
《红楼梦》第六十六回,肩负着尤氏姐妹的重托,出差外地的贾琏准备与柳湘莲说媒提亲,恰在平安州巧遇结拜后的柳湘莲和薛蟠。当贾琏将亲事提起之后,柳湘莲道:
“我本有愿,定要一个绝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贵昆仲高谊,顾不得许多了,任凭定夺,我无不从命。”贾琏笑道:“如今口说无凭,等柳二弟一见,便知我这内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无二的了。”湘莲听了大喜,说:“既如此说,等弟探过姑母,不过一月内,就进京的,那时再定,如何?”贾琏笑道:“你我一言为定。只是我信不过二弟,你是萍踪浪迹,倘然去了不来,岂不误了人家一辈子的大事?须得留一个定礼。”湘莲道:“大丈夫岂有失信之礼?小弟素系寒贫,况且在客中,那里能有定礼?”薛蟠道:“我这里现成,就备一分,二哥带去。”贾琏道:“也不用金银珠宝,须是二弟亲身自有的东西,不论贵贱,不过带去取信耳。”湘莲道:“既如此说,弟无别物,囊中还有一把‘鸳鸯剑’,乃弟家中传代之宝,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随身收藏着,二哥就请拿去为定。弟纵系水流花落之性,亦断不舍此剑。”说毕,大家又饮了几杯,方各自上马,作别起程去了。(第六十六回)
从这一段柳湘莲允婚可以看出,其对终身大事是多么草率,其对女性的认识是何等肤浅,其对自我的承诺又是何等的标榜。
草率表现在其根本就没见过尤三姐,仅凭贾琏的一面之词,就答应了婚事。
肤浅表现在其脱口而出的“绝色”之论。没有见面,更无交往,只要漂亮。
标榜表现在其自我夸口说:“大丈夫岂有失信之礼?”
也许,要求一个人格尚未真正走向成熟的少男不草率的确不易,要求那个时代的世家子弟洁身自好,连杯花酒都不喝,或许也太苛刻。但是一个自命清高、萍踪浪迹的男人,在对待感情上至少应该有超越流俗的见识,想不到竟也是“以色论人”“以貌取人”,其和一般浮浪子弟有何区别?
也许,男人重色尚可理解,但在如此重大的诺言上失信于人,就不可原谅了,不管是旧道德还是新道德,轻诺寡信几乎都是致命伤,可恰恰在这一伦理底线上,柳湘莲没有守住。
尤三姐的贞洁、不贞洁是一回事,柳湘莲如何对待尤三姐的贞洁、不贞洁又是一回事。从他对尤三姐的殉情上的表现可以看出,尤三姐差不多等于白死了。因为从其悔意上,并没有看出他对尤三姐的认识有多少深化、有多少升华: 仅仅“刚烈”二字的评价,就对得起尤三姐的殉情了吗?仅仅“流泪”二字的评价,就对得起尤三姐的殉情了吗?可以说,尤三姐的殉情彻底烛照出柳湘莲凡夫俗子的本色,原来那一切所谓的“高冷”都不过是伪装。这一“伪装”,使我突然想起了他的高级票友的身份。也许是长期的客串使其彻底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由于长期扮演戏文中的那些高富帅的公子哥儿、浪子弟儿,就以为自己也就真的成了高冷的公子、浪子,有点像入戏太深的程蝶衣了。
尤三姐爱柳湘莲是真实的,也是真诚的。因为毕竟她认识他,而且他是她的偶像,她是他的粉丝: 那是在舞台上,他衣袂飘飘的身影让她着迷,他慷慨激昂的唱腔让她陶醉,他的一抬手、一顿足都可能让她茶饭不思。于是,她爱上了他,而且这一爱就是好多年,深深地隐藏在心底。虽然她知道希望非常渺茫,然而梦还是要做的,万一实现了呢?
轻诺寡信
柳湘莲爱尤三姐是虚妄的,也是肤浅的。因为毕竟他不认识她,她只不过是他万千粉丝中的一员,只是听别人说她很漂亮而已。于是他就轻信了,也轻诺了,一旦听到些风声之后又犹豫了,依然是连面也没见,又后悔了。
在婚姻上,这个所谓的“冷二郎”未免有点过于贪心了: 既要“绝色”,又要“贞洁”。问题是能拿得起、放得下也行,却又偏偏拿不起、放不下。原来那么酷,那么俊,那么冷,那么风度翩翩的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绝尘少年,竟也是个“银样镴枪头”,无论如何也没能走出他所生存的那个男权社会的藩篱。要求柳湘莲对待尤三姐能超越一点是不过分的,毕竟有榜样在: 想想范蠡与西施,想想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想想红拂与李靖,想想钱谦益与柳如是,想想吴三桂与陈圆圆……
冷面、冷心的“冷二郎”,如果真是那么超凡脱俗的绝尘少年,好像没有理由再要求尤三姐“贞洁”吧?当然,两全更好,但是“绝色”与“贞洁”不能两全的时候呢?“肉体的贞洁”与“灵魂的贞洁”相抵牾呢?现在我们看到了,“冷二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可见他不过是在“扮酷”“装冷”,关键的时候却证明他亦是个肉眼凡胎。这让人想起贝多芬对拿破仑的感叹:“不过一凡夫俗子罢了!”
草率、肤浅,轻诺、寡信,哪还有一点江湖游侠的气质可言?
对未来,他还是草率的。
一次婚姻失败,就让他“觉寒冰侵骨”,于是“掣出那股雄剑来,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便随那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
你相信这样一个没有定性的人,真能在青灯黄卷中度过一生吗?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轻率呢?
一方面是其天性,一方面不能不让人再次回眸他那中落的家道——
那柳湘莲原系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已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第四十七回)
真正的酷不是浓墨重彩装扮的,而是源自深沉的思想的冷峻和深刻;真正的爱更不是听风就是雨的盲从盲信,而是源自一种对灵魂契合的精神伴侣的长期而艰苦的寻觅;真正的君子更不会轻诺寡信、反复无常,而是一诺千金、至死不渝;真正的看破也并不是以出家、不出家为标划的,而是看其到底有没有一种超越的情怀和达观的心态。
柳湘莲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一戳就破的虚幻的偶像派的典型。
《细品红楼小人物》(田崇雪 著)(以“小”人物视角洞察红楼大世界;田崇雪教授打磨多年的精彩讲稿)
来源:东方出版中心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