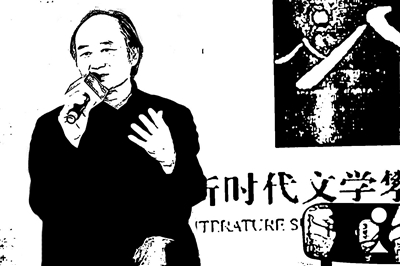时间:1月16日
主持人:欧阳江河(“迁徙计划”策划顾问,诗人,评论家,吕梁文学季文学总监)
对谈嘉宾:梁鸣(电影导演、演员、编剧,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发展中电影计划”入围作品《逍遥游》)
刘亮程(作家,“迁徙计划”推介作品《一个人的村庄》《本巴》)
双雪涛(小说家,“迁徙计划”推荐委员会成员)
王红卫(电影监制,编剧,策划,“迁徙计划”推荐委员会成员)
杨庆祥(诗人、批评家,“迁徙计划”推荐委员会成员)
朱山坡(作家,“迁徙计划” 推介作品《闪电击中自由女神》)
今年的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 备受关注,这是平遥国际电影展联合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联席会议”旗下重点文艺类出版单位,为电影产业推荐具有电影改编潜力的文学作品,为文学作品提供影视化合作与孵化平台,旨在打通文学与影视圈,促进文学与影视领域的融合接轨与产业合作。最终,由王安忆、刘亮程、田耳、林棹、叶弥、笛安、罗日新等作家创作的18部文学作品获得推荐。推荐委员会成员杨庆祥说:“文学和电影是个人的智慧、灵感以及奇思妙想,但其开花的结果却需要大量的分工协作和集体劳动,迁徙计划搭建了一个有效的平台。让更多的业界的力量进入,以此提升业界产业水平。”
1月16日,“迁徙·从文学到影视”论坛举行。
杨庆祥
原创性走到了一个疲惫期
这是一个特别要命的问题
欧阳江河:“迁徙计划”为文学和影视两个领域做了一个衔接,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文学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转变方式,和其他艺术门类衔接。这方面我们一直在探索,因为高质量的、有深度又好看的文学剧本的欠缺,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对电影、文学双方都具有挑战性。
同时,它提出了一种文学创作的可能性、一种影视创作的可能性,两者结合之后,如何产生出一种彗星撞地球的强烈撞击力?今天,我们来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我们把它推向一个更深的困惑、更深的一种可能性。
杨庆祥:不仅仅是剧本,我觉得在21世纪之后的20年以来,整个的原创,无论是思想的原创、文学的原创,还是剧本、电影的原创,都是非常缺失的。原创性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走到了一个疲惫期,这是一个特别要命的问题。我是职业的文学阅读者,一个非职业的电影爱好者,基本上如果有好电影出来,不管多贵都会去看,但是说实话,没有看到特别让我惊艳的电影,非常遗憾。中国比较早期的一些电影,我觉得特别有味道,能够反复给你一些启发。但是这几年,确实没有看到特别让我惊艳的电影,当然文学也是同样如此。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这倒是我们可以来讨论,或者来思考的一个面向。无论是做电影还是做小说,都有一个产业标准。这个产业标准从两个方面界定,一是你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产品,从技术的角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很多电影在技术方面都做得非常好,而且随着现在的技术水平的进展,电影里面的奇观、技术、舞美、音效都非常好,包括演员也挺好的,但是看下去以后总是觉得干巴巴的。
所以说一个好的产品首先是一个技术上的合格品,但是一个技术上的合格品不一定是大师级的作品,也不一定是杰作。这个时候需要思想、人文关怀、灵魂性的东西,这种灵魂性的东西很重要,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能真正完成从一个合格的工业品向一个杰出艺术品的转化,这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黄金时代的电影或者艺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些最好的大脑、最有趣的灵魂,会在一起喝酒、争论、吵架、打架,最后这个东西就出来了。但是最近这些年很奇怪,搞电影的不理搞文学的,搞文学的人太穷了,搞电影的比较有钱,有资本的力量在里面,搞文学的人说,你们挣钱一股臭味,我们是手艺人,我们的精神很高贵。搞诗歌的说你们搞小说的非常世俗,我们非常高洁。大家互相不理。
迁徙是一种流动,思想是需要流动的,不流动就不会有思想,不流动就不会有灵魂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大家都故步自封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就没有办法流动。鲍曼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观点“流动性现代性”,他说现代社会里面有一个趋势,我们讲行业,讲专业,讲圈子,其实就是把一个东西固定下来、让大家彼此隔绝,这会产生一个安全感和幻觉,觉得我在圈子里面做得特别好,大家都很认可。实际上长远看,这种流动性就消失了,真正综合性的大作品、大艺术品,大人物就少了。一个时代是要诞生大人物的,这个大人物不是说有多大的权利、有多少钱,是指他的思考、他的灵魂、他的大脑是那么有趣,所以“迁徙计划”是一个好的开始。
王红卫、双雪涛、梁鸣(从左到右)
电影是跟朋友关系很大的事情
文学是跟自己关系比较大的事情
双雪涛:提到小说改编电影,对于我个人来说,很难找到其中的规律,我自己一直没有想明白。
我特别赞同红卫老师说的,电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经常回忆自己几部小说的改编,得失、成败、具体的细节我当然也会想,但是最多浮现的其实是朋友,是你在跟谁一起做事。一个电影项目的制作时间一般比较长,三年、五年都有可能,过程中有一些人加入了,有一些人离开了,有一些人一直做到最后,这个过程是一段生命。电影是一个跟朋友、跟生命本身关系很大的事情,文学是跟自己关系比较大的事情。
最开始,小说也是因为印刷术的蓬勃发展才发展起来,是呼应着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电影也是根据技术发展而发展,如果文学作为一个基础,配以这么一个新的形式、新的技术,会把有趣的思想和有趣的灵魂传到更多的地方,这可能也是“迁徙计划”的意义。
梁鸣:有时候我在想,文学跟电影之间流动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看电影时会听到有人评论说这个电影还挺有文学性的,或者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会评价说它好有画面感,所以到底是什么在这之间流动?我在改编《逍遥游》的时候,觉得心理描述的部分对于我来讲特别难用影像去呈现,太多的心理活动、感受,好难用画面一一呈现,但是读的时候又有那么多层的感受包裹着你,完全能淋漓尽致地感受,但转化成影像该怎么去弄呢?
情节上相对好说,我们在探讨小说的时候,会看它的人物,首先角色的人物是否写得扎实,还有人物关系的编织是否特别,是否有趣,是否不落俗套。如果人物和人物关系都是很有趣的,其实情节上有时候也不用顾虑特别多,因为人物和人物关系是最重要的。我们转化到影像上关注的是演员的表演,看到的是演员诠释的这个角色,在叙事的电影里是跟着人物走的。
“迁徙计划”让文学和电影互相借鉴
欧阳江河:想请杨庆祥老师再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他对电影的失望,这后面包含的希望是什么?你希望在文学性和电影性的迁移的过程中呈现出怎样的东西?
杨庆祥:这个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说自己没有看过特别好的电影是挺不好的表达,其实是有很多不错的电影,也会自己掏钱去看。
刚才梁导、双雪涛、王(红卫)老师说得特别好,他们跟电影打交道比较多,亲身参与这个行业的制作或实践,所以里面的难度、复杂性,比我了解得更多。
梁导谈到的难度,无论从剧本的角度创造一个电影,还是文学的角度改编一个电影,这里面都非常有难度,包括梁导讲到的心理描写。其实无论是多么快的小说,本质上都是比较慢的,因为文字的间接感,对视觉的要求比较慢;但是无论多么慢的电影都是快的,因为电影的镜头和画面的要求是快,所以这里面的快和慢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小说怎么更快一些,电影怎么更慢一点。
实际上“迁徙计划”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让这两个不同的艺术门类互相能够感知到对方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艺术之间非常微妙的区别,互相借鉴,这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比如说小说,这些年我们明显感觉到小说变得快起来——小说的节奏,叙事的方式变得快起来,其实是从电影那里获得了很多的养分。
欧阳江河(左)和朱山坡
文学是对生活的第一次修改 电影可能是第二次修改
刘亮程:非常荣幸我有长篇小说《本巴》和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两部作品获得了平遥电影展“迁徙计划”的推荐。我想每一个作家可能都有一场电影梦,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可能天生都具有电影性,因为文学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影视制作过程。文学的种子最早是画面的,一幕幕的往事,那些曾经掩入遗忘深处的情感往事、生活的琐碎片段逐渐被一个作家从尘埃中打捞出来,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这就是文学写作的全部过程。只是这样的画面最后成型交给了文字,文字主宰了那个世界,把它接管了过来。
这样的文字完成之后,作为作家,我还是希望原初的感动、我的画面再还原回去,还原到电影中去,让它再度浮现。当然我也知道,这样的还原、这样的改编可能是危险的,可能是相去甚远的,就像文学是对生活的第一次修改,电影可能是第二次修改。
《一个人的村庄》这部作品写的是我的童年,其实我童年很不幸,我8岁时父亲不在了,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但是当我30多岁去回想和书写自己童年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获得了一种权利可以修改生活,把那样一个不幸的童年,修改成像《一个人的村庄》中呈现的这样一种文学世界。作家真是一旦获得一种文字的权利,他就获得了一种类似上帝的、可以让太阳从西边升起的一种能力。当然导演也是。
(本来是)一个不幸的童年,但当我回去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带着阳光回去的。我当时写作的时候似乎就有一种拍电影的感觉,我写得最多的就是村里面的老人上午坐在东墙根晒着早晨的太阳,下午坐在西墙根晒着逐渐远去的夕阳,被太阳晒透的厚厚的土墙上还有阳光的余温。老人旁边坐着一条老狗,人和狗都到了岁月尽头,狗看一眼人,人看一眼狗,就相互知道生命就是这样了,眼下就要过去了。一个白天一结束,村庄的一个时代就很快结束了。但是我依然希望这些曾经打动过我、让我写出过这样一本散文集的那些故事,通过电影再一幕幕地呈现出来,这个愿望不远了,我现在坐在导演旁边了(笑)。
文学的魅力跟电影的魅力有时候有个落差
这个很正常
朱山坡:我是写小说的,写了20年短篇小说,这几年获得大家最喜欢的小说集是《蛋镇电影院》,写我小时候奔赴电影院看电影的感觉,里面有17个关于电影院看电影的故事,这个小说集寄托了我对电影的感情。我本人很喜欢电影,我觉得电影跟文学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特别是小说,是电影的源头活水。中国的小说家值得中国的电影人、特别是导演信任,中国小说家讲述故事的能力非常强,尤其是现在年轻一代的小说家,讲故事的能力、讲故事的成果是值得电影人关注的。
“迁徙计划”是从文学文本迁徙到电影,我觉得非常必要,好的故事要迁徙到银幕上成为电影,讲故事的方式完全发生了变化,可能对小说和故事会有很大的升华和提高,还可以扩大影响力,这是作家希望看到的。我也很愿意我的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虽然有一些电影改得很好,但是也有一些不像我想象中那么满意。就像刚刚杨庆祥老师说的,从文学到影视的迁徙,不单单是故事的迁徙,还有思想的迁徙,特别是灵魂的迁徙。
文学是追求形而上的精神高度、是追求灵魂的,是从世俗中来,到灵魂中去,有升华的部分。而电影有时候会缺乏灵魂的高度,达不到小说家、文学家所期待的高度。这也不能怪导演和电影,有时候文学要表达的确实在电影里面表达不出来,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文学的魅力跟电影的魅力有时候有个落差,这个很正常,这个时候就需要作家跟电影人、导演、编剧有更深入的交流沟通,拥有更高的契合度、更广阔的合作空间,这也是“迁徙计划”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机遇。
刘亮程
电影作为娱乐消费产品
和文化艺术作品的两个属性如何统一
杨庆祥:整体来说因为我不是搞电影的,我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当然我作为观众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因为观众会花钱(买电影票),是买方。某些电影可能有点轻视观众,总觉得观众比较傻,包袱抖得特别多,并且一个包袱出来后,一定要把“1+1等于2”告诉观众,观众看了以后会觉得,我有这么傻吗?我难道不知道吗?
另外,我个人更喜欢复杂的电影,无论是从技术的层面还是思想的层面。思想的复杂性怎么呈现出来,无论对文学还是电影都是一个挑战。现在很多电影、话剧总体感觉都特别闹,前些年都向相声、小品看齐,后来又向脱口秀看齐,特闹,包括人物的台词、动作,太多了。中国有一个传统的审美就是留白,电影、文学其实都是想象的产物,想象的产物就一定要给别人留下想象的空间。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简单的、单纯的,但是又深刻的、复杂的电影。听起来很矛盾,实际上是不矛盾的。
梁鸣:其实电影有娱乐属性和商业属性,有很大一部分观众不愿意在电影院里思考太多,还是想去放松一下。杨老师说得也对,有一些确实是很多电影人需要反思的,不能什么时候都弄得像春节档,老是在过年。
杨庆祥:电影的陪伴属性我是承认的,而且它的娱乐功能确实很重要,我也是工作一天回去特别喜欢找些片子看,但是陪伴的东西有很多,电影的陪伴怎么跟其他的陪伴区别开来?这也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听过有声书或者我很傻的做过别的事都是陪伴,或者消磨时间,为什么去选择电影消磨时间?肯定在选择电影的时候已经有了区分了。电影怎么跟其他的形式区别开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王红卫:电影作为娱乐消费产品和文化艺术作品的两个属性非常难在一部电影里面统一起来,确实有,但是非常少,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分类和分众的形式。杨老师谈的是他、或者是以他为代表的一小撮观众的需求。电影太热闹,包括电影从小品化到脱口秀化,可能都是电影出品人、制片人、导演和编剧回应大众市场(的产物),是观众有这个需求才会出现这样的产品。
另外,我们还是要承认电影的文化属性,这也是那天在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试映会上我提过的,不管是文学还是电影都是有引领责任的,我反对永远不需要引领、永远跟着观众。如果只有那样的片子,一段时间之后观众可能会抛弃这个艺术形式。其实观众是不愿意我要什么你就给我喂什么的,这个引领是文学和艺术存在的意义,这种作用和价值我觉得是永远存在的。
刚刚刘老师说文学以后会慢慢退到影视背后,其实这个是再往前几年的情况,现在我们的情况是这边是短视频,可能会把电影给攻占了;那边会有上来就是几百万字、几千万字的网文,把文学给攻占了,短的东西吃我们(电影),长的东西干掉文学,这些都是在网络时代和流媒体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都不是由作者主导的,全部是由受众主导的。我个人觉得,我们面对网络时代受众需求的变化,会不会产生一些新的艺术形式,和一些新的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供图/PYIFF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