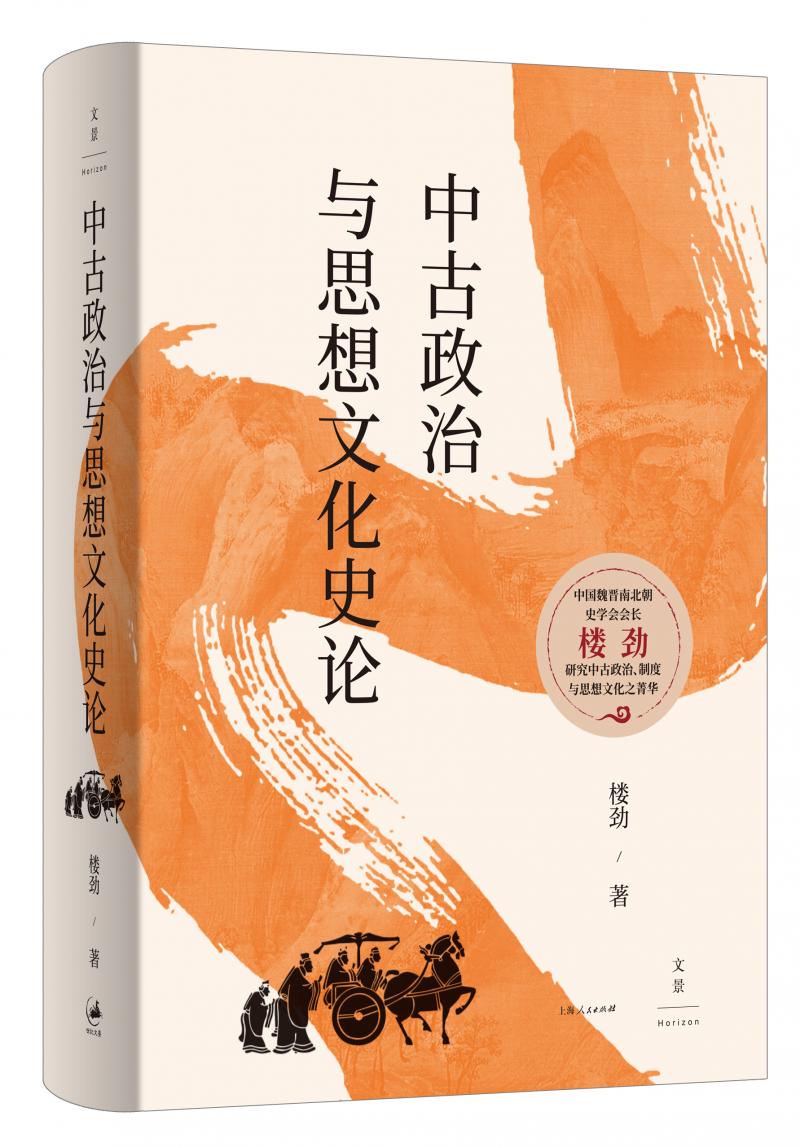在“女医”条这些蕴义特定的文字俱已释迄后,大致可对唐女医之制下两点结论:一是太医署教习的女医多为医官助手,主要是为嫔妃宫女提供贴身的医疗服务。故其各项规定一方面从属于官府各技术部门尤其是太医署选取和培养其所需技术人员的整套制度;另一方面又对其选取条件、安置处所、课程安排、教习方式等项做了诸多调整,以适应培养目标的需要。二是女医之制通体处于特定社会性别观的笼罩之下,并从一个独特角度反映了当时医疗领域的社会性别状态。这不仅集中体现于女医在整套官方医事体系中的卑微身份和附属地位,处处渗透于其习业、执业的全过程,而且也典型地透露了当时在女性身心和智力、女医与男医之别、女性疾患就医等方面的一系列共识或偏见。合此两点而言,即可认为唐令“女医”条的资料价值主要不在医学本身,而在于其中所示医疗社会学范畴的各种状态,包括其具象化为相应的职业规范、习惯和官方制度的态势,尤其是特定政治体制、知识系统和社会性别观对于医疗史和妇女史的深切影响。
最后还须注意的是“女医”条在《医疾令》中的位置。此令先列太医署诸医生选取、教习、课试之法,其末即为“女医”条,后面再继以其他医药行政条文,这样排序既是女医在太医署教习体制中仅处附属地位的反映,又提供了女医之制有可能晚出,是在太医署其他生徒管理条文之后方被附入《医疾令》的线索。由于《医疾令》源头在西晋《泰始令》,其中并有医署设官教习生徒之条 ;《天圣令》所存唐令则出于开元二十五年令 ,但据前面对武周《梁师亮墓志铭》载其“起家任唐朝左春坊别教医生”的分析,女医之制的定型入令恐当不晚于唐初。故若推溯此制之源,其时间范围暂且可框在西晋至唐初之间。
再从西晋往下梳理,《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医博士、助教条原注述晋太医署设助教教习医家子弟,继曰:
宋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至三十年省。后魏有太医博士、助教。隋太医有博士二人,掌医。皇朝武德中,博士一人,助教二人;贞观中,减置一人,又置医师、医工佐之,掌教医生。
据此,无论西晋医署教习是否包括了女医,东晋以来其实际已处于停废状态,至刘宋文帝时一度恢复,十年后罢撤。《宋书》卷八二《周朗传》载周朗在孝武帝登位后上疏论政,其中一条论巫风及医事有云:
针药之术,世寡复修,诊脉之伎,人鲜能达。民因是益征于鬼,遂弃于医,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复半。今太医宜男、女习教,在所应遣吏受业。如此,故当愈于媚神之愚,惩艾腠理之敝矣。
其下文载朗“书奏忤旨,自解去职”,此建议落空。不过周朗请由东晋以来归属门下省的太医教习男、女医生 ,仍可说明当时宫廷和官府既缺男医也需要女医,但医署却无教习之法,民间则巫风盛行而尤其缺乏系统接受过医经、医术训练的男、女医 。至于《唐六典》上引文述西晋以来医学沿革一提刘宋即述后魏,则显然是以此为隋唐医学教习之法的正源,其原因除有鉴于北朝之况外,更是由于南朝医署迄无博士、助教之官 ,也就再未恢复医徒教习之制。在此前提下,梁陈定令虽有《医药疾病》,其中自然不会有生徒教习之制,就更罔论有选取女医习业之法了。
北朝的情况与之相当不同,《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载太和中所定官品,太史、太卜、太医博士皆从七品下,太医、太史助教皆第九品中 ,这类设置本身就表明北朝甚重方术的传统也已体现于其教学活动 。又《魏书》卷八《世宗纪》载永平三年十月辛卯下诏立馆治疗京畿内外疾病者,“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其后文又载延昌元年四月癸未,因肆州地震死伤甚多,诏“生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须之药,就治之”。 故北魏后期医署教习之况虽史载不详 ,但宣武帝诏文所述“分师疗治”及“折伤医”名称,却仍透露了唐《医疾令》中诸医生、医官分科的来源 。再看《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医署原注述其北魏以后沿革之要:
北齐太常寺统太医令、丞。后周有大医下大夫、小医上士。隋太常寺统太医署令、丞,有主药、医师、药园师、按摩、咒禁博士……后周医正有医生三百人,隋太医有生一百二十人,皇朝置四十人。
据此,无论北齐有无医署教习之制 ,但其到周隋实甚兴旺,唐《医疾令》中有关太医署生徒选取、教习各条,即应承此发展而来。
经上梳理可见,若女医之制出现于唐代以前令文的话,那应该不会是在南朝,而是在北魏以来,又以周、隋的可能为大。尽管其事仍因记载阙如而难断定,但北朝既然更重方技,其社会性别状态也因北族的冲击而多元不一 ,女性习业方术的可能自亦较大。即就官方教习而言,《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载石虎居摄赵天王后:
内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宫人星占及马步射,置女太史于灵台,仰观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实。又置女鼓吹羽仪,杂伎工巧,皆与外侔。
这种在宫廷广设诸女伎术官的做法固然可视为一个特例,但北朝民间女医并不像南朝周朗上疏所称的寡鲜,却可证于敦煌莫高窟几幅涉医壁画中的女医图像,这多少也为女医之制的发轫提供了某种佐证。现将有关图像描述于下:
一、时属北周的296窟:其覆斗顶北披东端绘有主题为“施医施药,疗效百姓”的“福田经变”,上有一黑衣妇从后扶抱一裸体患者欹枕其胸前,黑衣妇侧有一浅红衣男子在旁协助,患者左侧有一黑衣男子持勺为其服药,右后侧有一跪坐浅红衣女子持臼捣药。此图之右,则为扶抱患者的夫妇恭送已戴上幞头的持勺男和捣药女骑马离去。
二、隋开皇四年所建302窟:其顶人字披西坡下端绘有同一主题的“福田经变” ,上有一裸体患者卧于席上,两侧各有一红衣男子以双手持定患者左、右手肘,患者肩部左侧有一黑衣男子为之诊疗,患者足后下侧有一跪坐的红衣女子作煎药状。
三、盛唐217窟:其南壁所绘“法华经变”的下端 ,有一贵妇坐于堂内,目视其右侧一妇所抱小儿,堂外有一侍女正引一持杖戴幞头的红衣男医趋向堂前 ,男医侧后有一双手捧盒的白衣女子亦步亦趋。
以上图像中的涉医女子,以往或视为“家属”“侍女”,但其中的捣药、煎药及捧盒女子,画中示其角色与确为家属、侍女者显然不同 ,尤其296窟图右与医者一并骑马离开的女子,及217窟在持杖医者侧后亦步亦趋的持盒白衣女子,其为医者助手的身份呼之欲出,可断其必为当时所认女医形象。需要指出的是,莫高窟北凉、北魏以来诸窟壁画表现的佛经故事,虽有怀胎分娩、盲人复明之类的题材,却要么是渲染其事神异而未有医者出现,要么是虽有医者而无女医图像 。故上列数图,至少应可表明周隋至盛唐女医流行于民间的状态,从官方制度每与民间之事互动的角度,再结合当时医署教习之制的兴旺,当可将之视为女医之制始于周隋确有一定社会基础的证明。由此再据北周武帝始以软脚幞头为百官“常冠”之事 ,并据北周296窟所绘骑马女性医者与盛唐217窟所绘持杖红衣男医皆戴幞头的形象 ,则可进一步推想两者或皆为官身,然则北周以来官府已有女医似非毫无证据可言。综上诸种事态,大致可以认为女医之制或始于北周,并在隋定《医疾令》时附入令篇,置于医署生徒教习诸条之后,唐初以来当又有所调整,即为今见《天圣令 · 医疾令》所存唐令“女医”条的模样。由于《天圣令》各篇之末所存唐令皆标明“右令不行”,故“女医”等条唐末以来应已隳废 ,宋仁宗时修令时遂将之摒出新令 ,至于其后嫔妃宫女即便仍有女医为之服务,也只是一种并不纳入法定教习体制的余绪而已。
(选自楼劲《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世纪文景2023年1月出版,注释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