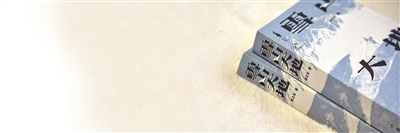著名作家杨志军多年来埋首于文字中,创作出《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大悲原》《藏獒》《伏藏》《西藏的战争》《海底隧道》等一部又一部的大部头。
杨志军自言:“我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这个不可救药,所以,我也比较喜欢写这种气质的作品。”
在青海度过了青春和壮年时代的杨志军,最新作品就是长篇小说《雪山大地》,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该书同时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这不仅仅是我的故事,更是父亲和母亲的故事
《雪山大地》是一部描写高海拔地区变迁史的作品,讲述着父辈们和后代用生命改造环境的故事。杨志军在青海生活了40年,谈及《雪山大地》的创作初衷,他表示,最初就是想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写一户汉族人和草原牧民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相濡以沫的交往。“但一动笔就发现,这不仅仅是我的故事,更是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是所有在青藏高原留下足迹、洒下血汗、度过青春乃至全部人生的父辈们的故事。”
杨志军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讲述说,他的父亲是从洛阳来到西安西北大学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路西进到了西宁,在一家破破烂烂的马车店里开始创办《青海日报》。杨志军的母亲在贫困中求学,成为青藏高原上第一批由国家培养的医生。“后来几乎年年都有西进的人,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建造了草原牧区的第一所学校、第一座医院、第一家商店、第一个公司、第一处定居点、第一座城镇。一个地区从落后到进步的足迹是那样深刻,里面贮满了父辈们的血汗和被时间演绎成荒丘的生命,并在多少年以后开出了艳丽的花朵。”
《雪山大地》就是以杨志军父亲母亲为原型,融合了很多个父亲母亲的故事而写成的。杨志军的笔下,父亲和母亲为草原告别落后蒙昧,走向现代文明与现代化生活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献牺牲。小说的另一线索,是“我”全家人与先后担任公社主任的藏族人角巴、桑杰一家互敬互爱、生死相依、命运与共,结成了亲密的一家人。
在杨志军的语汇里,“父辈们”本身就带有浓浓的诗意,“这种诗意既是浪漫的,也是残酷的,更是迷人而悬念迭出的。”他说,“雪山大地让人面对的全都是人生的大题目和大选择,它代表了生命所能承受的全部考验,也隐藏了人生历程走向荣耀和暗淡的所有转捩点,是命运在无形中的推送和引导。”
之所以小说名为《雪山大地》,杨志军解释是因为“雪山大地”作为藏族人最原始的自然崇拜,指导、规范着他们的生活和行为,再艰难的处境,有了雪山大地的眷顾,也会让他们相信奇迹的发生。草原上的人简单也纯粹,说他们的话,拜他们崇敬的雪山大地,他们就能跟你有过命的交情。在这里,父辈们的故乡概念历来比较模糊,原籍和老家远远没有脚下的土地来得亲切,“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种情怀:愿意为高原付出一切,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虽然几十年来在青海经历了许许多多,但杨志军坦陈写作的触动却是抽象的,全部加起来也就五个字:感恩与敬畏。“我感恩高原,敬畏自然,我对雪山大地情深似海,我希望雪山大地的绵延能成为更多人的体验,希望在我讲述父辈们和同辈们的故事时,能有共情者跟我一起歌哭而行,流连忘返。”
山乡巨变也好,时代巨变也好,都是从吃喝拉撒开始
在杨志军看来,一个人的历史一定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一个人的情感一定是民族情怀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发展一定是时代发展的一部分,“所以,作家关注的是个体,每一个个体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提及《雪山大地》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杨志军表示,他在书中想表现的不仅仅是山乡巨变所带来的景观变化,也不仅仅是收入增加,最关键的是人心的变化,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是精神的变化。
杨志军回忆说,多年前他在牧区采访后写了一篇消息寄给《青海日报》,消息写的是几个牧民卖牛羊,“《青海日报》很重视这个事情,当时我想不到为何这么重视,但是现在看来,这是思想观念转变的开始。在长期习惯中,牧民认为牛和羊就是财富,他们不会卖。可现实是,牧民要依水草而居,他们一年有六次迁徙,在茫茫大草原上一次搬迁不是八公里十公里,而是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这样长距离的搬迁,家里不能有家具、电器,只有帐篷、毡等几样,牦牛一拖就走了,他们有钱的话就买首饰,戴在脖子上、手上,因为便于迁徙。这些首饰虽然给他们带来愉悦感幸福感,但对于生活质量并没有帮助。”
此外,杨志军了解到,上世纪70年代,一些牧民吃喝不愁了寿命还不是很长。“我一直在追究这个事情,后来慢慢了解到,是因为他们的饮食不均衡造成的。他们吃大量的高蛋白、高脂肪食物,像牛羊肉、奶制品,粮食和蔬菜水果吃得少,每天缺乏维生素,营养严重失衡。我在这部小说里一直在写这些,写父亲让他们学会卖东西把财富变成金钱,还写了藏民去超市买东西,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为什么还要写?我就是想强调对于藏民来讲,超市就是一个巨大的通道,一个营养通道,一个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通道。”
杨志军感到欣慰的是,《雪山大地》写出了藏乡的变迁,“山乡巨变让他们的生命变得美好起来,这是我一直想关注的一个问题。这种变化的过程也告诉我,山乡巨变也好,时代巨变也好,都是从吃喝拉撒开始。所以这部作品中,我更多地涉及了衣食住行的问题以及有关衣食住行的生活场景。”
在杨志军看来,一部小说最难写的不是情节的跌宕起伏,不是人物的喜怒哀乐,不是对话、心理、景物、事物,而是那些由不断重复和不断变更的生活场景组成的“生活流”,也就是在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说什么、想什么的过程中,展示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微妙的互动。
所谓诗意的帐篷生活,其实缺乏幸福感
以前的牧民是依水草而居,哪里有水草就往哪里迁徙。但现在随着时代变迁,他们有了定居点,不用再迁徙了。杨志军说以前曾经陪几个朋友去牧区看到一个定居点,虽然房子很漂亮,但朋友们不喜欢,说定居点的房子造得都一样,他们认为在草原上搭帐篷,才是诗意的居住,“我当时就忍不住反驳,我说你那个诗意的居住地里面什么都没有,帐篷中间是灶台,最尊贵的主人是老人,然后这边是客人睡的地方,那边是女人睡的地方,门口是男人睡的地方,所有客人都睡在地毡上。草原人病很多,像肝包虫、胃包虫、风湿性关节炎,为什么呢?因为睡的地毡长年累月,会变得不隔潮。帐篷里面并不卫生,你住帐篷必须清洗,没有河水怎么办?用牛粪擦,牛粪是相对干净的,但是它也有寄生虫。肝包虫、胃包虫这些病都来自和牲畜的密切接触,有寄生虫的传染危险。”
因此,帐篷在杨志军看来毫无诗意,“牧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帐篷里没有电,看不到电视,外面发生什么根本不知道。定居点虽然房子是一样的,但是定居点有煤气,有电,有电视,有冰箱,有自来水。贫穷不可能带给人幸福感,贫穷也不可能带来生命的长寿和高的生活质量。我长期跟牧民打交道,深知从逐水草而居变成定居给牧民带来巨大的好处——现在他们的平均寿命肯定有六七十岁了。”
人的精神一旦低下,社会的扭曲和堕落就会随之而来
杨志军之前的《最后的农民工》曾想叫《雪白》,这本书又叫《雪山大地》,问他何以对“雪”钟情?杨志军表示,雪的喻义是干净,而干净也是“人”的尺度,是他内心的渴望,“有身体的干净、思想的干净、灵魂的干净,但现实的污泥浊水又往往使人希求干净而不得,所以,它已然成了一种做人的理想。”
杨志军表示,《最后的农民工》最初想用《雪白》这个名字,因为“做一个怎样的人”是这部小说要重点表达的。《雪山大地》里的“雪白”,则是一种更贴近生活的描写。杨志军认为雪白的环境里拥有雪白的人,这是一种完美的自然形态,是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完善的体现。“在《雪山大地》里,我追求自然环境和人生境界的统一、视觉影像和人物内心的统一。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一个壮阔而高挺的环境里,生命的格调也因此有了一种对应的呈现,那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爱,是爱的极致,是不掺杂任何私欲和异物的纯粹。”
大家喜欢说青藏高原是净土,但杨志军认为,如果不是带着心灵的素雅去拥吻大地的洁白,净土就将擦肩而过,“真正的净土来自我们的内心,来自‘人’的纯粹,就像《雪山大地》中,父亲编创的小学课文那样:我生地球,仰观宇宙,大地为母,苍天为父,悠悠远古,漫漫前路,人人相亲,物物和睦,山河俊秀,处处温柔,四海五洲,爱爱相守,家国必忧,做人为首……”
对于为何他的创作一向着重于精神层面,杨志军回答说:“精神探讨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稀缺,人的精神一旦低下,社会的扭曲和堕落就会随之而来。文学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在捡来的石头里打磨出珍宝,精神是宝中之宝。”
杨志军曾经在《环湖崩溃》中描写了为爱付出一切的“母马精神”,在《藏獒》中描写了忠义勇善的“藏獒精神”,在《你是我的狂想曲》中写到了拒绝堕落、蔑视诱惑的“田横精神”,如今又在《雪山大地》中描写了干净纯洁的“雪山精神”。在他看来,文学既是精神的产物,更是产生精神的息壤,所有能被他崇拜的先辈作家,一定是精神饱满的作家,是一些能够用自己的言行树起一座座高峰的精神引领者:“老子、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鲁迅是有精神的,苏格拉底、但丁、雨果、托尔斯泰都是有精神的。我的写作就是一种向他们致敬并学习的漫长过程。”
一个作家的理想主义一旦泯灭,他的写作生命就等于垮了一半
《最后的农民工》《你是我的狂想曲》《雪山大地》是杨志军的“理想主义三部曲”,他表示,三部作品在情节和人物上没有任何关联,有的只是思想和情感的一致。《最后的农民工》讲的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对城市的建设和完善,“这种建设和完善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可感的,也是无形的。我想告诉大家,地平线上,插天而立的‘人’,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剪影……”
《你是我的狂想曲》说的是一群音乐人,如何在艰难中创作,也让音乐塑造了大写的“人”。杨志军说:“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人,却依然保持着完美的理想,这是因为不管我们前行的脚步有多快,‘人’的地平线总是跟人保持着原来的距离,而我们依然在毫不懈怠地追求。人这一生从来没有明净天空里的飞翔,只有泥淖中的挣扎,当你裹了一身脏东西破土而出时,你才会发现,多数人因为没有‘人’的翅膀已经变成了泥。”
《雪山大地》写的是父辈和同辈如何让自己的肉体变得高贵,让自己的精神变得富有的故事。“贫困击不碎人的追寻,挫折打不烂人的道德,死亡毁不掉人的信仰,这才叫志士仁人,是一些可以为别人的美好而停止自己心跳的人。我觉得除了爱,一个人不可能再有更靠近‘人’的标准。”
杨志军说自己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不可救药”,虽然有人觉得谈理想主义很可笑,“但是我一直觉得一个作家的理想主义一旦泯灭,他的写作生命就等于垮了一半。如果不坚信理想主义,会辜负读者的期待。此外,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理想,就会成为一个很乏味的人,如果艺术、文学的存在与理想没有关系的话,就等于削弱了历史和文学的力量。”
文学本就是孤独者的自语
很多人说理想主义者是孤独的,问杨志军是否有这种孤独感,他回答说:“理想主义者的孤独是正常存在,理想需要孤独,孤独造就理想。”
但杨志军说自己没有因此有任何不适感,“文学本来就应该是孤独者的自语,何况我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让我觉得理想主义的价值也许就在于它的少量存在和少量拥有。面对繁复杂乱的生活,当你殚精竭虑去提纯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孤独和安静是那么有益,孤独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在任何时代都能获得幸福感的生存方式。孤独算什么?有能力写出自己想写的作品,就是一个作家最大的幸运。”
在青海生活40年,如今在青岛又生活了近30年,杨志军表示,在自己的味觉和视觉里,青岛和青海没什么区别:“它们都是咸涩的,又都是蓝色的。我热爱大自然,几乎是带着本能的冲动把两个地方共同的味道和色彩写进了作品。而它们也像有灵魂的活物一样,用优美而芳香的气质,把我的作品镶嵌在了大地的怀抱里。很难想象,要是没有俯拾皆是的景物描写,要是不存在我对雪山、草原、海洋、天空的感受和朝觐,我的作品会简陋成一种什么样子。”
而对于现在读者阅读口味的变化,杨志军坦陈不知道如何迎合读者去改变自己。“事实上,我的写作变化只来源于自身的需要,也就是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一些根本性的追求是不会改变的。1985年,我发表了中篇小说《大湖断裂》,里面说‘全部生活就是一种怎样做人的选择’;1987年,我发表了长篇小说《环湖崩溃》,揭示了草原生态正在走向崩溃的原因。一个是关于‘人’的思考的开始,一个是关于‘生态’的思考的开始,几十年过去了,这两种思考从来没有改变过,它们几乎贯穿了我的所有作品。”
对于杨志军来说,写作是他的一种表达方式,“未来的写作计划是有的,但不敢说,害怕完不成,变成瞎说。”
供图/小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