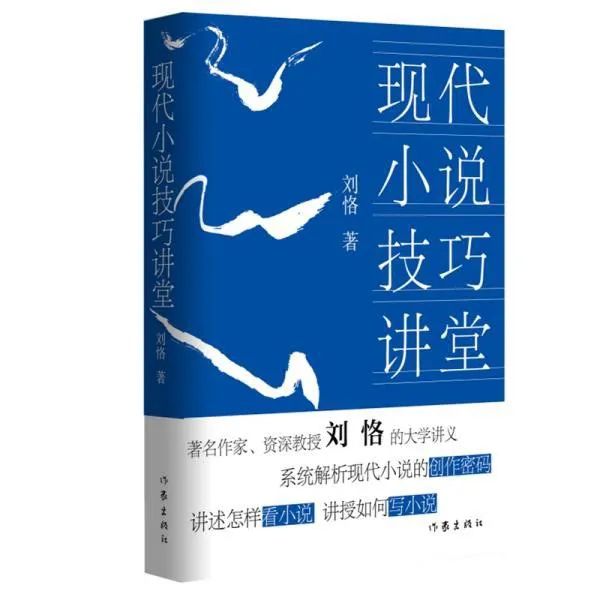1月8日凌晨,先锋小说家、学者刘恪因病医治无效,在湖南岳阳去世,享年70岁。在作家墨白的纪念文章中,他回忆了自己所看到的刘恪的文学人生,“写作是刘恪呈现自己生命的一种形式。在刘恪身上,生活和写作呈现两个状态,就是轻和重。”更有刘恪如何践行着人生格言“真心地帮助别人是一种幸福”。
1月8日早晨7点,海英微信告知刘恪在老家岳阳去世。虽然有所准备,但这消息仍然使我生活的天空充满雾霾,我久久地坐在桌前,不法平息内心的悲痛。刘恪兄,我们不是说好的吗?等过了癸卯年春节去岳阳看你,可你不言一声就走了,这让我们怎么面对?
2022年12月最后一天下午,海燕打电话过来,她从海英那里得知,刘恪在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这消息使我们内心沉重,我们默默地为他祈祷。又过几天,海燕留语音给我,说他从张新赞那里得知,张新赞和高兴他们去岳阳看望刘恪,临别时刘恪苏醒过来。这说明刘恪恢复了意识,远道而来的朋友给了他生命支撑和精神安慰。对于刘恪这样注重情谊的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我们都希望他能转危为安。可是,不幸的消息最终还是来了。我泪眼朦胧地坐在电脑前,把我在2019年写的《我所知道的刘恪先生》一文放到了朋友圈里追忆刘恪,在这篇文章的面前,我写了如下文字:
刘恪先生千古!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刘恪先生今天凌晨4时,在湖南岳阳逝世,终年70岁。
2010年2月27日,也就是庚寅年正月十四,刘恪和苗梅玲来访。中午我约了评论家刘海燕一起相聚,那是他从北京来到河南大学后我们第一次相见,此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兄弟,我们一起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他每次来郑州,我每次到开封都要聚一聚,已经无法记清我们有多少次的交集。2020年初我接到他的电话,感觉他的语言表达出了问题。到了这年的夏季,得知他患了帕金森,等到了9月底我们在郑州河南大学新校区再见时,他的行走和语言表达都有了明显的障碍。
随后,我就约了《河南文学》主编李一给刘恪在2021年第二期《河南文学》做了一期封面人物,同时刊发了沈念《刘恪:水边的“托特”》和杨厚均《诗意迷宫与本土经验——再谈刘恪的先锋小说创作》的两篇文章,内容涉及了刘恪的长篇小说《寡妇船》《蓝色雨季》《城与市》《梦与诗》《城邦语系》与中短篇小说《红帆船》《梦中情人》《墙上鱼耳朵》《空裙子》等,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新时期以来刘恪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
在编辑和出版这期《河南文学》之间,我们多次相约,一直等到2021年的10月27日,他才发短信来说从岳阳回到了郑州。我当天就约了李一去看他,这次出现在我面前的刘恪基本上已经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一切都由女儿料理。这是我和刘恪人生中最后一次相聚。
虽然没有再相聚,但心里一直挂念着他,常有微信来往。最后一次和刘恪兄联系是2022年9月1日,因为在这之前的8月28日我给他短信,辛苦他安排一个学生给他准备《刘恪研究小辑》所需要的内容。《刘恪研究小辑》是《河南评论20家》的内容之一;之前和田中禾、孙先科、李伟昉、刘海燕、李勇、李勇军等人相聚时决定做“21世纪河南作家系列研究工程”,其中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各选20家。在说到评论20家时,大家都最先想到了刘恪,所以才有了上面的微信联系。等到了9月1日他回短信给我时,因为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我已同刘海燕和李海英商定,由海英来做刘恪的研究文章。我就回复告诉他情况,让他安心养病。
李海英是河南尉氏人,曾在河大师承刘恪和耿占春,博士毕业后分去云南大学任教。在和海英联系时,正好耿占春也在昆明,占春也建议由海英也写刘恪。到了2022年10月中旬,海英就把论文发给了我。海英这篇研究文章以《先锋,作为至高虚构的永恒梦想——关于刘恪及其理论专著的贡献》为题,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刘恪在文学理论上的建树。刘恪在河南大学工作的十年间,写下了《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等七部约有350万字的理论著作,另有20多万字的课堂讲义“文学理论关键词”尚未出版。
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
我喜欢刘恪的小说,曾在《莽原》2010年第2期点评过他的短篇小说《墙上的鱼耳朵》,也喜欢他的理论著作,2013年12月间在河南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暨刘恪学术研讨会”上,我作了大致如下的发言:
写作是刘恪呈现自己生命的一种形式。在刘恪身上,生活和写作呈现两个状态,就是轻和重。一星期不下楼,上午做一顿饭,要么白菜要么豆腐,上午吃一顿,下午留一半晚上吃,所以说刘恪把自己的生活看得很轻。相对而言,刘恪的写作是非常丰富的,刘恪用写作呈现了他的生命过程并彰显其意义,这是第一。
第二我觉得从刘恪身上能看出做人的境界,即人格的力量,就是刘恪的写作和为人的同一性,他对写作的真诚和对做人的真诚是相辅相成的。当年刘恪主编《新生界》的时候,鼓励、影响、培养了许多文学爱好者,他以自己的真诚和文学标准来发现文学新人,我们能从中读到从刘恪身上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
第三点是刘恪对中国小说叙事学的贡献。刚才贺绍俊先生提到了夏志清,夏志清改变了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判标准,其实刘恪的这些理论著作,也校正了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的评判标准,这个标准,是指小说叙事学方面的,是文学观念方面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目前的小说评论,多是以社会学意义为标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文学评判都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打转转,根本没有提到小说叙事学的意义上来。所以说,我觉得刘恪的理论著作影响,或者说是校正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评判标准。
据李海英在文章中透露,诗人萧开愚后来劝刘恪该写小说了,他总说等退休了就写一部大小说,初步计划50万字,怎奈世事弄人,他这一创作计划今天已经被他带去了天国。或许,等有一天我们在另一个世界相聚时,他送的见面礼就是一本厚厚的文学巨著。刘恪兄生前无论做文还是做人,都堪称典范,这从他去世后朋友圈里友人对他的怀念就有所窥见:
杨剑敏:惊悉刘恪先生去世。二十多年前,当时我供职的《百花洲》杂志,曾想聘请刘恪先生来担任主编,可惜因故未成。如成,《百花洲》或能成为先锋文学的一方重镇;后来我也不必离开了。
孟庆澍:那批先锋小说家纷纷拿了或准备拿茅奖,只有刘恪孤独地死了。
野莽:刘恪曾为我的长篇《纸厦》写过八千字评论,称其为中国第一部狂欢化小说。在北京,我把他介绍给几位女士的时候,我说他是刘恪,女士们说哦,我说《红帆船》的作者,女士们说哦,我说北大和鲁院研究生班毕业,女士们说哦,我说莫言的同班,女士们说哦,女士中突然站起一位,二目放光:我敬刘老师一杯!
李海英:刘老师给本科生开设过“现代小说技巧”“先锋小说技巧”“美学”“小说写作”课程,给研究生开设“西方文学理论”“文本分析实践”“文学理论关键词”“文化研究”等课程,这后三种是应我要求、专门给我开讲的。我的刘恪老师,以讲师职称退休,我的导师耿占春多方争取,学校才给了副教授待遇。直到办理退休手续,他大约才知道他在文学院拿的是最低档的工资。他从未在意过,这卑微。愤懑的是我,是我们。他终是舍弃了这卑微的生活。
陈瑶:记得前年,他最后一次来诗云书社。他当时住在郑州河大新校区教师家属院,让我上午开车到郑州接他,当时他走路已经很困难了,拄着一根和他差不多高的棍子,一次只能挪动大半个脚。在书店点了外卖吃了饭,陪他买了药,又陪他去趟院里,半个脚半个脚的挪,从东门挪到文学院,办完事把他送到郑州。
那天他还买了一摞书,虽然他说话走路都不方便,但是思维很清晰,还要雄心勃勃的整理《刘恪文集》。这些年他有时在岳阳,有时北京,有时在郑州,几次说去看他,但一直没有成行,那次竟是永别。刘恪老师最后买走一摞书,没有给钱,当时我觉得他忘了,也没好意思说。过年的时候他和我联系,说要给我转钱,还有我开车接送他的包车费用,说他把廊坊的房子卖掉了,有钱!我说不要了,他就在电话那头着急的吼我……
在刘恪的生活里,有着无尽的生活秘密为我们所不知,但是我们知道他真诚的待人。刘恪先生这位从洞庭湖畔走出的“文学巨匠”(河南大学文学院《刘恪教授讣告》语),在他曾经主持过的《江河文学》《新生界》《东京文学》,为青年作家们搭建与世界对话的平台,他在各位不同的场合鼓励、提携青年作家,比如众所周知的“文学湘军五少将”的田耳、沈念、谢宗玉、马笑泉和于怀岸,如今都已成为了卓有成就的小说家。他常常受邀到各地为文学创作班学员授课,不辞辛苦,桃李满天下。
应该说,在刘恪的一生里,影响了许多人,他从受益的后人那里得到报答也理所应当。“真心地帮助别人是一种幸福”这句话是我从《我所知道的刘恪先生》一文中摘录下来的,也是刘恪兄生前的人生格言。刘恪兄生前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想,所有熟悉他的人,都会记住他这句话。
2023年元月10日,于郑州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