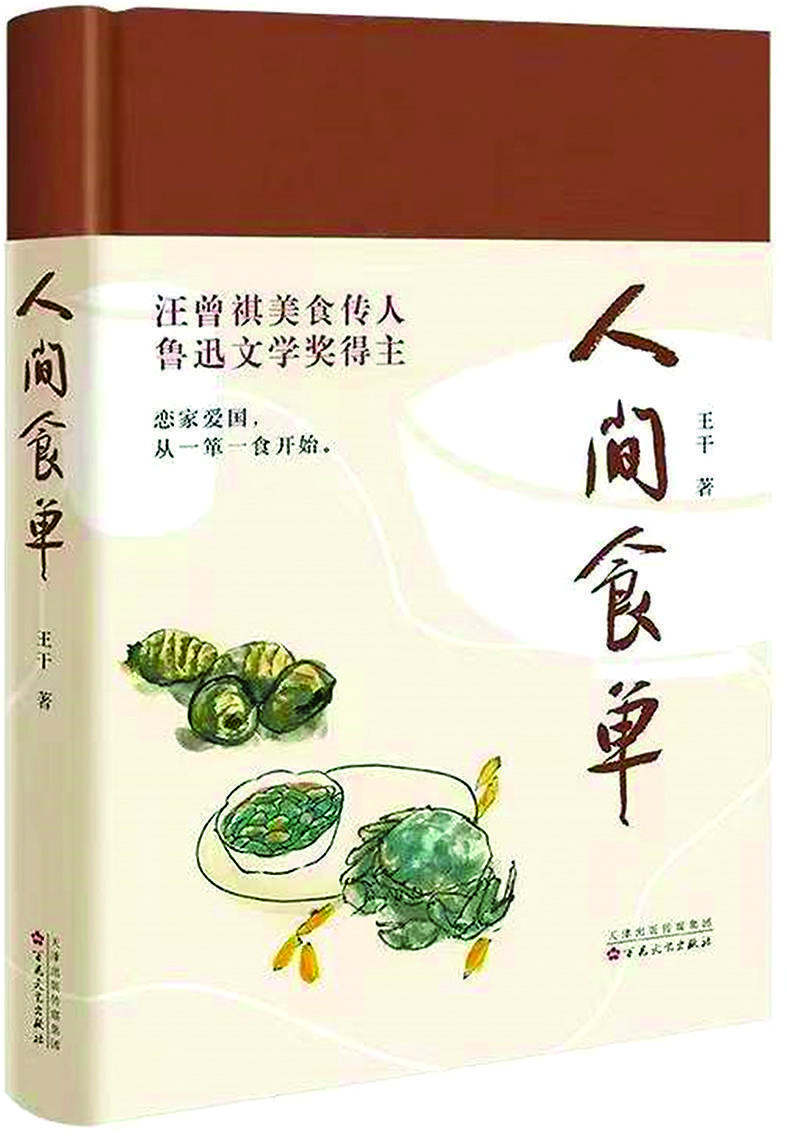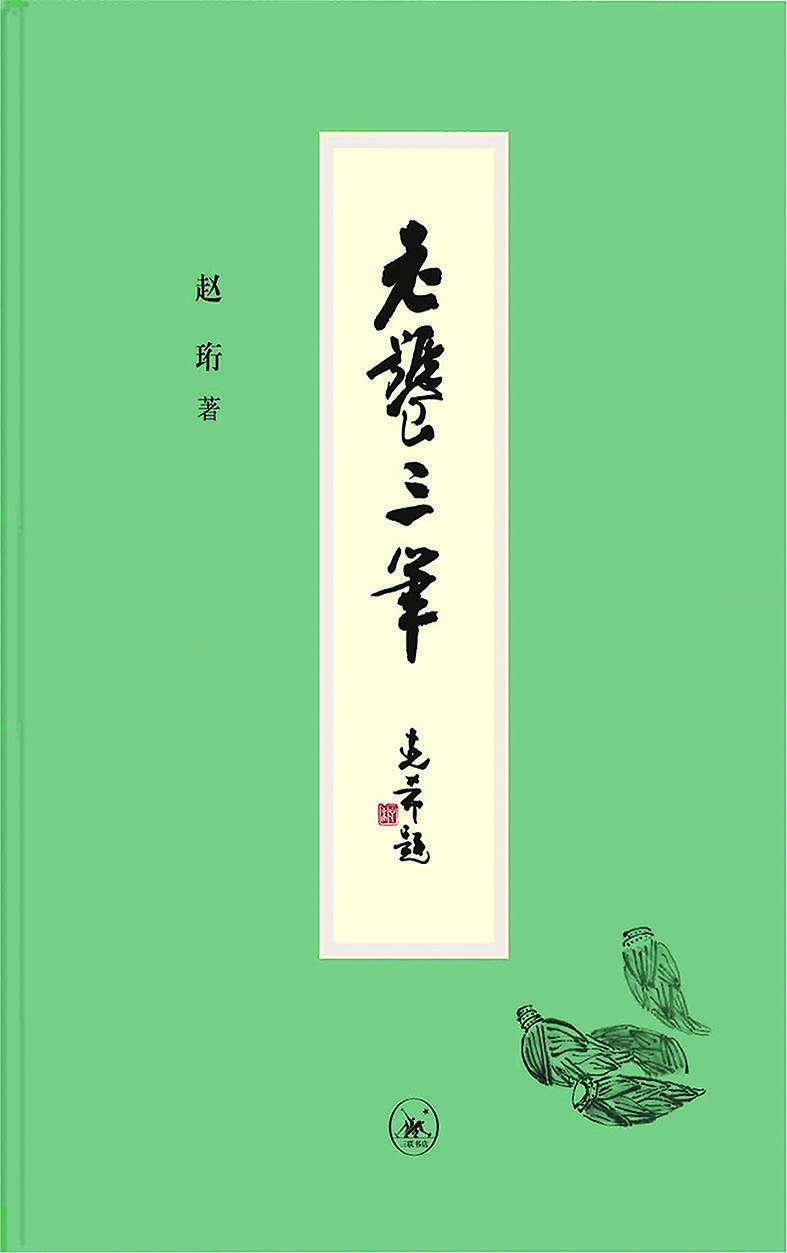文人和美食的“量子纠缠”源于何时,显然已无法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过去1000多年,这种有如知己般的心灵慰藉,就从未间断。且不谈随着时间流转,东坡肉、太白鸭、五柳鱼这些文豪自创的美食都已走进寻常巷陌,就说如今时常被吃客们挂在嘴边自嘲的“老饕”一词,其首创者竟然就是“吃货”苏轼。至于从古到今将“吃”上升到学术高度的食谱著作,据汪曾祺先生考证,也“大多都是学人的手笔”。正如前些年有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语所说:“没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借助于文人的刁钻评介、洒脱轶事,更多美食走出深闺,为人追捧;而各类美食佳肴也反哺了代代文人,一时间洛阳纸贵的美食随笔,将作家从单一刻板的文人形象中剥离开来,展示了他们亲和多元的世俗风骨。
善食者,必有邻
评论家王干的《人间食单》,文如其名,写的自然是四方美食。但穿过林林总总的特色美味,书中还有一位绕不过去的灵魂人物,那就是作家汪曾祺。《人间食单》以汪曾祺之子汪朗的序言打头,以一篇《梦见汪曾祺先生复活》的后记收尾,中间又辑录了记叙汪曾祺美食往事的《“美食家”汪曾祺》《赤子其人赤子其文》等随笔,捡拾了诸如“周末节假日隔三差五地到老头(汪曾祺)家蹭饭”等交往经历,脉络清晰地展现了王干的“美食师门”,用他在书中的话来说就是:“我是汪先生的追随者、模仿者、研究者。”
不仅是结构布局上的“汪味”,《人间食单》对汪曾祺的致敬,可谓是融入肌理的。在《里下河食单·鱼鳔花生》中,王干讲到口腹之物的创新,就会情不自禁联想到汪曾祺发明的“油条揣斩肉”;在《吃相和食相》中,王干谈及梁实秋和汪曾祺的美食文章,自然而然地认为汪曾祺高出一筹,揄扬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参与感”;至于在《里下河食单·慈菇》等文中,顺着相同的叙述对象,提及汪曾祺写过的《咸菜茨菇汤》,就更是意料之中了。
除了师承的脉络,王干的《人间食单》还写到了不少文坛上的“同好者”,有一篇题为《“贪吃蟹”谢冕》的随笔,即使面对比自己年长近30岁的长者,王干仍然还是那副“玩世不恭”的语腔语调,文中“泄密”当时就已经80多岁的谢老一口气连吞17只生蚝、22个冰淇淋,“称赞”谢老是北大连夺写作量、运动量、酒量、饭量“四个第一”的知名教授。
谢冕的满腹经纶为学界熟知,所谓的“贪吃”又被王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于是《觅食记》的著述和面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有趣的是,《觅食记》请来的后记作者竟然就是王干,而王干又在后记中透露汪曾祺和谢冕原本就是好友,京城的“文人美食圈子”看似各有版图,但又因为相知相惜,融合在了一起。既然以“贪吃”闻名,谢冕笔下的文人吃客也无一不是大快朵颐的主儿,特别是在《馅饼记俗》一文中,谢冕就自爆连续多年组织“谢饼大赛”,“比赛谁吃得多”,最终,连“一贯严于饮食”的洪子诚都连吞六只,荣获“新秀奖”;北大前校长周其凤也“闻风报名”,却因食量过小而被清除出赛,令人不禁捧腹。
学者赵珩的《老饕三笔》,承接了《老饕漫笔》《老饕续笔》的一贯风格,温和平静、娓娓道来。虽然同是将一群志同道合的吃客引入文中,但与谢冕、王干信手拈来的幽默劲儿和其笔下风趣的“老小孩们”不同,赵珩更多是以仰视的尊崇视角,讲述那些曾经有过交往、如今已经离世的“老先生们”,说是书写美食,其实更是怀念旧人。在谢冕的《觅食记》中,饭桌上的“交锋”时有发生,而他本人就因为“扬州狮子头是否应放荸荠丁”而多次与叶橹激烈辩论;但在《老饕三笔》中,启功、朱家溍、王世襄、周绍良等老先生,“虽然都精于饮食之道,但绝对不会点评桌上的饭菜”,最多只在餐桌上回味些过往的饮食经历。赵珩称赞老先生们“描述之精到,令人如临其境,于是桌上的出品也就显得黯然失色了”,这大概就是不同文人的不同趣味吧,无论是豪放有如谢冕、王干,还是含蓄之于赵珩,事实上都深谙生活之道,堪称可爱之至。
始于南,吃在北
想当年,“吃货文人”的祖师爷苏轼,就是一路遭遇贬谪、一路研发美食,而被冠以“美食家”头衔的汪曾祺,也是无论身在高邮、昆明还是北京,都能神速融入当地美食,留下了数量众多的饕餮文章。不约而同的是,无论谢冕、赵珩还是王干,虽然如今都定居北京,浸润着独特的京城美食文化,但其“美食素养”的初训之地又都是南方。
在《老饕三笔》中,赵珩多次提及“我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是几代女主人都是南方人”“我的祖母和母亲都是南方人的生活习惯”。也正因为此,当他在《清粥小菜》中讲起北方人的吃粥配菜时,印象里却满是诸如福建的肉松、上海的黄泥螺、苏州的虾子鲞鱼、兴化的醉蟹这些典型的南方吃食。与赵珩祖母同乡的汪曾祺,在《四方食事》中就曾经对虾子和醉蟹极尽赞美,称赞前者“鲜得连眉毛都掉了”,后者则是“天下第一美味”;王干的《里下河食单·醉蟹醉虾醉泥螺》,也同样写到醉蟹和黄泥螺。与赵珩爬梳历史传承和追寻少年记忆不同,王干更多是以本乡人的近水楼台,展现了从选材到清洗、从制作到品尝的全过程。如同汪曾祺一样,王干的随笔也弥散着浓厚的人文情怀,就比如他讲里下河人洗刷螃蟹,“用鬃毛刷子刷,不用钢丝刷子”,是因为“螃蟹会疼”;又比如他说里下河自古以来称香菜为“盐须”,取的就是香菜学名“芫荽”的同音,印证了当地深扎民间的古代文化的影响。
出生北京或是寓居北京多年,谢冕、赵珩和王干对北京吃食的偏爱也溢于言表,正如谢冕在《觅食记》中所取的一篇文章标题:“这城市已融入我的生命”。《觅食记》中的《燕都五记》一辑,收录了五篇与北京相关的随笔,撇去打头的《这城市已融入我的生命》,另外三篇记叙的都是坐落在北京的西餐厅、日料店、湘菜馆,另外就只有《那一碗卤煮火烧》写的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小吃,至于炒肝、面茶、灌肠等,都只在《燕都小吃记》中以百字篇幅概而论之。赵珩在《老饕三笔》中也描述了记忆里的几样冬令小菜,比如“旧时很普通”的冲菜,“今天在北京几乎看不到了”;又如“北京冬季家庭餐桌上”的辣菜,“已经有六十年没有吃过了”。谢冕、赵珩都没有开门见山地讲明,但在时光荏苒和岁月流转中,“很多原有的生活情趣和习惯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那些外来的饮食文化,正在蚕食着传统的饮食体系,也在冲刷着过往的饮食记忆。
《觅食记》以《面食八记》开篇,用全书1/4左右的篇幅,记叙了饺子、面条、馄饨等最为常见的面食,如此醒目和高标,恰恰体现了重视,用谢冕的话来说就是:“我在北方吃了这么多年北方的饭,我感谢北方的大地、父老乡亲让我享受到面食。”值得玩味的是,虽说“南方重米、北方重面”,面食的“根系”始终在北方,但谢冕每写一种面食都涉笔南北对比,比如包子,“北方口重,近咸;南方口轻,偏甜”;比如春饼,在北方“总带着壮阔平原的苍茫之气”,在南方“当然拥有了南国软糯的风格”等。除此之外,谢冕还饶有兴趣地把面食进行了“性别划分”,称烧麦和馄饨是“女性的”、馒头是“男性的”,真可谓吃出了生活韵味、吃出了人生情趣。
旧食事,新况味
在《老饕三笔》腰封的最显眼位置,写着一句“饮馔小文章,人生大况味”的推荐语。如同商量好的一般,无论《老饕三笔》,还是《人间食单》或《觅食记》,都没有把山珍海味、八珍玉食作为品鉴对象,而是透过那些最家常、最普通的百姓吃食,展示着最亲切、最世俗的人生况味。
《人间食单》写的是源自土地和河流的家乡味道。对于王干来说,能与远去的家乡味道相关联的,自然也是充盈着特定时代气息的尘封记忆,这其中酸甜皆有、悲欣交集。比如王干写到螺蛳,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妻子怀孕时想吃螺蛳,自己便在大冬天跑去湖边摸了几颗,请小饭店加工做汤,妻子“喝得很开心”;比如写到秧草,他回忆起过去炒秧草时都要倒上小半碗菜籽油,但又担心锅上沾油父母会责怪,没想到秧草耗油,锅像“水洗过一样”;又比如写到神仙汤,他联想到神仙汤的命名,称乡民面对一碗最普通的“酱油汤”,却“做出高大上的范儿”,展示了“面对苦难和贫困时的乐观和通达”。王干透过“食物”所写的“食事”,让人洞见了犹如晏殊笔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相叠加的复杂情绪,我们很难将王干所叙的旧事归纳成单纯的“苦”和“乐”,但正是这种含混难辨的状态,才更加贴合本真的生活原态。《老饕三笔》也是如此,书中《刨冰》一文就写了20世纪30年代初赵珩家里“买过一个美国出产的电冰箱”,后来因为其父每天“偷吃”冷食,冰箱就给卖了;直到1980年代,家里才再次购置冰箱,赵氏父子开心地将放置冰箱的小厅称为“饮冰室”。赵珩大户出身所造就的独特经历,自然不是绝大多数孩子所能感知和企及的,但撇去具有个性特征的具体事件,那些附着于人类最基本追求上的情感因子,却毫无疑问是互联和共通的。
《孟子》讲,“食色,性也”;《汉书》讲,“民以食为天”。食物在文人的记述中如此重要,想必不仅仅因为它喂饱了口腹,养育了生命,当然还因为那些与“物质需求”须臾不分的“精神需求”,比如某种丰富的感情和过往的经历——复杂而厚重、绵延而深长。
文/易扬
来源/文汇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