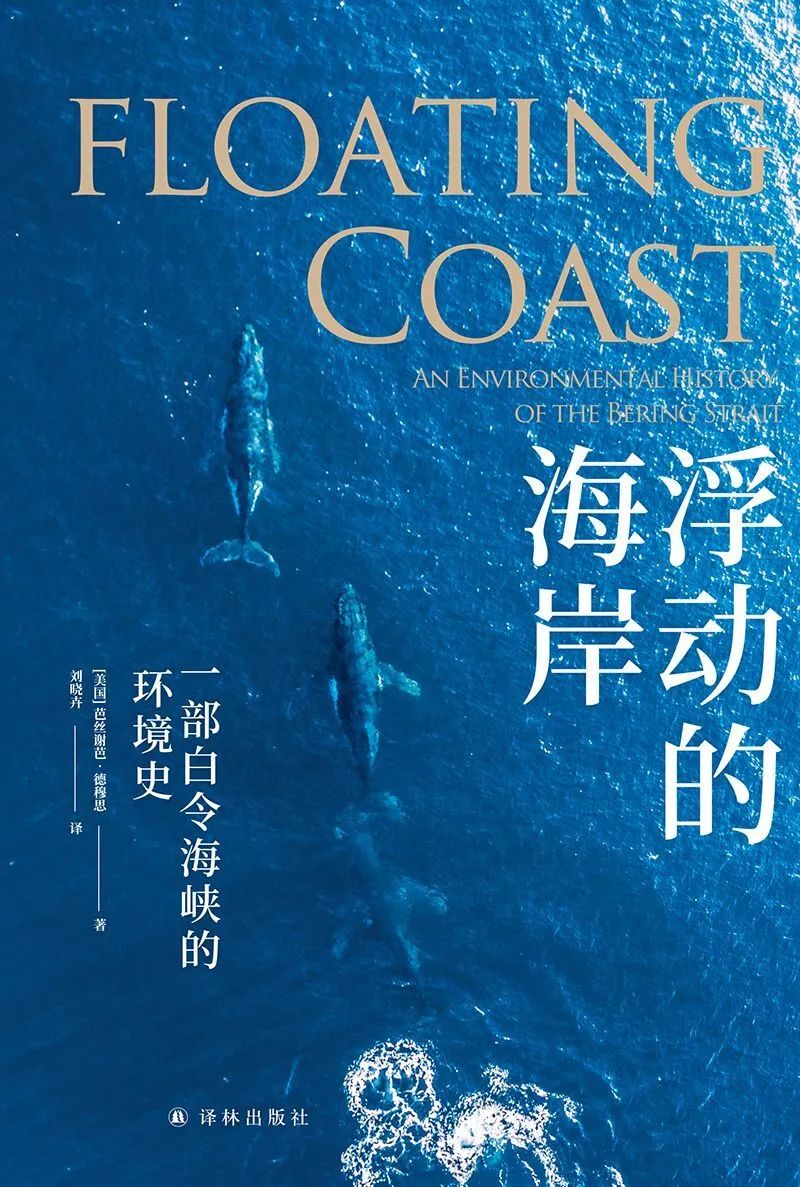自19世纪以来,人类在白令陆桥这片极北之地开启了一场极具现代意识形态的试验,在白令海峡——从俄罗斯到加拿大的北极陆地和海域,人类的生活与自然相融,也给自然带了破坏。
作家芭丝谢芭·德穆思根据自己与该地区原住民一起生活与采访的经历,并结合丰富的档案资料,写出了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浮动的海岸》,展现了在这一有限的空间中所发生的社会、环境的冲突。作者通过自然界的透镜,为人类历史的书写提供了一个新鲜而富有远见的视角。它是对现代化进程在海洋、陆地以及地下所造成破坏的诗意沉思,也是一则关于我们所创造的世界的寓言。
作品选读
18世纪末的某一天,一头弓头鲸宝宝出生了。时值深冬,数月以来太阳低照,温度也很低,使得白令海远至南部的海面也结上了冰。鲸鱼妈妈找到浮冰上一块开阔的空间用以分娩。在倒转的蓝色晶莹的冰层间有一块是空心的,灰白色的宝宝被鲸鱼妈妈放在上面,呼吸了它的第一口空气。沿着这块浮冰薄薄的边缘,其他的弓头鲸妈妈也产下了它们的宝宝。伴随着一股血流,鲸鱼妈妈安静地产下了宝宝,小鲸鱼游入了海中,这片海是两万多头鲸鱼的家园。
在春日暖阳下,白令海表面的冰层向北漂移。鲸群也跟随着冰层向北迁徙,穿过了白令海峡,鲸鱼宝宝一会儿自己游,一会儿趴在妈妈的背上休息。海洋里不时有浮冰融化成水,它们与其他小弓头鲸群相会合,头鲸一路上吐出串串水泡,引领着鲸群。到了6月,鲸鱼妈妈、鲸鱼宝宝和它们的鲸群,一起向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的波弗特海游去,其穿行的脊背标示着海冰的下缘。在没有夜晚的漫长慵懒的日子里,鲸鱼妈妈给宝宝喂食,宝宝嬉戏玩耍,有时短暂地游散开去,然后成环形向前游。夏日渐去,进入9月和10月,鲸鱼又一次向西游入楚科奇海,鲸鱼宝宝游动时抓紧妈妈的鳍。初冬的寒冷黑暗使浮冰加厚了很多,海洋中的哺乳动物有缺氧而呼吸困难的危险,这时候鲸鱼会游向南方。此时,鲸鱼宝宝已经出生半年多了,它更加勇敢,能够在更深的地方潜水,在水面呼吸的时间也更长了。
从海面上看,白令海显得空旷苍凉——夏季蓝灰色的海面不时会有风暴,不见太阳的冬日里,海上覆盖的是厚厚的冰层。然而,白令海峡是世界深海环流的终点。源于北大西洋的水流在几个世纪后到达白令海,在此汇集了大江大河冲刷而来的营养物质。在海峡处,两个大陆向彼此靠拢,由于风和海底地形,产生了涡流。温暖的海水和冰冷的海水汇流,将铁、氮、磷等元素带到海洋表层。在海洋表面,这些元素遇到了夏日充足的太阳能,遇到了大气中的碳元素,形成了有机生命体。海水接触了空气,加上太阳的照射,二百多种光合浮游生物成形了。这些浮游生物和藻类是白令海最原始的生命形式。亿万的浮游生物和藻类就这样在这片世界上最为丰饶的海洋生态系统安家了。
浮游生物所做的事情是所有生命体都会做的最基本的事情——不断繁殖。它们不断地将太阳光转化为淀粉组织,使海洋充满能量,这些卡路里需要供养三百多种脂肪丰厚、成群成堆的浮游动物,它们形色各异,从小虾、仔稚鱼到神话的缩影——水螅、触角怪以及由体刺、液囊和胶状组织构成的生物。鲸鱼的任务是把这些分散的能量聚集起来,以此供养其上百吨的巨大身体。嘴巴是它们的工具,它们有着和小船一样长的下巴和薄板状的胡须,它们的胡须比牙齿还多,进食时能够帮助它们从水中过滤出来磷虾。在浮游生物密集的地区,鲸鱼能在六周时间吃下去一个季度需要的食物。弓头鲸妈妈也就是这样用十四个月的时间在体内孕育出一个一吨重的宝宝。宝宝出生后,妈妈还要劳累一年多,捕食海洋生物,产出滋养宝宝的奶水。鲸鱼无不如此。在二百多年前,鲸鱼吃掉了白令海里一半的初级生物。
正是因为汲取了海洋中的能量,鲸鱼具有了自己的力量。弓头鲸在海洋世界里能做好多事情,其中之一便是和其他鲸鱼共同生活在一起。即使独自遨游时,它们的歌声也时而轻快、时而婉转、时而低沉,有时刺耳如咯咯吱吱的铰链作声,有时是低沉的轰隆声,有时如鸟鸣一样高昂。当它们发现成群的磷虾时,它们会唱歌示意其他鲸鱼,一小群鲸鱼会像大雁一样形成V字队形,它们一边向前游,一边张开大嘴捕捉成群的桡脚类动物。它们的语言只有自己同类能明白,其他物种是无法理解的。
能够跨越物种分野的是能量。弓头鲸也用它们的肉体供养着其他生物。一些小鲸鱼宝宝成为虎鲸的口中之物。一些鲸鱼也成为人类的食材。每磅弓头鲸的肉比任何其他北极陆地或海洋的物种所含的卡路里都要高。连一头一岁的小弓头鲸都够一个村庄吃半年的。尤皮克人、因纽皮亚特人以及沿岸的楚科奇人是最早捕猎小鲸鱼的人。
对鲸鱼的捕猎一直存在着。弓头鲸能活到二百多岁,当这头鲸鱼宝宝出生时,美国还没有购买路易斯安那州,沙皇俄国也未曾拥有阿拉斯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刚刚问世几十年,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将在五十多年后出版。在小鲸鱼的一生中,它将见证人类如何梦想乌托邦的到来,如何发展核能招来灾祸,人类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性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和技术力量来重塑世界。
小鲸鱼能幸存下来是令人惊叹的,并不只是因为二百年对于哺乳动物的生存来讲确实很长。鲸鱼是将工业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吸引至白令陆桥的重要因素。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人类对能量的控制利用。商业捕鲸船就是其中的先锋军,船上所载的未必是革命者,而是意图将鲸鱼的躯体变为商品来获取利益的人们。他们杀戮鲸鱼,获取利润,是基于市场在不断增长的预期。在他们到来之前,这里的鲸鱼不是用来贩卖的,而是被尤皮克人、因纽皮亚特人和楚科奇人看作生灵。这些人也捕猎鲸鱼,但是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有转世轮回,万物难以久长。在商业捕鲸船出现后的几年中,鲸鱼自己也认识到了美国船只的危险,并学会了一些行为来躲避这些捕鲸船,以对抗商业对它们的渴求。
1852年的9月底,两个捕鲸团队在楚科奇东北海岸相遇了。一对白令本地的捕猎者在他们帐篷附近的海边搜寻时,发现了三十三个衣衫褴褛的男人跨过苔原向东南方向缓缓前行。一开始,本地捕猎者并没有接近这些人。他们人数众多,而且语言也不通。然而,北极的绝望境地超越了语言。船员们打捞的物资——饼干、朗姆酒、糖浆、面粉、宠物猪的残粮和临时帐篷——不足以让他们熬过已从群山之中呼啸而来的冬季。本地捕猎者经过观察和思考,选择了怜悯。
本地捕猎者对外来者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们在其冬季村庄的海象皮帐篷中分成不同家庭。俄国探险者谢苗·德兹涅夫曾在1648年路过此地。八年后,维图斯·白令率领他的队伍在辛哈克沿岸登陆。詹姆斯·库克和约瑟夫·比林斯在18世纪末带着大英帝国的重托探索了这片海峡。分别由奥托·冯·科策布和米哈伊尔·瓦西列夫率领的两支俄国队伍在19世纪初来到这里。哥萨克商贾在更远的西边的奥斯特罗夫诺聚集点做着生意。在过去的几个夏季里,更多的船只经过这片海岸,他们的出现就好像海市蜃楼一样神奇。但是,这些遭遇了海难的水手面色苍白、行动缓慢,他们既不想与本地人开战,也不想做交易。他们蹲坐在自己的冬季帐篷里,行动古怪。每天清晨,他们都会刮胡子。他们不喜欢本地人有着狂野手势的仪式活动。他们的歌声很滑稽。村里的女人需要帮他们缝皮衣,教他们如何穿皮衣。他们带来的糖浆和饼干很好吃,但是快不够了。村民们给他们提供了住所和衣服,还把村庄里的食物分给他们吃,这食物便是鲸鱼肉。
这些人是遭遇海难的“市民”号的幸存者。“市民”号从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出发,赶着第五个商业捕鲸季而来。对招待他们的村民,船员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船长托马斯·诺顿后来这样描述村民:“当我们孤立无援、处境艰难时,他们出乎意料地给予我们很多同情和帮助,这让我们始料未及。”但是,感激之情也不能让这些船员喜欢上鲸鱼的味道。美国船员难以忍受滑滑的且嚼不烂的肉,特别是当生吃的时候,“即使时间长了也还是无法适应这讨厌的东西”。就像他不会与村民们分享他对洗浴、性、所有权、衣服和宗教的看法一样,诺顿船长没有告诉村民们他对鲸鱼肉的反感。诺顿和他的船员们在村民的住所度过了冬日幽暗的日子,透过海豹油灯冒出的烟雾,他们相互审视着对方,由此也开始了一段博弈,博弈的中心就是,白令人的生活应受何种价值观的引导。
从新英格兰来的捕鲸者与白令本地的捕鲸者价值观相异,并不是因为他们付出的劳动不同,他们都是靠捕杀鲸鱼为生。他们的差异在于对以下几个基本问题的看法不同:什么是人?什么是鲸鱼?鲸鱼的价值在哪里?未来会怎样?诺顿将鲸鱼看作供养村民们的“食材”,但对其他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鲸鱼的语言。
栖身于自己帐篷里的诺顿,也不知道在白令陆桥生活要面对不断的变化。某一年,大雁群没有来到它们经常栖息的湖里。某个冬天,风暴潮将海洋上的冰块卷起,把它们带入几百英尺外的内陆,所经之处一切尽毁。某一时刻,一个蹲在冰面上等海豹上浮喘气的猎人却意外地遇到了北极熊。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中生活,尤皮克人、因纽皮亚特人和楚科奇人认为,世界是没有固定形态的,鲜有东西能一成不变,但是大多数东西都有灵魂。就像未来可能被突然侵袭陆地的海洋冰块改变一样,灵魂可以改变他们生活的土地。萨满可以变成鲸鱼,再变成人;人最开始可以是一头海象,然后慢慢长成一个男孩;一个强大的咒语可以让人在五天里变为一只北极熊;驯鹿可以有人类的面孔。人和其他事物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土地和海洋是鲜活地存在着的,有感觉和判断力,也会一时兴起做出危险的事情。在这个充满各种意志的世界里,生存依赖于相互合作。
弓头鲸和人类的合作需要经历一种特殊的变化,它们需要奉献出生命。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因纽皮亚特人阿萨特查克在八十年后说:“鲸鱼从自己的国度观察着人们。鲸鱼会说,‘我们游向照顾穷人和老人的人们,我们把自己的肉身奉献给他们’。”它们会根据捕猎者的道德品行以及在仪式上对鲸鱼的重视来决定是否献身。女人们会通过一些安静的仪式来和鲸鱼对话,仪式上有魔力的萨满的舌头会变成鲸鱼的尾巴。在斯乌卡克,尤皮克人会把肉带到海里,一边喂给一直用身体供养人类的弓头鲸,一边低声歌唱。倘若没有这些仪式,鲸鱼会告诉彼此,人类在道德上和行为上都不足以让它们为之献身。它们不愿为不值得的人而死,它们宁愿留在自己的国度。
如果鲸鱼离开了自己的国度,它们会在春天游弋于阿拉斯加附近,春秋季节活动于楚科奇海滩和岬角附近,一些楚科奇的村民在夏天也会捕猎灰鲸。在鲸鱼出没的季节,船员们准备好能装载六到八个人的海象皮小船,小船漂荡在冰冷的海上。每条船上都有一位船长,这位船长一般和他的妻子一样,能够和鲸鱼进行灵魂上的沟通,同时还具有熟练的捕鲸技巧。他还得确保鱼叉、绳子、浮标及鱼枪等都是干净洁白的,那是鲸鱼们最喜欢的颜色。然后,船员们开始在冰的边缘观察鲸鱼。有人需要一直盯着水面,以便发现突然露出水面的黑色脊背。一队人可能会观察几周的时间。他们不但不能点火,也不能多说话。每个船员都穿着崭新的浅色衣服,这样水下面的鲸鱼就会以为看到的是天空和冰面。在斯乌卡克,女人们送丈夫们去海里捕猎时,会祈祷“猎手们就像透明人一般,人过不留影”。
《浮动的海岸》芭丝谢芭·德穆思/著;刘晓卉/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5月版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