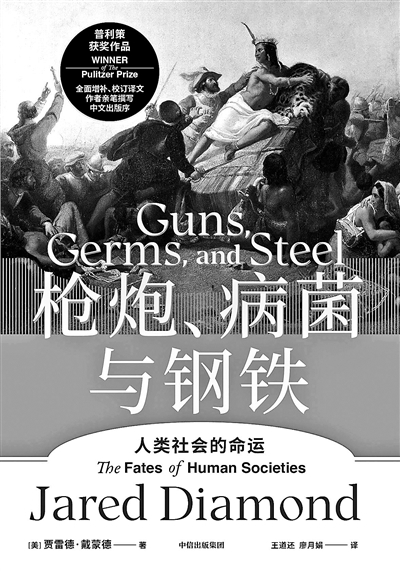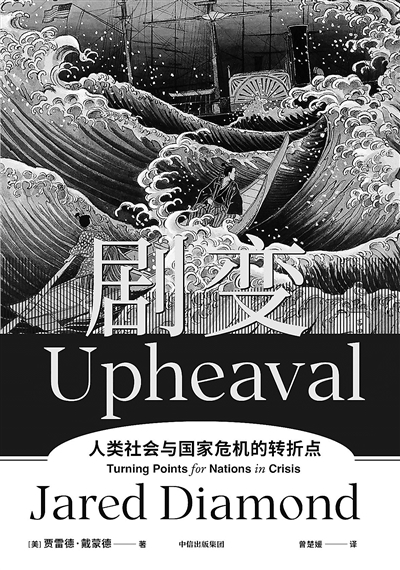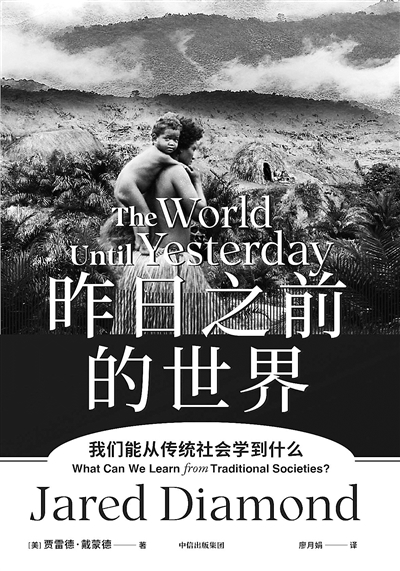时间:2022年4月21日晚7点
嘉宾:贾雷德·戴蒙德 博物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
项飙 人类学家,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主持:邱昱 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
主办:中信出版集团
贾雷德·戴蒙德教授“人类史”系列作品,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昨日之前的世界》《剧变》等,2022年1月由中信出版集团推出新版,讨论关于人之本性、进化与征服、环境与社会、传统与现代、危机与未来的诸多议题,力图勾勒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逻辑和轨迹。4月21日晚,贾雷德·戴蒙德教授与项飙教授以“人类社会如何走到今天?又将去向何处?”为主题,结合戴蒙德系列作品的全新版本,回望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探讨现代社会所面对的危机与书写历史、社会的意义。
一个世界知名的胆囊领域的专家,为什么年过50了突然决定写书?
主持人:今晚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两位国际知名学者——贾雷德·戴蒙德教授,他以《枪炮、病菌与钢铁》等一系列作品,邀请我们从独特的视角重新理解和阅读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项飙老师是中国当今最具国际声誉的人类学学者之一,长期关注国际与国内的移民、劳工和社会问题,其人类学专著《全球“猎身”》曾获国际人类学界久负盛名的安东尼利兹奖,他也十分关注中国、印度与第三世界的社会议题,并非常积极地参与中国社会的公共讨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讨论人类文明的轨迹,传统与现代,危机与未来等一系列议题。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开始——是什么驱使戴蒙德教授在一开始去做这个异常艰巨宏大的任务,书写关于人类历史的书,又是什么支撑你在几十年里一本又一本写下去呢?
戴蒙德:对我来说,我不觉得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相反,那是一种乐趣。
从我3岁开始,我那当老师的母亲就教我识字阅读,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列举国家、河流、动物。我一直对语言感兴趣,在前往世界各地工作的过程中,也对不同的族群产生兴趣。问我为什么写书,因为这是我能做的最愉快、最有趣的事情。不过,我直到1987年才开始面向大众写书,那年我50岁。在那之前,我一直在实验室里工作,是一名胆囊生理学家。我是世界知名的胆囊方面的专家。我还研究新几内亚的鸟类。
1987年,我的妻子生下了我们的双胞胎儿子,我第一次当上了父亲。人们经常会谈论世界将发生什么,比如热带雨林将在2050年消失,以及2050年世界将面临的问题。我出生于1937年,到2050年我已经113岁了,肯定已经离世,所以2050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想象中的年份。而我的孩子到2050年是63岁,正值人生盛年。我意识到我儿子的未来,不取决于胆囊,不取决于新几内亚鸟类,而是取决于世界的状况,取决于对世界上不同民族为何有不同经历的理解。
因此,儿子的出生促使我从胆囊生理学转向研究历史、地理、人类学和社会科学,并开始写书。我确实是一本接一本地写,当我写某一本书没能涵盖世界上所有有趣的事情时,我就会考虑写下一本。我的每本书通常需要4到7年的时间来写完。因此,我最近一本书《剧变》是在3年前,2019年出版的。我刚刚开始写我的下一本书,希望能在我90岁生日,也就是2027年时面世。
领导人不同,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否会有所改变?
戴蒙德:我正在写的这本书,目前部分内容要保密。但我可以告诉你,它的内容是关于领导力的。我一直对领导人的问题感兴趣,比如说,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领导人是否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领导人不同,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否会有所改变?
有个例子,阿道夫·希特勒,可怕的纳粹德国领导人。1930年,希特勒在一次车祸中差点丧命,一辆重型卡车从侧面撞上了他的车,他当时坐在副驾驶座上,差点被撞死。那是在他上台前3年。如果希特勒当时死了,欧洲还会发生二战吗?还会发生一场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大屠杀吗?有人可能会说,希特勒是一个异于常人的、邪恶的、有魅惑力的人。没有希特勒,就不会有二战或大屠杀。但另一方面,一战后《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导致德国很可能会试图扭转一战的败局,德国还是可能再次开战,而且德国一直存在反犹太主义。这只是一个例子,历史学家们仍在争论领导人是否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历史上如此,在商界也是如此。比尔·盖茨是与众不同的,马克·扎克伯格也是与众不同的,计算机和社交媒体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或者在体育界,有一些著名的体育教练,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我们的篮球教练约翰·伍登通常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体育教练,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因此成绩斐然。如果没有约翰·伍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篮球会如此成功吗?
最后,在宗教方面,重要的宗教领袖,耶稣基督创立了世界性宗教,穆罕默德也创立了世界性宗教。但耶稣基督当时在罗马帝国,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政府组织,而穆罕默德生活在7世纪阿拉伯半岛。如果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没有出生,当时罗马帝国的其他人或阿拉伯半岛的其他人是否也会创立世界性宗教?
这些例子表明了这一尚未解答的问题——领导人是否会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个有趣且重要的问题,将是我下一本书的主题,我希望这本书届时能在中国出版。
主持人:听起来非常有趣,这涉及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谁塑造了历史?是结构性因素还是个体的能动性?你这本关于领导人的书,似乎是讨论这个大问题的好方式。我记得,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对社会人类学非常感兴趣。我曾和一个朋友聊天,他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在IT行业工作。当我谈起对社会人类学的兴趣时,他说,你看过《枪炮、病菌与钢铁》吗?那是这个领域非常经典的作品。所以,贾雷德,你无法想象你的书有多受欢迎,甚至一个计算机科学家都会去读。
历史上那些失败者,会认同今天由成功者写成的历史吗?
主持人:项飙老师,你能分享一下对贾雷德·戴蒙德教授“人类史”系列作品的想法吗?
项飙:当然,我注意到贾雷德的作品在全球都大受欢迎,我想这是从《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开始的,并随着后续新书的出版,他的热度变得更高。我没有具体研究过中国读者对这些书的接受状况,但我知道是很受欢迎的。我很想知道,中国读者是如何阅读这些书的。我还非常想知道,贾雷德,你是否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行业,读者的理解是否有什么差异。
当我听到贾雷德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书,以及他如何写这些书时,我非常感动。很明显,他写这些书不是为了狭义的学术目的,而是为了解决我们所有人在这个关键时期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视野如此广泛。正因为这些问题是如此真实、如此根本,以至于不能由任何特定的狭义学科来解答。另外,他写这些书是因为他一直关注子孙后代的未来。因此,这种驱动力比单纯出于学术生涯考虑或狭义的科学好奇心要深得多,强大得多。我想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书有如此广泛的吸引力。我想补充一点,你的书很重要,因为它们提出了宏大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被讨论,即我们如何理解历史。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可能很多人已经问过你了,你在新几内亚的朋友亚力,是他引发了你写《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兴趣吗?他最后是怎么理解书上所写的内容的?
我在想,历史上的失败者,是如何阅读总是在讲述统治者的历史的?历史是否也可以被理解为斗争的历史,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历史?我还想提出书中的一个小片段,我认为这对中国读者很重要——我们如何理解郑和下西洋,即他到东非的航行。这是一个错失的机会?还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全球外交的例子?
它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错过的机会,因为当时中国本土的权力过于集中于朝廷,也因为当时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因此,郑和错过了殖民非洲的机会,也没能在哥伦布之前登陆美洲。但我们能不能把殖民主义定义为历史的相机抉择?因此,我们要寻找另一条线索,至今隐藏在人类历史中的线索。当然,纵观历史,如果我们从谁是统治者,谁是成功者,谁是赢家的角度来看,殖民主义确实是一种驱动力。但历史是否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因此,郑和那并不是一个错失的机会,它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一个例子。鉴于中国今天在世界的地位,我认为,这是需要智慧碰撞的吸引人的辩题,我认为这种讨论具有非常直接和深远的政治影响。
一个新几内亚人的问题,问住了彼此
戴蒙德:你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我来回答其中几个。
亚力是一个新几内亚人,我在1972年偶然遇到他。当时我在一个岛屿的海滩上散步,有一个新几内亚人过来和我一起,他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问了我各种各样的问题,关于鸟,关于火山。他想知道我研究鸟类能得到多少报酬,然后他问我关于新几内亚人和新几内亚历史的问题。最后,他的眼睛闪闪发光转向我,他说:“为什么你们白人来到新几内亚,带来了很多货物,带来了物质财富,而我们新几内亚人却没有搞出这些名堂?”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我完全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知道新几内亚人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而我已经在新几内亚工作了8年,我也知道新几内亚人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
那么,为什么欧洲人来到新几内亚,带来了文字和金属工具,还有政府组织,而传统的新几内亚却没有这些?那是1972年,我当时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花了15年时间才找出我在 《枪炮、细菌与钢铁》中给出的答案。但我再也没有见过亚力,所以我无法当面回答他。
至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吸引人的、重要的问题。中国在公元前221年首次实现统一,此后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大一统状态。欧洲从未统一过,即使是军事天才屋大维、查理曼、拿破仑、希特勒,没有人能够统一欧洲。今天的欧盟使欧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联合,但它不是中国那样强大的统一。为什么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会有这些差异?
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自然地,答案似乎是地理起到的关键作用。你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的地图和欧洲的地图。中国的海岸线是平滑的,中国没有大的半岛。欧洲的海岸线则非常曲折,有意大利半岛(亚平宁半岛)、有希腊半岛(巴尔干半岛)、有西班牙半岛(伊比利亚半岛)、有丹麦半岛(日德兰半岛),这些半岛各自都发展成独立的社会,有独立的语言和独立的国家。但中国没有这些半岛。欧洲有些大的岛屿——大不列颠是一个大岛,爱尔兰是一个大岛,克里特岛、撒丁岛都是大岛。这些欧洲岛屿中的每一个都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往往使用不同的语言。中国没有那些大的岛屿。
再说河流,中国有两大河流,黄河和长江,并行流动,两河之间的土地地势低,所以黄河和长江在历史上很早就被运河连接起来。但欧洲的河流,因为阿尔卑斯山位于欧洲的中部,欧洲的河流像自行车轮的辐条一样呈放射状流出。莱茵河流向西北方,易北河流向柏林,罗讷河流向西南方,多瑙河流向东方。欧洲的河流将欧洲分成不同的社会。中国的河流则连接了中国。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之间的差异,部分与地理有关,但我认为它们也与农业有关。欧洲的农业依赖小麦,中国的农业最初部分依赖水稻和小米,后来小麦才被引进中国。但是,种小麦与种水稻是非常不同的。种小麦的农民可以自己单干——麦农只需把麦种抛撒出去,然后等着收割麦子。但是水稻不是这样的,种水稻的农民需要灌溉水稻,因此必须与其他人合作,经营一个灌溉系统。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农业系统要求人们合作。欧洲的农业系统允许或者说要求人们成为个人主义者。但是,我们在中国发现了另一个实证例子——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是种植小麦,而不是水稻的。我也听说过、读过一些文章,认为在小麦种植区的中国人比在水稻种植区的中国人更趋向于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
这是个啰唆的回答,却说明中国和欧洲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这让我着迷。在我的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有一整章是关于中国的。在我的书《崩溃》中,也有一整章是关于中国的,试图去理解为什么中国和欧洲的历史走了如此不同的道路。
一眼望不到岛屿,所以缺少远航的动力
主持人:我想在二位的作品中,一个主要的共同点是关于流动性和相互关联性的问题。贾雷德,你的作品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等不仅强调了可以看到的主体的流动,如人、船、钢铁,还提到了那些微小的和几乎看不见的东西,如种子、病毒和病菌的流动,在理解某一文明繁荣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请你与我们分享一下,你有关迁移或移民特别是在人类早期历史中,如何为人类文明和繁荣提供重要动力的观点。
戴蒙德:移民是个有趣的话题,移民在世界各地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你提到了郑和下西洋的例子,15世纪,来自中国的宝藏船队抵达了东非海岸。看起来这些舰队似乎就要绕过非洲的好望角,抵达欧洲。但是舰队返航了。为什么?为什么欧洲的船队却一直向前航行?作为一个地理学家,我再次想到了诸多地理因素,包括为什么人们会有不同的移民冲动。
让我们以中国为例。从史前到15世纪欧洲殖民扩张之前,最伟大的移民是来自中国南部沿海的农民。他们首先移民到台湾岛,在台湾岛,他们衍生出了南岛语族。这些中国农民又在公元前2000年移民到菲律宾,然后到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斐济、夏威夷,他们成为波利尼西亚人,他们再移民到复活节岛,然后到新西兰。
相比之下,非洲人从来不移民,即使是到马达加斯加岛。最先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似乎是印度尼西亚人,而不是非洲人。还有北美和南美的原住民,美洲的原住民从未航行到中国,也从未航行到欧洲。为什么?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如果你站在东南亚的海岸,如果你站在新加坡向外看,会看到苏门答腊。从苏门答腊遥望,你会看到爪哇。而从爪哇,你能看到龙目岛。从龙目岛,你看到的是弗洛雷斯岛,从弗洛雷斯岛,你看到了帝汶岛,而从帝汶岛,虽然看不到澳大利亚,但你能看到澳大利亚大火的尘埃云。然后从新几内亚,你看到新不列颠岛,和新爱尔兰岛,还有所罗门群岛。换句话说,岛屿的存在刺激了人们造船,因为他们知道有地方可去。
而在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看不到任何岛屿。在欧洲,你站在海岸线上,可以看到一些岛屿,从法国,可以看到或隐约看到不列颠岛,当然,从法国的海岸,你可以看到科西嘉岛。而从希腊,你可以看到或感觉到克里特岛。因此,在我看来,岛屿的存在刺激了欧洲人的殖民,刺激了中国南方农民的移民,而没有岛屿刺激非洲人和北美、南美的原住民的移民。
这些都是地理的原因,但也有文化的原因。我的理解是,在15世纪的中国,人们认为中国拥有我们想要的一切。我们为什么要派出船队?那些船队只会给我们带回白色的长颈鹿。那些船队造价昂贵。为什么要在白长颈鹿身上浪费那么多钱?而欧洲需要船队带回香料,因为当时欧洲的肉,因为没有冰箱,气味和味道都很糟糕,欧洲人需要香料来掩盖肉类的不良气味,所以欧洲人最终派出船队到印度,然后到东南亚。
这就是我看到的世界不同地区人民在移民上产生差异的部分原因。
文/中信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