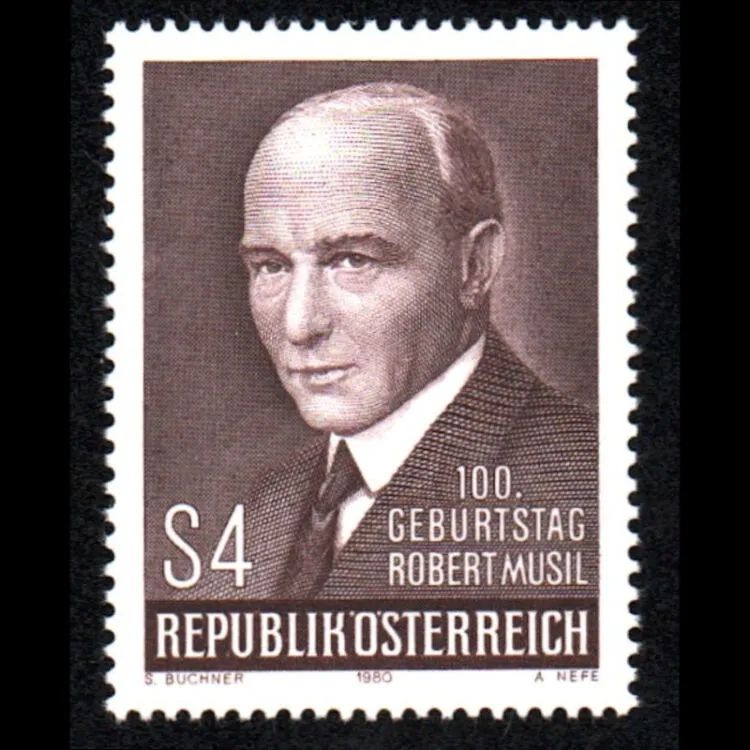今年是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逝世八十周年。穆齐尔与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一同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伟大作家。
1999年,在德国贝塔斯曼文学家和慕尼黑文学之家的要求下,由作家、评论家和日尔曼文学家各33人组成的评委会提交的一份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长篇小说排名表中,《没有个性的人》以35票的得分位列第一。
虽然如此,相比与他并肩的那些大作家,穆齐尔即使在最热的时候,也依然显得有些孤单、落寞。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重温穆齐尔的人生和创作历程,我们又该说些什么?
傅小平/文
1924年,罗伯特·穆齐尔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故:他的父母相继去世。也是在这一年,奥地利爆发了有史以来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穆齐尔因此陷入经济贫困和丧失亲人的双重痛苦之中。然而,这直接促成了他全身心投入到生命和心血之作《没有个性的人》的创作中。穆齐尔和一家出版社约定,由出版方支付给他固定的生活费,小说完成后即交付出版。
这注定是一场与魔鬼签订的契约。按照穆齐尔的计划,小说由三卷构成。第一卷《向可能到达的边缘前行》完成之后,于1930年出版;第二卷《进入千年王国》出版于1933年;按原计划,第三卷将于1938年出版,但突如其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他流亡到了瑞士,生活无着,疾病来袭。颠沛流离中,第三卷终成了没能完成的断章。1943年,当它以《在世遗作》为名出版时,这位日后声名卓著的奥地利作家已辞世整整一年。
事实上,即使在生前,穆齐尔也不能算是那种典型的“不能被同代人理解的作家”。在他生命的晚年就已经有“穆齐尔协会”成立,他曾获得过各种文学和戏剧奖项。但他最终没有逃脱经济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孤独,也没在广泛意义上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部作品在去世后会获得那么大的赞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表示:
在当代德语作品中,我从未如此有把握确信后世的判断。《没有个性的人》毫无疑义是最伟大的……这本书的生命将会超出这几十年,并会在未来获得崇高的荣誉。
这个预言在今天已经部分得到印证。1999年,在德国贝塔斯曼文学家和慕尼黑文学之家的要求下,由作家、评论家和日尔曼文学家各33人组成的评委会提交的一份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长篇小说排名表中,《没有个性的人》以35票的得分位列第一。不仅如此,穆齐尔的这部作品在西方评论家的眼中,是堪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和托马斯·曼的《魔山》并驾齐驱的现代派巨著。穆齐尔则与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一同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伟大作家。
继作家出版社于2001年首次引进出版这部难读的名著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5年推出修订版,一时间在文学圈内外引发了一阵不大不小的“穆齐尔热”。在此前后,穆齐尔的小长篇《学生托乐思的迷惘》以及短篇小说集《两个故事》《三个女人》等,也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引进出版,并引起了小众读者的关注与阅读。虽然如此,相比与他并肩的那些大作家,穆齐尔即使在最热的时候,也依然显得有些孤单、落寞。今年是穆齐尔诞辰140周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温穆齐尔的人生和创作历程,我们又该说些什么?
01
关于《没有个性的人》,被引用最多的莫过于米兰·昆德拉的话。他认为,穆齐尔“将卓越的、光芒四射的智慧赋予了小说”,“使小说成为绝妙的理性的综合”,也因此,“尼采使哲学与小说接近,穆齐尔使小说与哲学接近”。昆德拉进一步表示,如果说菲尔丁在讲述一个故事,那么福楼拜就是在描写一个故事,而穆齐尔呢,他要思考一个故事。
其实,用传统的文学视角看,这部奇特的作品概而言之,可以说就是“没有故事”:在奥匈帝国的维也纳,人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旨在筹备1918年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在位70周年的活动。同年,德国将庆祝德皇威廉二世在位30周年。人们称奥地利的这个行动为“平行行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年恰好是两个帝国覆灭的年份。32岁的青年知识分子乌尔里希就是这个委员会中的一员。此前,他已经进行过三次尝试,企图出人头地,但是当军官、工程师和数学家的三次尝试都未曾取得令他满意的结果。他就在这个严肃而又怪诞的委员会里无谓地忙碌着,遇见了一些人,和几个情人来往。甚至与亲妹妹之间产生了错位的“爱情”。然而这一切都仅仅只是插曲。
最后,乌尔里希如同穆齐尔本人一样害怕,如果不把自己的个性塞进某个公共认可的口袋里,那个性就会像粉末一样四散而开。但对他来说,可能性比中庸的、死板的现实性更重要。正因为他害怕在一个极其技术化的时代再也找不到“整体的秩序”,他便决定“休一年生活假”,以便弄明白这个已经分解为各个部分的现实的“因由和秘密运行体制”。这样,他便退而采取一种消极被动的、只对外界事物起反射作用的态度。他觉得自己是个没有个性的人,因为他不再把人、而是把物质看作现代现实的中心……
这样一部超越时代的作品难免招致非议。有人说,穆齐尔过于抽象的叙事特点使人物缺少生气。也有人说,这部小说不忍卒读。德国文学批评家拉尼茨基如此描述:“毋庸讳言,《没有个性的人》好比一座沙漠,沙漠中虽有几处景色优美的绿洲,但是从一处绿洲到下一处绿洲的跋涉往往令人痛苦不堪。没有受虐心理准备的人还是趁早投降为好。”即便是一些通读了小说的人,也指责穆齐尔不是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德国学者、作家瓦尔特·本雅明称赞了他的非凡智慧,却只字不提他的艺术造诣。但也有一些人给予了好评。小说的第一卷出版后,即有评论家比尔赞赏道:“1075页中没有一行字言之无物,每一行字都对这部无可比拟的作品的整体结构有重要意义。书中写了什么?今日的整个世界。”
奥地利邮票上的穆齐尔
如此表述看似玄虚。却一语道出了小说的“天机”:没有同时代的现代派小说所刻意追求的一切元素。无论其思索的长度,段落的慢节奏,都给人一种“传统式”行文的表象。然而,穆齐尔正是要在此种不引人注目的表象中,对小说进行一场结构性的革命。他把一种执著、细密的分析能力带进了现代小说。这意味着后世的作家倘要具体而确切地解释他的时代和生活,他就必须面对他所树立的这个迄今仍然未曾被逾越的标杆。
02
如同所有未完成的传世作品一样,《没有个性的人》同样给人带来了无尽的悬想,或许还有深刻的启示。同为德语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在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说中感叹道:我向穆齐尔学习的东西是最难的东西:这就是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自己的创作,但却不知道这个创作是否能完成,这是一种由耐心组成的冒险行动,它是以一种近乎非人道的顽强精神为前提的。
确如卡内蒂所言,穆齐尔的“顽强”可说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精神生动表现他在写作过程中经历的难产与反难产的艰难斗争中:为了撰写两篇总计一百多页的小说,他用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其间他总是“没日没夜地工作”。而穆齐尔从1905年开始设想《没有个性的人》,20年代开始动笔,前后易稿二十余次,一直到去世,书仍然没有完成。无怪乎在他看来,“写一本书要比治理一个王国重要得多,而且也困难得多”。
而实际上,穆齐尔是有可能在生前就获得更大声誉的。在大学撰写哲学博士论文期间,穆齐尔写出了他的处女作《学生托乐思的迷惘》,虽然遭到多家出版社拒绝,最终还是于1906年出版。小说出版一年后再版了四次,称得上是畅销书了,穆齐尔也受此鼓舞放弃了大学教学的机会决心当职业作家。此后,穆齐尔于1924年出版小说集《三个女人》,再后来,他还出版了同样薄薄的小说集《两个故事》,也多少引起一些反响,但更为厚重的作品《没有个性的人》迟迟没能写完,再加上时局的动荡,穆齐尔被遗忘就可想而知了。
穆齐尔曾把他写作总是难产的原因,归结为极其微少的传达欲望。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源于他特殊的文学理念。在青年时代,穆齐尔曾被问及想通过小说达到何种目的,他言之凿凿答曰:“通过心灵与精神的力量控制世界”。确实如此,穆齐尔从不满足于讲故事,他的小说故事情节都极尽简单。以《学生托乐思的迷惘》而言,故事讲的是,二十世纪初,临近崩溃的奥匈帝国,沉默内向的主人公托乐思不适应军校的寄宿生活,从思乡病开始,到得不到父母安慰,求教于数学老师的失败以及阅读康德的困惑,最终他变得糊涂茫然,迷惘万分,以至于和年长一些的同学赖亭、白内贝走到一起,充当他们以大欺小、仗强凌弱的帮凶。赖亭和白内贝发现了同学巴喜尼的偷窃行为,于是把他带到教学楼里的一个隐蔽的储藏室施以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托乐思从一开始就是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会不时地给赖亭和白内贝出些绝妙的点子。随着恶毒行为的升级,托乐思最终选择和冷酷无情的同学分道扬镳,小说的结局是托乐思退学,巴喜尼自首后遭校方开除,但赖亭、白内贝则利用他们的如簧巧舌顺利开脱了罪责。
这部日后由德国导演施隆多夫于1966年搬上荧屏,并获奥斯卡最佳外语奖的小说,诚如书评人远子所言,初读时会联想到青少年对成长的不适与青春期的躁动,但深入细读就会发现,穆齐尔并不只是写了一部揭露德意志守旧意识的校园小说或青少年小说,他实际上是想借助少年间暴力恶作剧事件,探讨传统社会解体时期人们对支配欲的盲目贪求可能带来的恶果。某种意义上也因此,穆齐尔在交代故事的同时,对小说做了很多“切割”和“赘述”。虽然小说情节因此变得不连贯,但就像远子说的那样,正因为穆齐尔杂以大量的夹叙夹议和心理分析,乃至哲学思考,并用反情节的思维过程和独白式的沉思对话让故事步步推进,才使得这本不到两百页的小说,显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一样漫长。
同样,收录穆齐尔中篇《格里吉娅》《葡萄牙女人》和《佟卡》的小说集《三个女人》看似写的,三个男性主人公分别遇到命中注定的情人,并品尝着精神的狂欢。但如有论者所言,穆齐尔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还写出了这狂欢深处的幻灭,以及在此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未来人”的特征。而包含了《爱情的完成》和《对平静的薇罗妮卡的诱惑》两部中篇的小说集,看似写了两个无关轻重、体量短小的爱情故事,穆齐尔叩问的却是身体和灵魂的存在问题、感知和思索的关系问题、此在与彼岸的时空问题、激情与压抑的矛盾问题、野性与文明的选择问题。
03
支撑起《没有个性的人》这座“大厦”的,当然也不是故事情节,而是穆齐尔对整个人类历史所取得的成就、当时的人类世界的,巨细无遗的思考与洞见。读完这部巨著,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感叹道:“穆齐尔把所知道的或想知道的都写进一本百科辞典型的书中,而且极力赋予这本书以小说的形式。但这本书的结构却在不停变化,或者他又亲手拆毁它,眼睁睁地看着它变化,使他不仅无法写完这本书,甚至无法确定这本书的轮廓究竟如何才能容纳规模如此庞大的素材。”
在《没有个性的人》里,穆齐尔借阿恩海姆之口说:“在本世纪初,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就已经为新的、机械化了的社会和情感生活创造了史诗,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和弗洛伊德则揭示了低层的魔力: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深感已经没留下什么要我们去做的事了。假定我们有一个荷马:扪心自问吧,我们压根儿有没有能力去听他吟唱吧?”但摆在穆齐尔面前的挑战是,即使没有人聆听,他依然要像荷马那样吟唱,只是他要唱出从未有过的曲调,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文学创作不应该承受一种现成的世界观。文学创作的任务也不是描述“什么是”,而是描述“什么应当是”。换言之,他是想发现一种新的小说样态,更进一步,他想在小说中提供一种新的理想、一种新的道德人。
在旅途中小憩的穆齐尔
然而,穆齐尔所处的时代,差不多就是欧洲历史上观念最混乱、迷惘的时代。旧的时代已告崩溃,新的世界尚未显露,新的理想、新的道德人更无从谈起。由此,穆齐尔本人也像乌尔里希一样找不到“行动的意义”,甚至是感觉到“昏眩”或“无力”,“而且还掺杂着一种可怕的厌恶:对不得不重新开始的厌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表示,穆齐尔的窘迫,恰恰是当时欧洲时代精神的直接反映:它看不到出路何在,它处在“危机”之中,它注定是未完成的。
生命中最后十年,穆齐尔基本上是在贫困、寂寞、无助和凄凉中度过的。他面对更大的内在贫乏还在于,在此期间,他几乎没有完成任何可供发表的文字。时值1940年,穆齐尔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印象:“我觉得末日在向我招手。”他于两年后去世,身后留下一些书和他的两箱手稿。他留下了纪念碑似的著作,却没有留下供后世凭吊的墓碑,他的骨灰按家族传统洒在了日内瓦附近的森林里。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