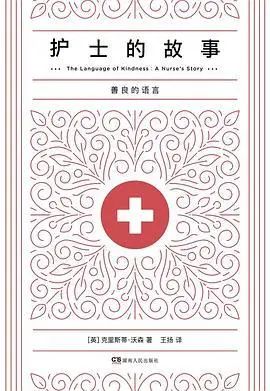最近几天不断传来的疫情趋缓消息,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春讯。许多发生疫情的国家和地区也终于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严阵以待来控制病毒的蔓延。
无论在哪,这场无声战役中冲在最前线的永远是医护人员。而正像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向媒体强调的,重疫面前,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团队,就是我们的护理团队——“医生有多重要,我们的护理姐妹们就有多重要。”
我们都知道南丁格尔,却很少真正体悟“护士”这一群体的重要性——在病弱的躯体和严肃的治疗措施之间,在个体最脆弱、最易受伤害和最孤单时,正是护士的存在,让我们不再感到孤立无援。
当了20多年护士的克里斯蒂·沃森拥有这一职业几乎共通的性格特质:她坚定而温和,果敢又满怀柔情,敏锐又细致入微。她又是特别的,敏感于病人的情绪变化,回应需求、支撑尊严、思考价值,并用畅达的文字记录了下来,比如分享在面对病人时的“表情管理”——
放慢呼吸和动作,专注于表现随和的肢体语言和温柔的微笑。如果护士表现得焦虑,患者会以为自己差不多万事休矣。
我们跟随作者,来到儿科重症病房,看护士给从火灾中生还的小女孩洗头;来到急诊室, 和护士们一起应付醉鬼和毒虫。我们会遇见病痛缠身的年长病患,那是社会亟欲忽视的隐形人口。我们也将认识每天开出无数处方药的药剂师,以及太平间里必须目睹家属接受亲人死亡的护理人员。而沃森在父亲罹患癌症后更是意识到:护士所能给予的,并不仅仅是照顾我们的身体,更是守护我们的灵魂。
今天,为你带来护士沃森的自白——站在手术台边和病床前,被人们认为是“永远的配角”的她们所拥有的丰沛内心世界,以及一颗悲悯之心。
《护士的故事》 [英] 克里斯蒂·沃森 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推出
1
手术室里的情景对患者来说一定很可怕,但我已习以为常。能习惯这种事情其实挺让人惊奇的。生活并不总是这样。
我亲眼看过的第一个手术是一场心肺移植。那时候我19岁,还是个护士学生。手术格外漫长:超过12个小时。它需要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表现得像一支接力队;但他们手里传递的不是接力棒,而是人类的心和肺。我那天护理的是一个一直在等待一组新肺的患者:一个名叫阿伦的14岁男孩,患有囊性纤维化症,只能躺在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整日疲惫而虚弱地咳嗽,皮肤灰黄。我帮他做术前准备,把可可油涂在他干干的膝盖上,拿走他的GameBoy游戏机,并发誓会用生命保护它。我用一块三文鱼粉色的、浸过无菌水的海绵润湿他的嘴唇,不想冒一丁点让他接触任何细菌的风险。
星星和月亮形状的光源围绕着阿伦的病床,微微照亮他的房间。在他的床边,继父用蓝丁胶帮他把一个小小的软木公告板固定在墙上,上面是他和朋友们的拼嵌式照片,每个人都在微笑。儿童病房里的个性化装饰很常见。除了穿墙而过的氧气管道和带厚厚透明管子的抽吸器,病房可能就是一间最常见的儿童卧室。
我们聊着天,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但当搬运工进来帮我把他送到手术室时,他紧紧抓住他妈妈。“我睡着之前别走。”他说,然后望着我,“你会一直在那边吗?”
“我会的。你准备好了吗?”
他摇了摇头说还没有。但我还是朝搬运工点了点头,他们把他的床推出病房,走上走廊。其中一个搬运工是个活泼的小姑娘,一直在吹口哨。儿科病房的走廊墙壁专为孩子打造,上面画着动物和花朵。孩子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推着点滴架,他们的父母或护士在他们身后微笑。搬运工吹着口哨,阿伦又摇了摇头。他妈妈握着他的手,快步跟在床边。我用余光注意着床尾的显示屏,上面呈现的是阿伦的血氧水平。我不会让它掉下去的。“不是现在。”我在心里说,“稳住,稳住。”我听说有孩子被困在坏掉的电梯里,情况越来越糟,等有人找到电梯工程师时,氧气已经耗尽,孩子的心脏完全停止跳动。我很焦虑,但已经学会摆出护士最常使用的表情。我放慢呼吸和动作,专注于表现随和的肢体语言和温柔的微笑。在解释临床实习对我们积累经验有何益处时,一位护理讲师告诉我们,患者如果看到有经验的护士表现得很焦虑,他们就以为自己差不多万事休矣了。
手术室是一个由走廊和推床构成的迷宫,各处覆着蓝色的无菌罩布,放着除颤器片和难对付的导气管组件。手术室护士的脚步很快,木底鞋在走廊上吱嘎作响,半系半敞的手术罩袍飘动在身后,仿佛魔法师。手术室里有很多设备间,其中一间需要护士跪在地上,拿着检查表,每天早晚各清点一遍:有效期、套数、新订批次的日期。角落里有一台高压灭菌器,一些设备正在那里接受消毒;动脉血气仪可以告诉护士麻醉师进展如何,患者是否有氧或充满二氧化碳气体。蜿蜒的走廊里光线暗淡,空气似乎格外浓重,像承载味道那样承载着记忆。如果听得足够认真,你就能听到它讲的故事,关于被误摘的肾脏,关于停电而发电机没有启动的时刻;再或是关于正在接受除颤的患者氧气还没被移除,发生的一场爆炸,那声响不输炸弹,最后导致麻醉师头部受伤,进了重症监护室。如果墙能讲话。
大多数人都不会留下关于手术室的记忆。我们睡去,然后醒来,无法计较这中间发生的事。手术室护士看到了一切。但手术室又确实是个“生死掌握在他人之手”的地方。大多数时候一切平安,然而一旦出了差错,便会引发一场灾难。当患者状况突然恶化时,原本有条不紊、安静平和、一尘不染的环境就会变成战场。麻醉师会尽最大可能预测哪些患者可能会出问题——肥胖的、吸烟的、怀孕的等等——但总有意外发生。有的患者声称自己在手术中醒了过来,却动弹不得。这种现象可由麻痹剂和患者对同时施用的镇静剂反应不足来解释。有些患者对麻醉药物的反应很激烈,血压会下降到危险的地步,偶尔还会心脏骤停。
我照顾过这样的患者:他们在术后得知手术时情况有些不稳定,但医生设法稳住了局面。护理的语言有时候很难表达。心脏细胞在培养皿中跳动,单单一个细胞。而其他人的心脏细胞则在不同的时间里在培养皿中跳动。不过当它们碰到一起,就会以和谐的频率一起跳动。医生可以用科学来解释这一切,但护士知道科学的语言是不够的。手术室护士会把“你丈夫/妻子/孩子在这里死过三回了,不过今天是个好日子,通过大量电流和可能会把肋骨搞断几根的胸部按压,我们已经把他/她救了回来”翻译成一些普通人可以接受的语言。一种奇怪的诗歌。
2
我尽量不去想手术室里会发生什么,不去想所有可能会犯和曾经犯过的错误。我摆出一副“外表淡定,内心慌张”的姿态,直到我们抵达麻醉室,里面充满了令人心安的设备和表情非常放松、面带微笑的麻醉师。“好啊,女士。你好,阿伦。”麻醉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与阿伦对视着,手术助理一直在近旁忙活,准备监视器和贴标签的注射器。我站在床头,离阿伦的妈妈很近,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比如阿伦在麻醉气体的作用下睡着后,同时需要带她出去的几秒钟内,迅速够到并拉她出去。我们不希望她看到患者在被麻醉后的下一个阶段:眼睛被胶带封住,头被尽可能向后掰,一根管子插进他的气管,针头扎入静脉,剩下的衣服全被脱掉。然后我们还会在他的皮肤上涂一层浑浊的铜与必妥碘溶液,直到他看上去不像个人,而像块肉。1800年,议会成员瑟洛勋爵就术前准备说过:“外科手术不比屠宰科学多少。”外科手术向来被看作比较低级的职业,在中世纪时妇女都可以做。直到8世纪,女性才退出了这一行业,因为外科手术训练进入大学,而当时的女性没有上大学的资格。针对外科手术的态度和公众观念的发展,现在已远远超过针对护理的,而后者似乎还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咬紧牙关,等待着那个糟糕的时刻:孩子即将接受麻醉,父母要向他/她吻别,把他/她交到陌生人手中。我对麻醉师心怀敬畏——尽管就要独自负责一个病情复杂的高危患者,她依旧冷静、镇定,令人心安。
后来有一回,我去手术室和护校同学杰茜一起观摩手术。当时,我同样对麻醉师印象深刻,心怀敬畏,直到杰茜告诉我他们俩之间有一腿。手术过程中,我发现杰茜把口罩慢慢往上推,直到把眼睛都罩了起来。“你干嘛呢?”我问她。“这里的所有人我都睡过。”她说,“除了躺着的那个。”
“忙起来,”我说,“时间过得很快的。”
时间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如果我们在家人做手术的时候等待,它会变得慢吞吞的,每秒钟都像是一分钟,每分钟都几乎是一小时。如果是我们自己接受手术,时间就过得飞快:我们倒数十个数,然后事情了结。
大手术室里挤满人,但你还是能够听到一根针掉落的声音。外科医生脑袋后面有一个高高的架子,上面放着一台收音机,但它也很安静。手术顺利时,没人会注意到舒缓的音乐。“把音乐关小点”往往意味着事情出了岔子——动脉割伤、出血、血压下降或心脏骤停。但今天根本没有音乐,说明情况不容乐观。我跟一群医学生和初级医生一起站在观摩台上:大手术室里挤满人是一场引人关注的或具有开创性的手术的标准配置,而手术过程中的教学是通行做法。现如今,为实现教学目的以及获取其他各国医生的建议,全世界的外科医生都对日常手术进行拍摄和流媒体传播:洛杉矶的手术细节专家再也不需要离开洛杉矶去别的地方。手术室里有许多屏幕,但它们首先是为手术室里的人架设,而且跟实际的手术还存在一定距离。很多人研究着屏幕上的影像,观看外科医生的手在患者体内上上下下,仿佛舞者一般翻转扭动,以完美的同步性与一旁正在搏动的心脏共舞。我想我从没见过什么东西,能像阿伦在我眼前跳动的那颗心脏这样美妙。当然多年以后,我也见过一些更加美丽的东西,比如通过超声波看到的我自己孩子的心脏,它在屏幕上轻轻跃动。
3
阿伦在房间中央,身体就像一条独木舟。医生的手正在他身体里。把手放进别人身体,用手指触摸心脏,与他短暂地融为一体,这是一项多么奇怪的特权。我一边看着手术一边想:外科手术和患者,多么像母亲和她未出生的孩子,都在一段时间内共享同一具躯壳。房间里散发着氯、漂白剂和汗水的味道。还有一种奇怪的刺鼻金属味,可能是血液的气味。墙壁很干净,但我知道体外循环膜氧合器——在某些手术中,会带动一个人全身血液参与循环的机器——一旦裂开,墙壁、天花板,以及所有的医生护士和机器设备,都会浸在血海中。好一场恐怖片。
我颤抖着,专心盯着阿伦的一绺头发。它提醒我阿伦并不是一具待宰的尸体,而是一个热爱天文学的男孩,他破旧的GameBoy游戏机已经被我安全地锁起来。外科医生的身体完全伏在阿伦的身体之上,只有他的手和胳膊还在动。其他的医生(我数了一共是4位)围绕在手术台边,面对着他,其中一个拿着抽吸导管,吸净医生手边的血液,以便他更好地进行观察。另一位外科医生只是负责举着一盏大灯,照亮阿伦的身体内部。到处都是灯光,即便只穿着一件薄罩袍,手术室里仍然很热。但灯光永远不够用,我看着整个手术团队——大多数都是头发灰白的男人,只有几个女人——想象他们的职业生涯都是从举灯的工作开始:他们是如何从负责举灯到抽吸血液,再到让手在患者体内起舞。那一定是一段需用一生去注视的时光。外科手术令我着迷,尤其是在这家三级护理教学医院。这里没有枯燥的例行公事,即便有,也是对有复杂和重大就医需求的儿童施展手术。
但今天我到这里并不是来看主刀医生的。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身材宽大的女人,帽子前额露出稀疏的头发,戴着双层手套的手放在身前,手指呈海星状伸开,手掌向下。她身前是一张放着各种金属器具的长桌,在白色的天花板上反射出钻石般的光泽。通常,主刀医生或辅助医生会在不抬眼的情况下说些什么,她就会拿起一个器具——手术刀、缝线、镊子或动脉止血钳——递给他们,把刀柄那端放在他们手里,就像递剪刀那样。有时没等医生说话,她就能把器具递过去。他们之间十分默契。她是手术助理护士,当一种器具用完,手术助理护士就会转向站在她身后的护士,向她眨眨眼,并把器具放在托盘里递过去,由她放到手术台后面的桌子上。房间里的一切都不会被带出去,并要再三清点。“以免外科医生不小心把一根棉签留在患者身体的某个洞里,或把手术刀留在肺里,纱布留在肠子里。”第二天,手术助理护士告诉我,声音严肃,“我们还有更严重的丢失情况。有时手术进展不顺,我的器具就会被他们扔掉,然后就找不着了。”
“扔掉?”
“被外科医生,有时还会是护士。”她看着我,挤了挤眼睛,露出微笑,“这份工作压力真的很大。”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实情,也不知道她是说外科医生还是她自己的工作压力很大,但我不敢细问。
她的眼睛里有一种闪光的东西,只有在靠近她时才看得见。我以前没注意到。她鼻子上有个洞,是戴鼻环留下的,而且后来我知道她对摩托车很着迷。她的样子一点都不像我想象中的护士。我获得的情况已足以让我意识到,手术助理护士不适合我。
4
今时今日,手术室护理发展到需要护士跨区域工作,这些区域包括外科住院休息室、主手术室、康复室和日间手术室,但手术助理护士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要做手术助理,就像夜班护士一辈子都要上夜班。实际上,现今所有护士都是日夜轮流上班了。我知道自己做事不大有条理,而且没法站太久,难以忍受手术室的温度。但在几个小时的手术过程中,我经常盯着手术助理护士那双坚定的手:这双手完美静止着,而后突然有了目的,即刻声势浩大地动起来,然后,再次静止——动作的方式与医生那美妙轻巧的双手完全不同。
我注视着这位护士的眼睛,想象她目光所及的事物。她的目光偶尔会落在这场我们共同见证的手术上,而后在房间里四处游移,落在医生身后的监视屏上,我看到她的眼睛注视着生命体征的读数;然后她又看向执业医务技术员(血气分析仪专家),后者头戴彩色扎头大手帕,坐在心脏转流机旁边的凳子上,在一块纸板上疯狂地写着什么。这台转流机看上去非常科幻,插满各式各样、七扭八拐的管子,仿佛水上乐园里复杂的水滑梯。护士转过头,瞥了一眼站在门口的助理护士,然后是器官捐献协调护士,后者手里正端着装有另一个人心脏和肺的盒子。那是一个普通的白色盒子,上面写着“人体组织”字样。手术助理护士的眼睛在那只盒子上盯了很久。然后她又抬眼看了看器官捐献协调护士,两人似乎交换了眼神,交换了某些我在当时还不明白的东西。但我很感激面前这一切的重要意义,整个房间遍布奇迹:科技、外科医学、科学与运气,还有护士们能够看出的悲伤与失落。
我一直站着,直到感觉不到脚趾的存在,而整个团队——包括手术助理护士——已经换了三班。所以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也感觉自己从未如此清醒。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5
那是手术后几周的事了,阿伦看上去判若两人。他的皮肤变得更有光泽,不再需要用氧气管呼吸,撕心裂肺的咳嗽也完全消失。他的卧室里现在堆满书、游戏和卡片。
“我超爱草莓冰淇淋,”他说,“我以前一点都不喜欢。”
护士并不执意寻找意义,但意义是她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她们自然会用一种心灵的语言,理解并形容患者是“心碎了”。很多护士都见过这种情形,而且最好的护理也出自心灵,而非头脑。
阿伦找我帮忙,替他给那个去世后把心脏捐给他的男孩的母亲写封信。这封信不能直接寄出去,但器官捐献协调员承诺会去询问那个男孩的母亲愿不愿意读这封信。如果她愿意,这封信会在适当的时机匿名送到她的手上。从那封信写下到现在已经20年了,我仍然记得那封信的每一行,它让我乐不可支:“您儿子喜欢吃草莓冰淇淋吗?”然后又痛哭流涕:“您儿子去世了,我因此还能活着,这不公平。我发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我想起我当时注意到,器官捐赠协调员和手术助理护士手术时交换的眼神。有时候,护理是洗净双手,在手术台前传递手术工具,清点棉签的数量。有时候,护理是整理外科医生手术袍的系带,是在医生开口之前就把需要的工具递给他。而另外一些时候,护理是察觉失落与悲伤,还有帮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写一封不大好写的信。
到我下班时,阿伦的妈妈跟我说,阿伦其实一直很喜欢吃草莓冰淇淋,但他们之前不给他吃乳制品,因为这会加重他黏液分泌的症状。
她妈妈笑得格外灿烂。“现在,这孩子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了。”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