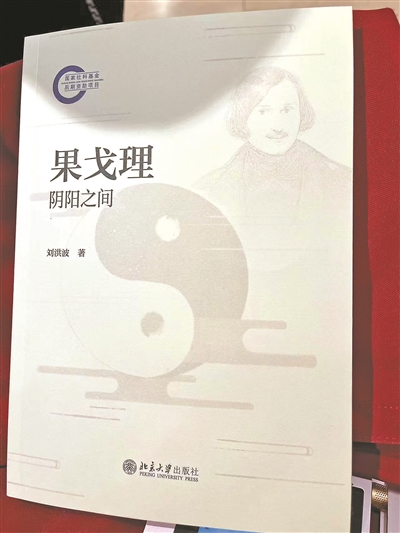前不久,草婴读书会北京分会携手北京大学出版社、风入松书店,一起为刘洪波教授的新书《果戈理——阴阳之间》举办了一场分享会。我虽然对果戈理所知有限,仅停留在知道他写有《钦差大臣》《死魂灵》,鲁迅先生对其推崇备至,但是,一向求知若渴的我怎么会错过这个好机会呢?
当晚,刘洪波老师穿深棕底色暗纹绸纱裙装,柔粉色蕾丝披肩覆于肩头,精致胸针与珍珠耳坠交相辉映,端坐桌后,眉目含笑、优雅温婉。嘉宾赵桂莲坐在刘老师旁边,她和刘洪波老师都是北京大学俄语系的教授。刘老师说,赵桂莲老师从头到尾目睹、陪伴、激励、帮助了她研究果戈理,直到写成这本书。
赵桂莲老师面容亲和,跟洪波老师一样爱笑,气度沉稳豁达,对俄罗斯文学大家及其名言、轶事信手拈来,娓娓道来时,智慧的火花在言辞间跳跃,常常惹得我们会心一笑。她看刘老师的眼神,满是欣赏与友爱。
刘洪波老师仍是一贯的真诚、谦逊。讲到她研究果戈理的缘起,原来是为了读博士学位,而非一开始就情有独钟。她笑着说本来喜欢的是普希金,但同事中已经有人在做专研,她“不得已”才转而去研究果戈理。而且那时她还对果戈理存有些偏见,“因为”,她说,“爱讽刺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恶意吧?”
看来,虽然洪波老师学习与从事的是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工作,但潜移默化中,早已秉持了我们“温柔敦厚,婉而不讽”的诗教传统。是啊,谁不爱翩翩浊世佳公子、阳光开朗大男孩!谁会一眼看上矮小多病、拘谨工作狂的苦行僧?
可是,批评家们对果戈理两极分化的评价让刘洪波困惑不解。此外果戈理身上的诸多神秘的疑团也很“迷人”:为什么一个人既是黑的又是白的,一忽儿是浪漫的,一忽儿又是现实的?他先天不足、一生怕鬼、从不站队,他如何自救?如何对抗“庸俗中的庸俗”?如何自立于大师云集的俄罗斯文林?为何如今,当果戈理研究成为显学,而中国人仅知其名,绝大多数人未曾读过他的作品,果戈理在中国竟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刘洪波说,在研究中,她越来越被果戈理所吸引,欲罢不能,23年“眺望深渊”,一头扎进“幽深的令人不解的黑洞”。虚心、慎思、谨严的刘老师对自我要求很高,她越是扎进资料堆的汪洋大海,就越来越多感受到果戈理的多样、多面、多变。这让她觉得底气不足,于是不断推翻、修正自己的看法和认识,不肯轻易成书付梓,总是要“再等等,再想想”。直到她寻找到一个独属于中国人的视角,独属于她的视角。那是一把钥匙,开启果戈理的神秘世界;又是一根线,连缀统摄果戈理的一生及其作品——那就是老子的“道”,中国的“阴阳”。
果戈理甫一出生就先天不足,但极具写作的才华与天赋,生命本能中,他用文学创作的“阳”来对抗生命里过剩的“阴”;中期他用入世的艺术创作对抗社会上的庸俗与丑恶;晚岁他用布道者的姿态努力发出思想者的最强音。
刘洪波说,虽然普希金没有出过国,但大家公认他是俄国的欧洲人。果戈理虽然在罗马生活多年,但他却是地地道道的俄国人。赵桂莲老师补充说,俄罗斯民族骨子里的性格是阴柔的性情中人,不像中国的“中庸”。
分享会中,我私心觉得,赵桂莲就像小太阳,闪耀、热情;而刘洪波,是温柔的月亮。两位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同年挚友,20多年想来也是一动一静相知互补的吧?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刘洪波见过太多高山,遂高山仰止,一直以小学生的姿态,孜孜以求,总觉自身天赋不够,因而倍加努力用心。23年磨一剑,这本《果戈理——阴阳之间》,资料非常扎实,干货满满、诚意十足。刘洪波认为果戈理最可贵的是真诚、执着,“他真诚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创作与使命,他是玩命写作第一人。”
果戈理已切切实实融入了刘洪波的人生,除了研究,更有“神交”。而这一场读书分享会,也让每个参与者与果戈理建立起了“间接神交”。会后轻松的讨论,又分明给大家增加了一把沟通的钥匙
文/木末
编辑/刘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