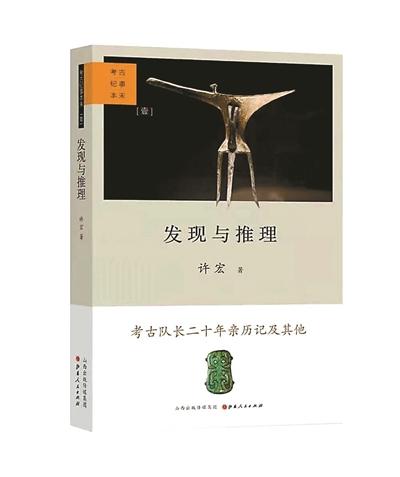
主题:考古背后有故事——《发现与推理》读书分享会
时间:2021年5月7日晚7:00
嘉宾:许 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郑嘉励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于赓哲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主持:许 楠 单向街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主办:汉唐阳光
从历史中获取情感慰藉和人生经验
主持人:今天这场活动源于许宏老师的《发现与推理》。腰封上非常特别的“推荐者”名字叫嵌绿松石铜牌,是出土于二里头的一件重器,推荐语是“考古队长二十年亲历记及其他”,非常酷的一本书。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开启对河南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工作,由此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尤其近几年来,考古成为越来越火热的一个话题。第一个问题想问三位老师,你们觉得人们为什么对距离那么遥远的事情充满了兴趣,并且热衷于探讨?
许宏:无论研究考古、历史——于赓哲老师是做文献史学的,我们没有特别“高大上”的动机,首先是要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每个个人,直到全人类,都会对自己的童年感兴趣。一个人如果不憨不傻,一定想了解“我”是怎么来的,小时候是怎么回事。这是非常朴素的情感,考古学首先要解决的是这样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在一百年之前是显学,就是为了因应大众的需求,解决萦绕在中国人脑海中的问题——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中国是怎么来的。在文献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先哲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然后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我们的学科在一百年前诞生了。
于赓哲:正如许宏老师说的,好奇心是人类进步的一个主要动力,没有好奇心就没有人类的现在。这个好奇心不仅有对未来的探索,还有对历史的探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永远萦绕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为什么探索过去?其实就是探索我们历史、文化的底蕴,探索我们这个民族、国家,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维模式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而且这个问题最终能够回答“哲学三大命题”的第三个命题——“我到哪里去”。对考古和历史的不懈追求,说白了就是人类对自己的一种关怀。
郑嘉励:我补充一点,喜欢听故事是人性中的一部分。故事,顾名思义,就是过去遥远的事物。人对故事的好奇心,除了知识性需求以外,更多的是因为故事里,蕴藏着人类过往的生活经验和人生经验。每个人都可以在故事里看到自己,甚至得到慰藉。故事里有知识、有趣味、有情感、有思想,每个人在里面各取所需。考古和历史,恐怕是故事的一个最大源头。把历史比成大江大河,爱好历史、研究历史的人就好比到大江大河边上饮水的小老鼠,不求把一江水喝干,感觉自己喝饱就够了。这是每个人从过去获得经验、获得慰藉的一种方式。人们对历史感兴趣,知识需求是一方面,情感慰藉和人生经验的获取是另一方面。

求真、存真的原则和“祛魅”的愿望
主持人:许老师之前的著作《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都是大众学术书籍,写的都是考古发掘和研究对象。《发现与推理》是许老师写的第一本考古发现背后的故事,为什么选择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学术史?
许宏:我以前的书都是正论性的,写我的研究对象,可是我对学术史特别感兴趣。也许是随着年龄增长,从以前关注对研究对象的本体研究,慢慢转换到对认识论的兴趣上面,觉得有意思的不仅是我们发现了什么,更是为什么我们当时那么看、现在不那么看了,这个变化的动因是什么?
这些东西我本想放在退休之后来写,但疫情期间居然有了整块时间,几乎每一天都可以按照我的计划和安排来写东西、来做线上课,非常难得。所以三个月时间就将这本小书写出来了。人们对考古感兴趣,但考古里面似乎又有许多云山雾罩的东西,我本着求真、存真的原则写这些文章,本身有一种“祛魅”的愿望。加上我读郑嘉励老师的书,包括以前读西拉姆的《神祇·坟墓·学者》、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的《江城》《甲骨文》等,这些书都把“我”融进去了,有一种代入感。我觉得这种写法特别好,以前没有写过,所以想尝试一下。
主持人:听说上市不到一个月就已经加印了,许老师作为一位畅销书的作者,是不是对“加印”这两个字已经不太兴奋了?
许宏:加印当然是好事,自己的作品更多为大众所了解和读到当然是好事。我坚决要求出版社价格定低,让年轻读者和同学们能够买得起。之前《何以中国》印得最多,有几万册,现在这本书上市一个多月,大家反映比我以前的作品更好读,这是我比较高兴的。
主持人:郑老师和于老师已经看过这本书了,两位老师从许宏老师这本风格不一样的书里,有没有读出新的观点和有趣的角度?
郑嘉励:许宏老师在新书里跟我们分享了十几个考古故事。许宏老师刚才举了我的例子,实际上我与许老师比起来,他是一个纯正的学者,我很大程度上更像一个文艺青年,借考古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个人对社会、世界的看法。许老师很少抒发个人情感,即使有也非常克制,主要是讲考古学者怎样通过推理,如何从考古发掘的遗迹和遗物中还原历史现场。
许老师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我相信大家都认同,他认为考古工作者根据遗迹和遗物还原古代社会,跟法警依据作案现场的蛛丝马迹,推理、还原犯罪事实的道理是类似的。但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发现与推理》讲述了很多故事,有些推理是成功的,有些推理可以说是反面的案例,也就是刚才许老师讲所谓“祛魅”的工作。有句话说“考古考古,就是连蒙带唬”,不成功的随意推测,坦率地说,就是瞎猜、瞎蒙。

许宏(右一),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面向公众的著作有《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东亚青铜潮》等
考古推理要守纪律、讲规范、有边界
郑嘉励:我们知道,任何文物都是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历史背景的产物。但是时过境迁以后,早期的文物脱离了原先的历史脉络,成了一颗颗脱轨的流星。考古工作者的研究与科学推理,一言以蔽之,就是如何把脱轨的文物还原到它们原先存在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和历史背景中去。
对考古和历史学者来讲,判断一个人学术水平的高低,就在于谁能够把遗迹和遗物还原得更具体、更真切、更准确。不能准确还原,也就不会有可靠的推理,也不会有关于考古的好故事。因为讲述一个好故事,其实就是揭示一个真相。脱离轨道的流星,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好比慈禧太后一串项链中的一颗珍珠,如果这颗珍珠溢出了原来它所在的项链,就无法知道它原先的位置。而高水平的复原、推理,理论,就应该把这颗珍珠还原到慈禧太后项链中的具体位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揭示文物的真相,并赋予文物一个好故事。我认为,如果考古学需要理论的话,最迫切的理论就是如何从遗迹和遗物出发去推理、复原古代人类历史和社会的理论,考古推理要守纪律、讲规范、有边界。
我希望许宏老师把“考古纪事本末”的系列继续往下写,去探讨怎样建立起目前考古学最需要的一种理论——从遗物到复原古代社会中间不可缺少的理论,推理的边界在哪里、纪律在哪里、规范在哪里?结合具体的个案和故事,去讲哪些推理是成功的,哪些是不成功的。
主持人:杨照老师有本书《中国是怎么出现的》,里面提到一个观点和郑老师的观点可以呼应起来,杨照老师说:“培养优秀考古学家比培养任何其他学科优秀的学者更加困难,因为考古学的两面要求基本上是彼此矛盾的。”这个两面,一方面指考古是实证学科,需要考古学家有非常严谨的科学实践、理念和主义,但另一方面,也需要考古学家有浪漫和想象的能力。有时候这两面是相互抵消的,但如果这个度拿捏得好,两方面也是相互作用的。
郑嘉励:推理,最难的就是历史感和分寸感的把握。分寸感,这东西很难说清楚,但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就像空气一般的存在。推理过程,风险很大,结论下到何种程度,语言要拿捏到何种分寸,这种地方最见功力。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唐代两京地区的唐墓出土了很多陶俑,唐俑里一些高鼻深目的胡人俑,牵骆驼的,拉大弓的,都是男性,但是迄今为止一个女性的胡人俑都没有发现。假设唐代文献、全唐诗全被一把火烧光了,考古学家只能根据唐俑去推断,很可能就会认为当时从中亚来到两京的胡人,只有男性而没有女人。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李白的诗里就提到过很多的胡姬。如果我们因为唐三彩里没有女性胡人俑,就推测好像当时没有女性胡人进来,这不是笑话吗?但考古材料肯定反映了某一部分的历史真实,当时的人用胡人俑随葬可能是有选择性的,只选择男性俑。这大概就需要较好的分寸感。
二里头3号墓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细心、诚心和公心
于赓哲:说实话我对许宏老师一直很敬佩,无论是从他的专业论文当中,还是从他微博上的表现来看,我知道他一直在坚守学者的良知和底线。坚持原则并不容易,个中的辛酸和压力许老师自己知道。《发现与推理》特别能展现许老师的风格,什么风格?我总结为三个“心”:
一是细心。许老师不愧跟大众科普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考古小白”、一点不了解考古的人都能看懂这本书。许老师知道大众在想什么,也知道大众的兴趣点在哪里。比如对于什么叫探方、什么叫探沟,文物怎么装袋,都讲得很仔细生动。包括打洛阳铲,这真不容易。我人生第一次打洛阳铲是在北魏太极殿,人家打出来的是成条的,我打出来的全是豆腐渣。许老师很细心,照顾到不同读者不同层面的需求。
二是诚心。这本书涉及理论,但重点不在理论,而是涉及很多考古学的公案,有些是许宏老师亲历的,有些是学术界的公案。讲这种公案背后的故事并不容易,因为这些故事发生在不久之前,讲出来要做到不偏不倚、公正无私。这本书透露出许宏老师的诚心,而且他愿意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比如绿松石小狮子是不是二里头时期的?广州“造船遗址”是不是造船遗址?还有铜奔马命名的问题,大家说“马踏飞燕”是郭沫若给命名的,我看许老师的书才知道不是,它本来是甘肃省文化局一位文物口的干部给命名的,郭沫若对此认可,由此叫马踏飞燕。但现在看来这个命名是有问题的。还有周处墓铝片,那的确是一件很令人诧异的事情,能满足很多读者对于考古学背后故事的好奇。许老师能够把这些写出来,我相信他是有勇气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很多时候并不容易,这不是你在一个网上匿名发言那么简单。
三是公心,公正无私。预先排除自己的立场,一切拿材料说话,而不是先预设一个立场,然后拿材料找补。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历史学研究,预设立场是完全要不得的一种方式。先预设这个地方是什么城、是什么时期的,然后用材料找补,貌似能自圆其说,实际上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以后一定会贻笑大方。许老师这本书以及他以前那些学术专著,可以放心读,我相信许老师的书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主持人:可能熟悉许老师的朋友都知道,许老师在年轻的时候最想进的是北大中文系,成为一名写作者,也许想成为一名旅行写作家,像刚才许老师提到的彼得·海斯勒。虽然后来没有进中文系,进了考古系,但在考古领域做得非常棒,无论是学问还是做人,给学生、读者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
观史需要距离感
主持人:推理能力、想象能力对一位考古学家很重要,而究竟把这个想象力和推理能力释放到什么程度才是合理的?也请三位老师谈一谈。
许宏:这个问题确实像郑嘉励老师说的,度的把握非常重要。在命案现场、犯罪现场,材料是支离破碎的,如果完全没有想象力,就没有办法把它们连接在一起。但想象力不是建立在文学想象上,而一定是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积淀基础上,然后通过自己的经验、通过别人的经验把它连缀起来,这里面“度”的把握是很不容易的。
考古学是舶来品,是一门全新的学问,不是国学。郑老师说的“中程理论”也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的考古学前辈俞伟超先生是我非常敬佩的大师级学者,他具有前瞻性,比我们看到更远的中国考古学的未来。他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学方法论,也就是从物质遗存转化成大家都能通晓的话语系统、复原历史的阐释系统,这样的方法是“最考古”的东西。以前号称考古学的“两大车轮”——地层学(借鉴于地质学)、类型学(借鉴于生物学)都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的,郑嘉励老师说的“中程理论”反而是考古学特有的,这个从对遗存的分析上升到大历史层面的方法论非常重要,其中包含着我们刚才说的推理和想象,如何把握度非常重要。
于老师说我这几年发声不易,我跟于老师惺惺相惜。于老师看着温文尔雅,但是在网上比较犀利。他刚才讲的我心有戚戚焉,理解万岁。实际上,这本“考古纪事本末(一)”想写的还多,但有些不敢写不能写。有些故事得放到以后,观史需要距离感,放一段时间沉淀一下,可以说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娓娓道来。我的书有两个系列:第一是三联出的“解读早期中国”系列,马上要出《东亚青铜潮》,但还没完,还可以继续往下写;再就是“考古纪事本末”这个系列,我想继续写下去。感谢二位给我信心。
郑嘉励:考古需不需要推理和想象力?肯定需要,关键是分寸的拿捏。分寸感取决于学者长期的工作经验、阅历和学习。考古的工作对象,包罗万象,分解一下,其实主要就三个东西:一是聚落遗址,古人留下的城市、村落遗址;二是墓葬;三是手工业遗存,比如瓷器、铜器的作坊。其实,这些考古工作对象都是古人的日常生活或者生产活动的一部分。除非非常复杂的图像和记事复杂的文本,例如墓葬壁画背后的观念世界,简牍文书反映的政务运作,一般来讲,这些工作对象都是古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不过时过境迁,脱离了原先的历史轨道,后人不理解,以为很神秘。其实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种地放羊,本质上并不神秘。
越是迂回越是复杂越是错的
郑嘉励:我个人有一个体会,在推理过程中,凡是把考古遗迹、遗物对象解释得非常迂回、复杂、弯弯绕绕,通常都是错的。毕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底层逻辑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不该弯弯绕。举一个例子,汉唐宋元考古,墓葬是最常见的考古工作对象。主要有两种墓葬:一种是砖室墓,还有一种是宋代以后流行的石椁墓;而土坑墓在江南很少发现,在浙江,东汉六朝时期,几乎连一个土坑墓都没有。这个现象,当然应该解释。我发现很多人解释起来就特别复杂、弯绕,如果回归到底层逻辑,其实很简单,这就是孟子讲的“无使土亲肤”。什么意思?古人的丧葬,不能让泥土、地下水、地下的虫子直接接触亲人的尸骸,否则会被认为不孝。土坑墓,尸骸与泥土直接接触,这跟孝亲观念是冲突的。一个珍宝,大包小包包起来,亲人的遗骸也一样,小棺材以外,再套一个、多个的大棺材,与外界完全隔绝,这就是棺椁制度的起源。丧葬的底层逻辑就是孟子讲的“无使土亲肤”,但偏偏这个逻辑(考古界)很少去讲,考古工作者解释的时候,偏偏很复杂,都喜欢往魂魄、往轮回上靠,越是迂回越是复杂越是错的,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主持人:许宏老师《发现与推理》这本书里说到“1号大墓”的发掘,这里面体现出的观念其实和郑老师说的非常贴近,就是我们怎么样用自己的经验和对事物的认知去迫近当时的真相。
于赓哲:许宏老师写这些东西,能够把这些事情原原本本给大家说出来真的不容易,而且需要勇气。当时我们心目当中一直想找一个高等级的墓葬,然后在这个区域内发现了“1号大墓”(但后来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祭祀坑)。许宏老师的结论是,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墓葬,而很可能是一个水井,只不过水井的构筑方式比较特别,以致井筒的部分被认为是一个盗洞。被当作盗洞以后,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人骨、没有陪葬物,因为盗光了。许宏老师解释为水井,我觉得很有道理而且合乎逻辑,但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不是就降低了宫殿的意义。
许宏:等于把二里头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塔尖给削了,塔尖没了。
于赓哲:好像许宏老师矮化了二里头,其实许宏老师不可能矮化,而是希望每一个结论都能够站得住脚、经得住考验,而不是把结论匆忙做出来。如果过一段时间结论被推翻,岂不是对我们形象更大的损害?看“1号大墓”就能看到许宏老师在学术上的坚守,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情操在里头。
搞考古的不收藏
主持人:郑老师在他的《考古四记》里面说了一些公众对于考古工作的常见误解,我摘取了一下:第一,考古是挖宝;第二,考古人近于古董商,至少对市场行情有相当的了解;第三,考古人是老气的,至少与时尚相当隔膜。许宏老师和于赓哲老师是否认同这个观点?我们很想知道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心中,考古到底是什么样的学科。
于赓哲:大众对考古的确有很多误解,有人说考古是官方盗墓,这可以说是对考古工作者的一种侮辱。自打明十三陵定陵发掘出现较大问题之后,考古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主动的发掘。现在一个是给基建清场,另一个是给盗墓贼擦屁股。盗墓贼把墓葬破坏了,考古工作者不入场将残局收拾一下,岂不是对死者更大的不敬?考古绝不是以寻宝为目的,你问许老师是丁公文字陶片重要还是同等重量的一片黄金重要,当然是陶片重要。考古干的是抢救性发掘,你说考古工作者是官方盗墓,相当于说拿手术刀的大夫和拿匕首的劫匪是一类人,反正都是给人开膛。
说考古工作者是古董商,懂价格,其实文物真假对于考古工作者不是个问题,自己挖的东西,真假不知道吗?所谓真假是搞文物鉴定,文物鉴定和考古有关系,但也不能说是完全相同。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文物鉴定专家或者考古学家书房里面堆满了文物。搞考古的不收藏,好像是夏鼐先生定的规矩?
许宏:李济,考古学之父。
郑老师列举了有些公众对我们的误解,我当然是有同感的,按理说这样的话题我不愿意回答。正像一个外科医生不愿意跟人解释他不同于劫匪一样,按理说这应该是不言自清、不言自明的事。潘家园古玩市场大门朝哪儿,我根本不知道,没去过。我只知道一个东西的历史价值,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市场价值,而且只见过真的没见过假的,行话叫“只见过对的没见过不对的”。我的女儿上幼儿园时,老师让填表,发现我是考古学家,就找我说帮她的一位朋友看看东西。我骑着自行车去了那个高档住宅,那位先生很诧异,说你怎么骑自行车来,你只要往兜里揣两件,房子和车子全有了,世界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我说如果我真有别的想法,心就乱了,就不可能从事这样的职业了。甚至某国家级大媒体找我做读书节目,编导一开始还说:许老师,我们从盗墓开始讲吧。我非常反感。
我书里也写,考古的魅力,第一是发现之美,第二是思辨之美,是一种高级智力游戏。“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我的一位做哲学研究的朋友,是知名大学的学术带头人、哲学教授,他去了二里头之后写了一篇札记,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说,考古学是一门本原性学科,它能给其他学科甚至公众提供灵感和给养。这是我们学科最大的意义。
整理/雨驿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