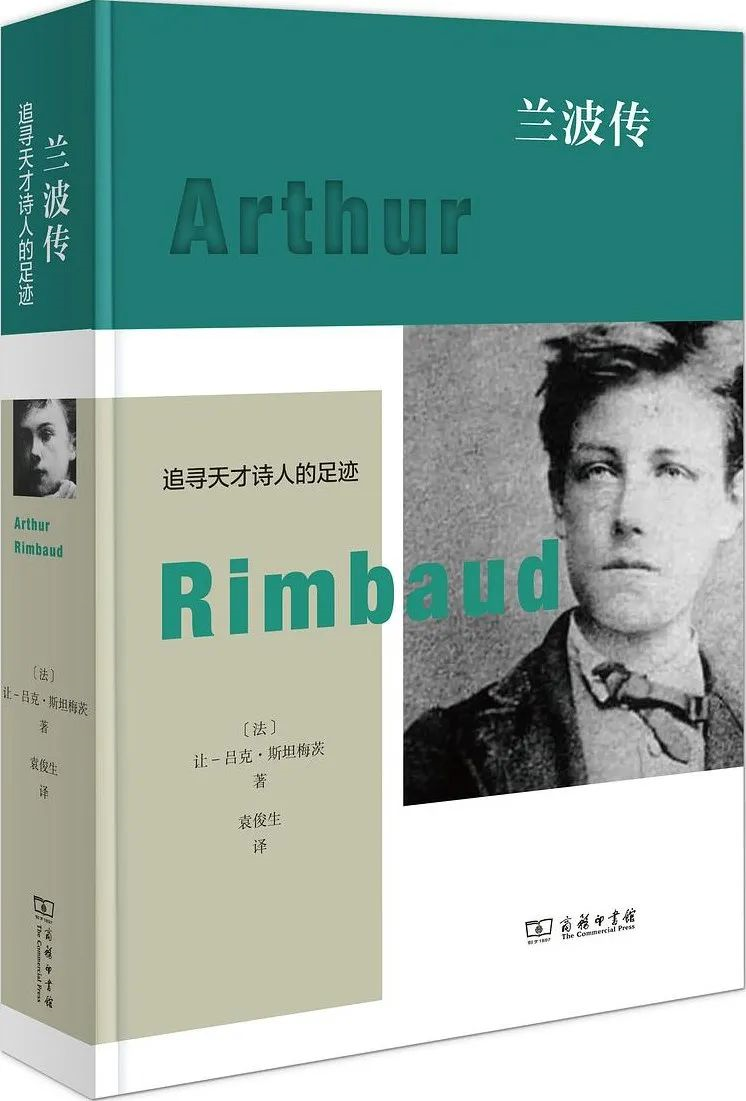19世纪法国诗人阿蒂尔·兰波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马拉美称他为“值得尊重的过客”,梁宗岱称他是文学史上“一闪而逝的流星”,他则自称“通灵人”,以《醉舟》《地狱一季》《灵光集》等诗篇震撼后世。从巴黎、伦敦,到布鲁塞尔、非洲大陆,兰波从未停止过逃离与漂泊。他用文字和旅行锤炼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让-吕克·斯坦梅茨集基于丰富的史料为兰波著传,更从思想上深入兰波的诗文与行动,以兰波的诗歌为蓝图、以兰波的书信为线索,将对诗歌的解读置于一切之前,为作为诗人的兰波提供开放的解释。
《兰波传》
[法]让-吕克·斯坦梅茨/著
袁俊生/译
商务印书馆2023年3月版
作品选读
跨越海峡那天风浪特别大,在七八个小时的航程中,“一对孤独的年轻人”,任凭海风吹打着脸颊,朝陌生的世界驶去。准确地再现他们当时的感受也许是一件很难的事,但任何想起兰波那时生活状况的人都不禁会想象,《醉舟》的作者与其创作素材相见时内心一定充满了爱意。后来在《地狱一季》里,兰波隐隐约约地提到那次跨海旅行:
我大概还要去旅行,要把聚集在我脑海中的魔法驱散掉。在大海上,我看见给人带来慰藉的十字架正从海面上升起,我爱那大海,它仿佛已把我身上的污秽洗刷干净了。
显然,没有任何准确的编年表可以证明这段文字写于何时。尽管如此,一个题材始终贯穿于《醉舟》和《地狱一季》之中,那就是洗刷污秽,清除负罪感的大海。兰波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他又可以反复吟诵:
绿水渗透了我的杉木船壳,
洗去蓝色的酒迹及呕吐物,
洗刷了我……
深夜里,船停靠在多佛尔港。两个伙伴找到一家旅馆。第二天一清早,他们就起床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到多佛尔城里去观光游览,但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实际上,那天恰好是个星期天,对英国人来说,星期天绝对就是安息日,他们费尽周折也找不到吃早饭的地方。况且他们对要讲一种外语而感到惊异,感到恼火。兰波一句英语也不会说,魏尔伦只能说几句最简单的话。他们毫不迟疑地离开毫无人气的多佛尔,乘火车赶往伦敦。透过列车车窗,他们看着秋天的景色,看着英国乡村的风景。接着,列车驶到伦敦的郊外,一座巨大的城市逐渐出现在眼前,城市上空覆盖着浓浓的烟雾。他们最终来到查令十字街火车站。和多佛尔一样,伦敦的星期天也显得十分冷清,饭馆和酒吧都不营业,大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到海德公园那边才能看见更多的人,有人在公园里做演讲,周围都是看热闹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两位朋友第一天都做了些什么。所有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都显得很新鲜。他们首先要考虑找到一处住所。离开布鲁塞尔时,他们随身带好联系人的地址,但9月8日这一天,他们好像在城里并未找到认识的熟人。
在接下去的几天里,他们设法和流亡在英国的法国同胞取得联系。就这样,他们找到了费利克斯·雷加梅,雷加梅的画室就坐落在朗汉姆街上,他和魏尔伦是老相识,曾为维尔麦希的书绘过插图,为“丑陋的家伙”晚宴绘制过请柬,与许多持不同政见的杂志合作过,比如安德烈·吉尔的《滑稽》杂志。他来到伦敦,继续从事画家的职业,为《伦敦画报》绘制漫画。雷加梅后来在回忆录里描述了这两位朋友来到他画室的情景。
1872年9月10日……在我屋外敲门的竟是魏尔伦,他从布鲁塞尔赶过来。他那身打扮还是很帅气的,虽然衣服穿得并不多,他好像一点儿也没有被命运压垮似的。我们在一起感到极为愉快。但他并不是一个人来的,一个同伴陪他前来,但此人一句话也不说,而且穿着也不讲究。
这人就是兰波。
当然,我们谈起过去的老相识。
看着我画画,魏尔伦来了灵感,从此我的绘画集里也就平添了两颗珍珠。
一个是“色当战败后的拿破仑三世”,另一个是“小皇储”。
每一幅画都配上几行滑稽的诗文,诗文模仿科佩的风格,放肆地签上浮夸的花缀签名,是约瑟夫·普吕多姆式的签名……
实际上,兰波虽然沉默不语,但后来还是为雷加梅的画集出了力,有关“小皇储”的那段诗文好像就是他写的,萨尔布吕肯获胜时,“孩子去捡拾子弹”。兰波当时显得很疲惫,像“昏暗的旅馆招牌”,雷加梅后来也给兰波画一幅画像,兰波坐在椅子上,头垂在胸前,昏昏欲睡,以至于人们只能看见他头上戴的礼帽。主人很快就把流亡在伦敦的法国人的消息告诉给来访者,尤其是把维尔麦希的消息告诉他们。见到维尔麦希的时候,兰波感到特别高兴,其实早在1871年3月,他就非常喜欢维尔麦希在《迪歇纳老爹》上所发表的文章。维尔麦希依然保持着刻薄、嘲弄人的性情,赏心悦目的小作品《诗咏花灯》就是这一性情的最好体现,这个作品对兰波的《与诗人谈花》有所启发。维尔麦希是一个“金发男子,稍微有点儿胖”,脸色看起来很健康,魏尔伦回想起不久前他们在一起合作的往事,那时他负责《金龟子,痴迷狂报》,两人常去拉丁区的咖啡馆里喝上一杯。聊天的时候,维尔麦希确认打算从霍兰德街34号搬走,那一带是平民百姓的街区。那间房的房东是个法国人,在维尔麦希的推荐下,事情很快就安排妥当了,魏尔伦和兰波马上就可以搬过来住。那幢楼房是亚当斯风格的建筑,窗户很高,还带有装饰,但室内则显得很昏暗。楼里所有的居室都被改造成带家具的出租房,空间显得有些狭窄,但房东的收益也会更好。尽管如此,房间倒不显得太寒酸。魏尔伦随身带的钱,再加上母亲定期汇过来的钱足够他们俩生活一段时间。
要描述兰波在那段时间的生活,就要求作者有一定的想象力。实际上,任何文字记载都没有留下来,甚至连目击者的点滴回忆都没有。最多只能从魏尔伦与好友埃德蒙·勒佩勒捷的通信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况且魏尔伦在信里很少提到自己的同伴,因为勒佩勒捷对兰波没有什么好感,而且曾多次挖苦兰波。
对于两位伙伴来说,尽管伦敦首先是某种新的发现,是代表着自由的都市,但他们依然摆脱不掉自己的过去。最初几天的惊讶,甚至惊奇感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实生活,他们要找工作,魏尔伦对自己的婚姻状况焦虑不安,因为玛蒂尔德已提出分居申请。兰波每天都要忍受这位“可怜的兄长”,因为魏尔伦无法原谅自己抛弃了那位“娇小的妻子”,而兰波则希望他能和自己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生活之中。魏尔伦的弱点是不可否认的,他始终不明白爱情是需要“再培育的”,依然固执地频频回顾那位孩子气十足的妻子,而且还在四行诗《黑夜中的鸟》里歌咏她。同时,他一直想念着小乔治,而他母亲已无权再去看望小孙子了。他反复琢磨莫泰一家人的做法,至于说尼科莱街,“我绝不会再迈进他们家的大门”。他在信中对勒佩勒捷这样写道,他委托勒佩勒捷为他的律师,全权处理他的事务,因为他坚信有人撬开他的抽屉,而抽屉里放满了他与别人的通信信件。在一份清单中,他将所有遗失的文稿罗列出来,这些文稿或者转交给玛蒂尔德的诉讼代理人居约-西奥奈斯特,或者被玛蒂尔德烧毁了,因为她对文稿中“丑恶的文字”感到愤怒。从此,魏尔伦和兰波又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了,但日子却过得紧巴巴的。尽管如此,诗歌却一直在神秘地守护着他们。
……
兰波一直在追求绝对的完美,唯有社会急剧变化才有助于实现绝对的完美。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证明《灵光集》写于何时,但所有的特征至少会让人们猜测,诗集的若干片段就是在那时写成的。整部诗集是在1874年誊写完毕的,但誊写本身也就意味着有些底稿恐怕早就写好了。某些段落倒更像是出自于空想,而非来自梦幻。《洪水过后》可以当作一个传奇故事来读,《圣经》故事经改头换面后糅合到这段文字里,但却寓意着深深的失望之感,他对旧秩序自然而然的重组过程感到失望,此文再次呼吁要掀起一场大地震,并希望看到一场大革命,以便彻底推翻过去的所有形式。《蛮子》及《战争》则以它们的方式描绘了这个新世界,“远离那些陈旧的避难所,远离那些陈腐的热情”。他的多篇文字似乎是受这种看法的启发而写成的。彻底转变人,转变习俗以及爱情已成为必然,而这一必然性已深深地埋在他的内心里,并与流亡在伦敦的某些公社社员的理想主义想法不谋而合。《灵光集》不可能归结于某种艺术灵感,虽然这种灵感就像是一座金矿。直到他写的最后几首诗,兰波一直在证明自己始终坚持着某种想法。相反,魏尔伦似乎忘掉了这种可能性,甚至考虑重新拾起过去所创作的诗篇,比如《失败者》,以便能在《未来》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他过去就曾设想以《失败者》为主编辑一部诗集。兰波与维尔麦希及安德里厄等人的关系是不容置疑的,虽然人们无法推测出他们之间更确切的交往活动。人们不妨去听听《灵光集》里的“声音”,那声音见证了一种挑战式的气氛,见证了一个回顾过去的严厉目光,见证了一个未来激昂的视野,那是一种绝对的、几乎带有神学色彩的视野,就像那个想象中的“理智”一样,想象者亲手去“推动新的和谐”。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