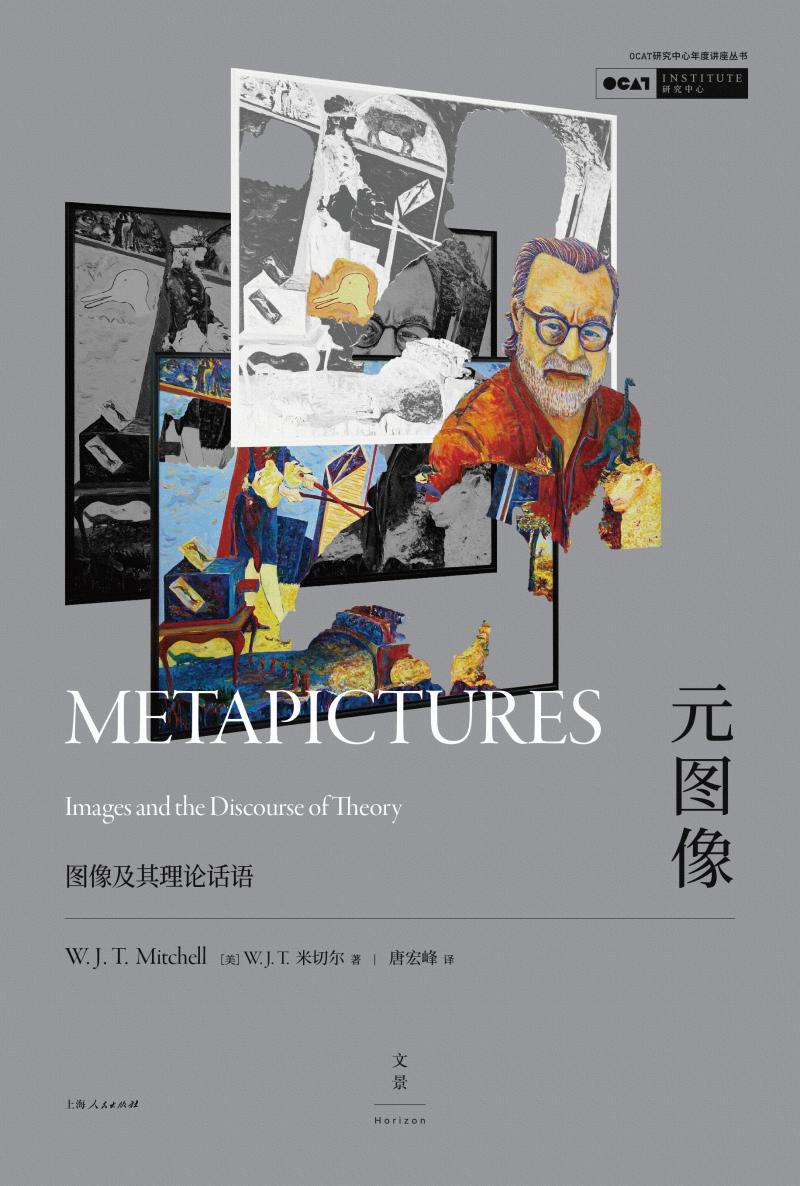图像学只不过是在研究我们人类的一种不可救药的倾向——不断复制自己和世界,这些图像能够同时产生知识和无知、可信的再现和不可信的幻觉。有经宗教对图像制作保持深刻怀疑,所以第二诫命禁止各种造像,因为人们会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倒,拜它为神。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理论效仿了宗教传统中去偶像化的方法,质疑马克思所谓的“意识形态暗箱”(camera obscura of ideology)中投射出来的集体幻想。科学和技术梦想着控制我们的图像,用它们为真理、权力以及人类繁荣服务。艺术则跨越所有这些边界,探索图像在情感、感官和认知层面的可供性,用各种图像群组进行思考和分析。他们把尼采的明智建议付诸实践,用锤子敲击偶像,不是为了粉碎它们,而是为了制造声响以揭示其中空的实质。通过追随尼采的下一步动作,图像学用音叉代替锤子,使我们的批判的和历史的语言与其所涉及的图像产生共鸣。
那么,什么是“图像学3.0”?我的回答只能是试探性的、推测性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的。对我来说,第一阶段的“图像学1.0”是通过摄影的发明和诸图像的一个全球跨文化图集而成为可能的。瓦尔堡的《记忆女神图集》是这一试图将图像世界总体化(totalize)的最显著案例。在潘诺夫斯基的努力中,图像学这门古老的学科重获新生,他展望出一种在不同媒介中追索图像意义的解释学领域。当艺术史突破了纯美术的限制,扩展到通俗图像和观看的日常实践,其本身就已为一般性的图像科学和“视觉文化”这一当代研究项目打下了基础。电影和电影研究使图像运动,揭示出图像其实一直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同时也动员和感动着观众。哲学和批判理论同样超越了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描述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去探究一种“图像转向”,在这种转向中,图像在认识论的、伦理的和本体论的问题上起到了核心作用,远远超越了美学的传统中心地位。【1】在我作为图像学家的早年经验中,图像和符码(code)之间的关系起着核心作用,符码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作为解释的关键,二是作为罗兰·巴特称之为“没有符码的讯息”的摄影的对立面。20世纪80年代,符号学、解构主义、现象学和批判理论似乎同时转向了以图像为其研究的核心对象,而数字图像的出现似乎证实了档案的新可能性,这个档案正在远远超出以模拟讯号和化学物质为基础的摄影的范畴。对一些人来说,这似乎意味着模拟性有消失的危险,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只意味着由于新的技术可供性的出现而使得这一切都在加强与激增。
在我看来,“图像学2.0”是信息科学和“数字—模拟”这一辩证关系与生命科学融合的产物,第一批“活像”开始作为大众文化和科学实验室的显著特征出现。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被取代了,不是被数字技术,而是被使克隆成为可能的生控合成、被对活物的活像的复制所取代。我们或可称这种活像为“生物图像”。
“图像学3.0”即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和其他那些试图以一种清晰的批判来把握历史时刻的人一样,我发现自己陷入了矛盾的漩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3.0并没有把过去抛在脑后,而是收集了所有以前时代的化石,并根据我们现有的新情况使它们重新变得生机勃勃。我不能肯定地说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元图像,或“图像之图像”(image of images),也没有规定只能有一种。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些候选者,主要是图像与物质状况在法证科学中重获新生的连接,以及作为克隆体的后继者及图像焦虑的主要对象而冉冉升起的“数据替身”。我想在这些考虑中引入一个新的关注点,对一个非常古老的主题的新关注—在新的语境中重新思考“世界图像”,不把世界视为“一切发生的事实”(all that is the case,呼应维特根斯坦),也不像海德格尔想象的那样,将其视为技术傲慢的病态症状。这个新的世界图像并没有把我们的世界描画成一个可被总体化的实体,而把焦点放在这个作为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之边界的星球栖息地上。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称之为“盖亚”(Gaia)原则。【2】我想把它与“愚人船”(Ship of Fools)的古老隐喻联系起来,并在“地球飞船”(Space ship Earth)这一巧妙比喻中对后者进行重新解释。这种说法提醒着我们,我们的星球是一个漂泊的岛屿,一片不宜居的虚空之中的一艘不稳定的船只,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称之为“时空之海”(Sea of Time and Space)。在我们脆弱的小岛、我们的愚人船上,海洋正在上升、沙漠正在扩大。如果我们找不到超越人类这一物种之愚蠢本质的方法,我们将像恐龙一样,最终只不过是另一种无法适应环境的生命形式的化石遗迹。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元图像可能必须在一种比人类历史更深远的时间内形成,即一种现时的古生物学(a paleontology of the present)。【3】
【1】参见拙作《图像理论:语言与视觉再现文集》(Picture Theory: 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中以此为题的文章,以及另一拙作《图像转向》(The Pictorial Turn, ed. Neal Curti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参见布鲁诺·拉图尔,《面对盖亚:关于新气候状况的八场讲座》(Bruno Latour, 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New York: Polity Press, 2017)。
【3】关于此概念的讨论,参见拙作《最后的恐龙之书:文化偶像的生命与时代》(The Last Dinosaur Book: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Cultural Ic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来源:文景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