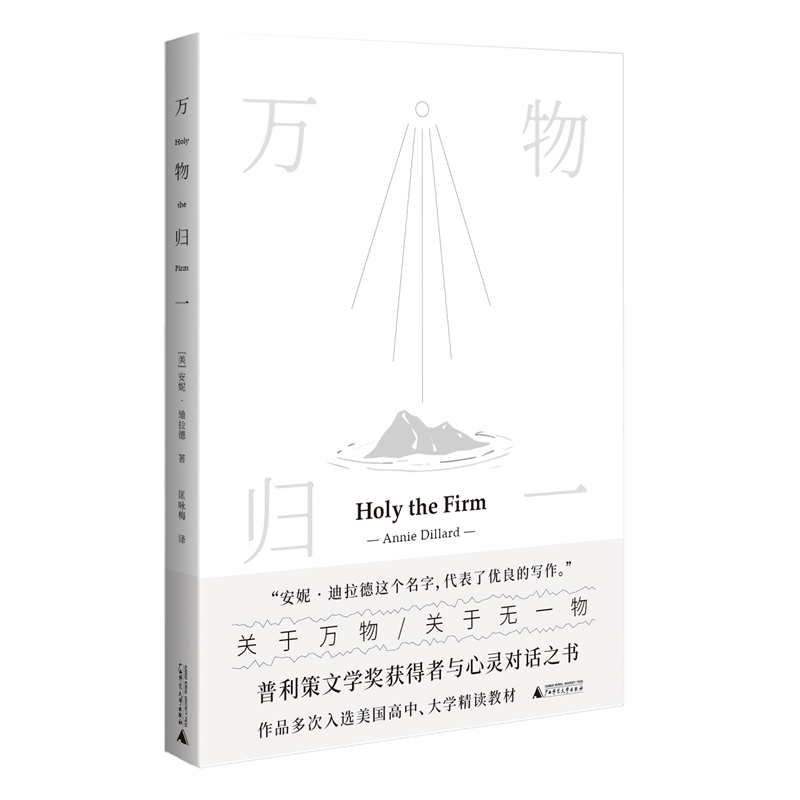安妮·迪拉德是美国自然主义作家,曾以《听溪客的朝圣》一书获普利策奖。迪拉德关心生死,关心大自然,思索神秘的现象,许多环保人士誉她为当代的“梭罗”和“爱默生”。
1975年,安妮·迪拉德独自来到美国西海岸,在普吉特湾的一个岛上居住。她住在一个简单的木屋里,里面的陈设只有“一扇偌大的窗户,一只猫,一枚蜘蛛和一个人”。这之后的两年里,她不断地追问自己各种问题,关于时间,关于真实,关于奉献,关于死亡,关于上帝的意志。在散文集《万物归一》(Holy the Firm)里,她写到了一只被烛火吞噬的飞蛾,写到了一名飞机失事后烧伤了脸的七岁女孩,写到了冰冷的海滩上的一次洗礼。但是,在变幻莫测的风景“幕布”后,在她所谓的 “硬实的东西——岩石山和咸水海”后,她看到的却是圣火的力量。
《万物归一》[美]安妮·迪拉德 / 匡咏梅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上海贝贝特 / 2022-5
蛾子锲而不舍地扑向烛火。嘶嘶作响,触火即退,翻转着消失在厨用平底锅的阴影中。或者,让火燎上了身,落下来,热辣辣的翅膀,好像要融化了,碰到什么粘上什么——平底锅,锅盖,汤匙——如此这般,粘住的蛾子只能小范围内扑打着,没法飞也跑不了。
碰到这种情况,我会拿根棍子,轻轻敲打一下器物,让蛾子们解脱出来 ;早上的时候,我会发现厨具上镶满了扯碎的蛾翅留下的金色斑点,铝制品上到处都是亮闪闪的粉末三角形。我就这样读着书,烧着水,更换好蜡烛,接着读书。
某个晚上,一只蛾子扑进了烛火,让火给逮住,烧干殆尽。当时,我肯定是盯着烛火的,要不就是那一道阴影划过书页时我抬起了头 ;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看到了蛾逝的整个过程。一只金色的雌性蛾子,很大的一枚,翼幅展开足有两英寸长。她扇动着翅膀扑进了火,腹部落入了烛泪里,粘上了,烧起来,动不了,几秒钟内就被烤干了。她那舞动的翅膀,就像棉纸一样烧起来,放大了烛火的火圈,让黑暗中我毛衣的袖子、身边金凤花的绿叶和松树皱巴巴的红色树干瞬间一蓝。很快,烛火又重新聚集,蛾翅化作一缕青烟散去。与此同时,她的六条腿蹬了几下,蜷曲起来,烧黑了,不动了,最终消失殆尽。她的头猛力地抽搐着,发出嘶啦的响声 ;触角变脆烧化,厚重的口器噼啪一响如同发令枪一般 ;当这一切结束时,她的头,据我判断,就像她的翅膀和腿一样已经烧没了。她是一枚新蛾子还是一枚老蛾子?她交配过吗?产卵过吗?她完成她的使命了吗?此时此刻,剩下的只是她胸腹部亮闪闪的角质壳——残缺的,烧得塌陷的一段金色条状蛾身,直直地挤在烛泪形成的凹陷里。
于是,这蛾子的精髓,这炫目的骨架,变成了一根烛芯。她不断地燃烧。蜡油没过蛾子的身体,从腹部到胸部,从胸部到参差不齐的洞口(原先那里是头部的位置),扩展融成火苗。一簇橘黄色的火苗包裹着她,投到地上的影子仿佛焚身于火焰中的僧侣。蜡烛有了两根芯,两簇同样高的火焰,肩并着肩。僧侣的头就是火。她持续烧了两个小时,直到我吹灭了她。
她持续烧了两个小时,没有变化,没有弯曲,没有倾斜——只有里面亮闪闪的,就像是瞥见投影到墙壁上的楼房失火,就像一个空心的圣徒,就像一个火苗脸的处女追随上帝而去。我就着她的光读着书,思绪纷飞,巴黎的兰波在一千首诗歌里烧光了自己的大脑,夜在我的脚下湿漉漉地聚集。
所以,我才相信,浴室地板上的那些中空的松脆物就是飞蛾。我想我认得飞蛾,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我都认得蛾子的身体部件,认得完全干空的蛾碎和蛾屑。你们中有多少人,我曾问过班里的学生 ,你们中有哪些人想倾其一生去当作家?当时我颇有些紧张,四周全是咖啡、烟卷和近在咫尺的面庞。(这是我们生活的目的吗?我心中暗想;任意光线下的任意肤色,活生生的人,人类的眼睛,这就是那唯一的最终的美吗?)所有的手都举起来回答问题。(你,尼克?你说说?玛格丽特?兰迪?我为什么要让他们说实话?)随后,我试图告诉他们,那种选择一定是意味着:你不能成为别的什么人。你必须披荆斩棘,全力以赴……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有两只手,不是吗?打从我记事起,我就有这种干劲儿。晚上干,滑雪后干,从银行回家的路上干,在孩子们睡了以后干……)他们以为我又在胡言乱语吧。管它呢。
草木改建的桌子上,我放了三根蜡烛,有客来访的时候就点起来。小不点儿通常会躲着蜡烛,但有一次靠得太近了,尾巴扫到了烛火上;我没等她察觉到就赶紧拂走她的尾巴。烛火晃动照亮了每个人的皮肤,在朋友们的脸庞上打下了光影。当人们离开,我从来不会吹灭蜡烛。我睡着了以后,它们依然燃烧着。
文 | [美]安妮·迪拉德;译 | 匡咏梅
来源:贝贝特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