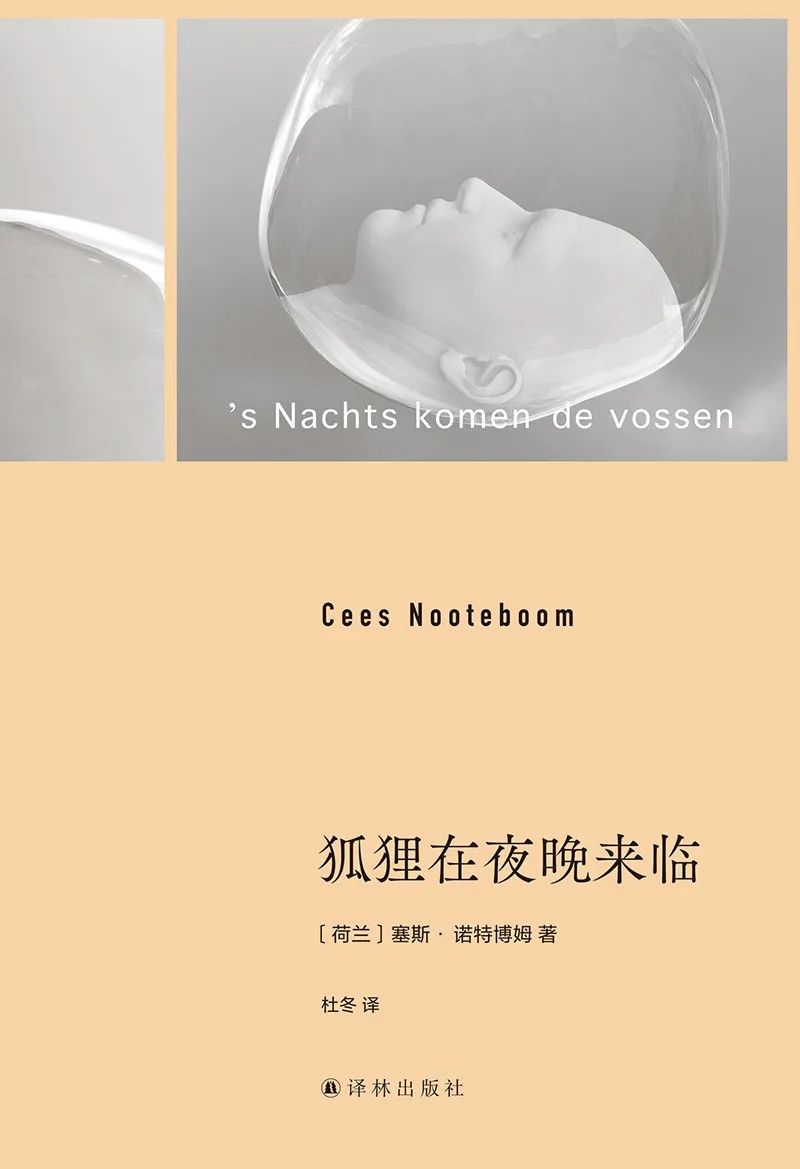随着《在荷兰的山里》《下一个故事》《万灵节》《失乐园》等小说的相继发表,荷兰作家诺特博姆声誉日隆。后现代作家、诗人A.S.拜厄特称他为“最伟大的现代小说家之一”。而在诺奖得主库切眼里,诺特博姆吃亏的地方在于,他太聪明、太世故、太冷静,以至于无法完全投入现实主义充满幻想的无限乐趣之中……显见地,库切难掩其对诺特博姆小说浓厚试验和先锋特色的赞赏之情。
近期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集《狐狸在夜晚来临》、游记《西班牙星光之路》。如此,即使诺特博姆依然小众,也终究是中文世界里“熟悉的陌生人”了。
1
“我想,让他自杀了事,我就不必自己写完小说了。”日后,荷兰作家塞斯·诺特博姆谈到小说《骑士已死》的写作过程时,曾做如是感慨。引言中的“他”是小说中的一位作家,或许是诺特博姆的化身。“他”决定接手写完一位荷兰作家因自杀身亡而未竟的小说,于是“他”从这位已死作家留下的笔记的片言只语中将小说的情节一点点拼接起来,作家的生平也随之慢慢呈现。诺特博姆最后没有让“他”自杀,小说在划上最后一个句号后完美谢幕。
然而让诺特博姆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整整十七年后,他才从这部小说的死胡同里走出来。待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诺特博姆迎来的是沉甸甸的收获——给他带来巨大国际声誉的小说《仪式》。或许,让他更感意外的是,即使相隔十七年,他的小说并没有失去《骑士已死》中所凸显的先锋和实验色彩。
此后,随着《在荷兰的山里》《下一个故事》《万灵节》《失乐园》等小说的相继发表,诺特博姆声誉日隆。后现代作家、诗人A.S.拜厄特称他为“最伟大的现代小说家之一”。而在诺奖得主库切眼里,诺特博姆吃亏的地方在于,他太聪明、太世故、太冷静,以至于无法完全投入现实主义充满幻想的无限乐趣之中……显见地,库切难掩其对诺特博姆小说浓厚试验和先锋特色的赞赏之情。
事实也是如此,诺特博姆总是被看作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纳博科夫的同类。如有网友所说,他写的是那种你会动不动就拿出小本子记上几句的“思想小说”,思辨色彩浓厚,情节却不出彩,倒像是存了心不让你拿起来就放不下的。所以他是文学界小圈子的熟脸客,却是大众市场的陌生人。好在译林出版社继前些年出版《仪式》《万灵节》《流浪者旅店》之后,近期又出版了他的小说集《狐狸在夜晚来临》、游记《西班牙星光之路》。如此,即使诺特博姆依然小众,也终究是中文世界里“熟悉的陌生人”了。
2
谈及自己的创作,诺特博姆曾激动地声明:“我哪里会去在乎情节!谁会去在乎情节呢!以情节见长的作家成千上万!”诚如作家本人所言,诺特博姆的小说因为情节散淡屡屡为一些读者所诟病。然而正是得益于其散淡情节所串联起来的深邃的哲学思考,他也因此备受赞赏。
诺特博姆最受关注的小说《仪式》,就是一部关于秩序与混沌、生命与虚无的小说,是一个敏锐而充满智慧的寓言。小说开场是1963年深秋,主人公伊尼·温特罗普在妻子弃他而去的那天上吊自尽。时间回溯到10年前,伊尼漫无目的的漂流让他先后遇见了两个人——塔兹父子。他们过着仪式化的生活,与外面世界格格不入。父亲憎恶人类,离群索居,生活严格按时钟进行,连他最后的自杀也不例外。儿子沉浸于古典日本文化之中,冥思苦索的生活、仪式化的死亡是他的理想。他耗费了一生积蓄,买到一只理想的乐茶碗,在茶礼结束后,他打碎了茶碗,然后沉水而死。
一对奇怪的父子,艺术化的自杀手法——如果说《仪式》的情节还可以吊吊读者的胃口,《万灵节》的故事则乏味得让人郁闷。通篇故事写一对男女在柏林一段温温吞吞乏善可陈的爱情,相处时间加起来不到三十个小时,竟写了洋洋洒洒二十多万字。小说的书名“万灵节”是西方的一个宗教节日,在万圣节的次日。该节日纪念死去的信徒,其罪尚未洗净,还不能上天堂。在这一天,人们相信亡灵会归来。故事的主要场景并不是发生在万灵节,然而主人公阿瑟·唐恩倒像是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节日——半明半暗、阳间和冥界的交错之中。
如其所示,诺特博姆的小说情节并不曲折,甚至有时候显得沉闷,他在寻常事物中灌注的哲学思考却颇为精彩。在《仪式》中,我们能看到对时间记忆的感悟、关于宗教的对话、对存在问题的争辩,甚至是关于瑜珈的议论。书中涉及到的人类仪式,至少就有基督教圣餐礼、苦修会的冥想、伊尼的割礼、犹太教的明耶、佛教的入定、日本茶礼等,每种文化、每段人生都与一些仪式紧密相连。
《万灵节》亦是如此。故事的每个枝节都被作者用来连缀自己思绪的片段。阿瑟的“狐朋狗友”在酒馆里的胡侃,或是阿瑟自己在柏林雪地漫步时的遐想……谈论、思考的话题从奥德修斯的远航,到尼采抱着驴子哭泣;从冯·宾根的音乐,到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画作,难以穷尽。无怪乎澳大利亚《世纪报》在向读者推荐诺特博姆的小说时称:读他的小说,最好带一本百科全书。
诺特博姆可不会为自己的书难读而感到抱歉。他在接受采访时辩解道,一本书写得过于复杂确实会丢失掉一些读者,但我的一些书写到艺术家、哲学家这个复杂群体,那这本书就应该是复杂的。“我不希望写一本很简单的书,但要是能写一本让读者绞尽脑汁的书,那也不错。”
不管怎样,相比他的长篇,《狐狸在夜晚来临》还是要简单一些,里面八个故事,就像作家赵松说的那样,其中的主要人物多数都是生活在异国他乡的荷兰人。而且,诺特博姆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无论以何种方式呈现他们的命运,都会赋予他们只有在异国生活的情况下才会有的某种气质。“无论他们的命运以何种方式在哪里展现,其实都暗示着类似的生活状态,那就是漂浮。 ”
3
在一次访谈中,诺特博姆坦言:自己的写作来自于旅行见闻。此言不虚,诺特博姆一生热爱旅行,游踪遍及大半个世界,单是住过的旅馆就让他写成了《流浪者旅店》。他说:“宾馆里的房间不计其数,在每一个房间里,我都写了一些东西,因为我的很多前期工作在旅行中就完成了。”
而诺特博姆的作品开始为中国读者所知,也正是源于新译名为《西班牙星光之路》的那本《绕道去圣地亚哥》。诺特博姆说,他从来没有这本书当成书来写。“我常会回头去写圣地亚哥。对我来说,它是西班牙的精神首都。西班牙就如同不同国家的结合,只是通过这个地方汇聚在一起,因为它是西班牙守护者、使徒雅各的埋葬地。我只是一篇一篇地写,没有想到它会成为一本书。不过最终还是成了一本书,但是我想这书也会原谅自己吧。”
与此相仿,《流浪者旅店》也可以说是系列文章的结集。在这十四篇游记性的散文里,诺特博姆写到欧、亚、非、澳四大洲的多个城市。与小说一样,诺特博姆的游记里,也包含了太多传统“游记”中不会具备的哲思和情绪,因此传统的“游记”写法也注定承载不了这本书的内容,于是他选择了一种近似于意识流的手法进行叙述。作为游记作家,诺特博姆也以他独特的叙述,深入到历史、文化的幽深之处。以有评论的说法,他的游记相比玛格里斯、布瑞南、弗莫尔以及莫里斯等以写游记见长的作家也毫不逊色。
这位五十多年来行踪不定的作家,在人生之初,却不见有多少不寻常之处。他1933年生于海牙,幼年时父亲即死于二战空袭,母亲后来成了一位“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徒,他被送入教会办的学校寄读,前后多所,有圣方济各会的、圣奥古斯丁修会的,但都因其个性难以适应教会学校的约束而未能毕业。1951年,他开始在希威散一家银行工作,1953年因为太瘦弱入伍不成,转而开始游历欧洲。两年后,他发表处女作《菲利普与他人》,小说讲述主人公在地中海的漫游故事,而又包含了一段重要的中国奇遇,作品随后获得了安妮·法兰克奖。次年出版诗集《找寻家的死者》之后,获得旅行资助,从此,诺特博姆真正过起了漂泊不定的旅行生涯。多年的旅行,也让他对世界许多地方的文化有着直接而深入的体验,加以他博古通今,遂得以在人类文明的广袤时空中任意驰骋。
或许,正是因为长年自由穿梭于欧洲的各国文化之间,诺特博姆的小说始终保持了丰富的张力。他的作品常常着力于关注非现实性的问题,如时间的短暂、记忆的飘忽、现实与思绪的朦胧,其文学主题包括死亡、自我的神秘性以及现实与幻想的关系等,充满了思辨的哲学意味。
而对表现形式的不断探索,则使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实验性,他采用《天方夜谭》《变形记》等文学经典中的框架叙事手法结构小说,而各叙事层的写作又大都具有不同的风格,故事中嵌套故事,随着故事推进,框架叙事与各嵌入叙事逐渐融合,甚至死去的人物也要活在其后裔里,最终参与叙事的融合。恰如有论者所言:诺特博姆以他独具一格的创作,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找到了自己坚实的位置。
译作选读
《狐狸在夜晚来临》[荷兰] 塞斯·诺特博姆/著;杜冬/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9月版
贡多拉小舟令人思古。当他读到这话时,他并不明白,即便现在他也不愿意想,生怕会失去此刻的忧伤。太阳西垂,雾气蒙蒙的潟湖上有一条黑色的贡多拉,如同飞鸟般的剪影,低矮的系船柱如同孤独的方阵大军,在远方逐渐隐去,仿佛受命要前去杀戮和摧毁,他则静静地站在斯基亚沃尼大道(Riva degli Schiavoni)之上,手中握着一张快照,已经发黄并撕去了一半——这的确够得上悲怆吧?他们的贡多拉当时到港的地点大致就在这儿,他们走上岸的地方就在那儿,在台阶那,或者是更远处的台阶,靠近一尊被杀害的女游击队员的雕塑,半没于水中。当时的天气和今天相似,即便从快照上也看得出来。他们正坐在台阶上,就来了一位年轻的军官,指着标志说这里是水警专用码头。如今他只需要找到那块标志,想来不会太难。
可如果我找到了,又能如何?我就会和四十年前的自己站在同一个地方,那又如何呢?他耸耸肩,仿佛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本来就无可如何,他想,这才是其意义所在。
为了进行这次奇特的朝圣之旅,他还同意了为葛拉西宫(Palazzo Grassi)的演出写点东西。现在去哪里?去寻找幻影,不,连这也谈不上,去寻找一片空白。他很轻松就找到了那些台阶,如今依然是水警的泊地。古老之城都不会轻易改变,那块标志依然在,钉在一侧的砖墙上,不过最近刚刚重新漆过。他在最高的台阶上坐下来。当时那位年轻的国家宪兵队(Carabinieri)军官如今恐怕早已退休,可即便这四十年里他青春不老,也未必能认出这位坐着的老者了。手中的快照是一位不知名的路人所拍,他背朝不远处的潟湖,以三十度的角度拍摄,这样就能把总督宫(Doge’s Palace)一同摄入画面。凑近细看,他不由得赞叹照片多么会说谎。不但能召唤起死者,也能让你和多年前的自己面面相觑。照片中的自己是一个长发的陌生人,如此有当年的味道,甚至能勾起早已消逝的前尘往事。
所拥有的依然是同一个身体——这真令人吃惊。可这绝对不是同一个身体。身体上附着的名字并未改变,这或许是唯一的共同点了。
他深思着,这张照片所真正承载的,与其说是忧伤或顾影自怜,倒不如说是一份声明,是否就在那时,他开始思考隐退。他坐在她的左边,她微笑着转脸朝向那不知名的摄影师,从额前拂开红发,弯腰抵着墙,将标记遮住一半。他看下去,灰暗的海水在低处的台阶上盘卷。一切依然是旧时情景,真令人吃惊!海水,如同鹭一般的贡多拉,他所坐的大理石台阶。只有我们才会退场,他想,我们将一生的种种风光抛在身后。他抚摸着身边凹陷的石面,似乎在感受她留下的空白。他清楚,在此情此景下,心头涌起的无非是老生常谈,可这谜团却永远无解。现实和完美本是一回事——现在他懂得这话究竟从何而起了。很难说黑格尔所暗示的,是否是当下这样的情景,只是当下如此应景。一切都是偶然而生,绝无可能视其为理性,这想法莫名其妙地让他如释重负。死亡本是自然的礼物,却时常会带来如临深渊的伤痛,你恨不得自己也坠入深渊,向死亡之谜的惨淡与真实投降认输。
这一切的开始平淡无奇。希腊的小岛,朋友的朋友的房子,借给他住是可怜他刚刚离婚,还没有习惯独居,渴望女人的陪伴。海岸边有一条步道,闲逛的、漫步的女人都从这里走过,他渴望上前搭讪,却又不敢,担心女人们笑话他,把他当作呆子。他的朋友温特罗普过去总把搭讪女人叫作“Ankatzen”。这说法并没有错,可他却总是做不好。鲁塞伯特(Lucebert)的诗句是怎么说的来着?长夜独漫步,窈窕兰舟过千帆。至少这一句很是真实。踱去踱回,踱去踱回,漫步,闲逛,观望。许德拉的雕像,渔船,在沉黑的夜里更加苍白,港口中高大的钠灯照耀下,轻轻随浪摇摆。还有燕子、柏树——但或许这都是他的想象?当时那里就有了钠灯吗?不过,记忆又何必强求准确呢?就当那是黄色的电灯,听到的是夜枭的啼叫,看到的是松树的黑影好了。唯一不变的只有轻拂码头的大海,其余的一切都可改换,是装饰你记忆的道具。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