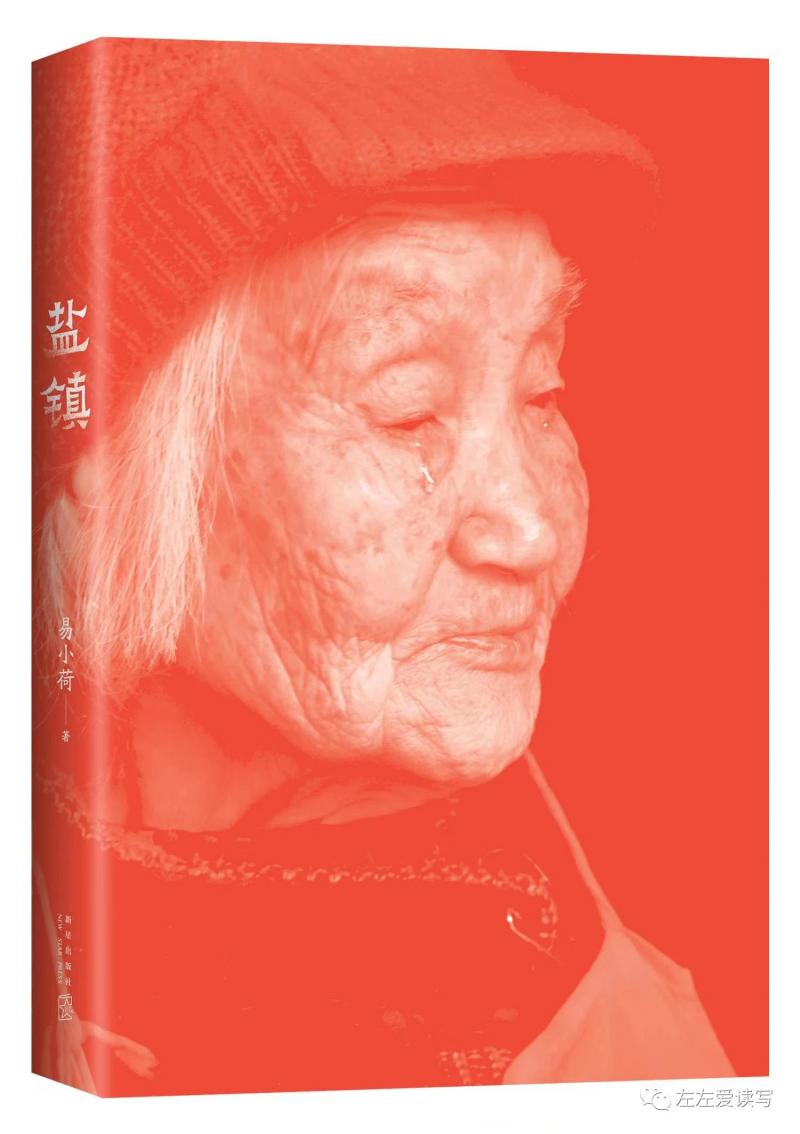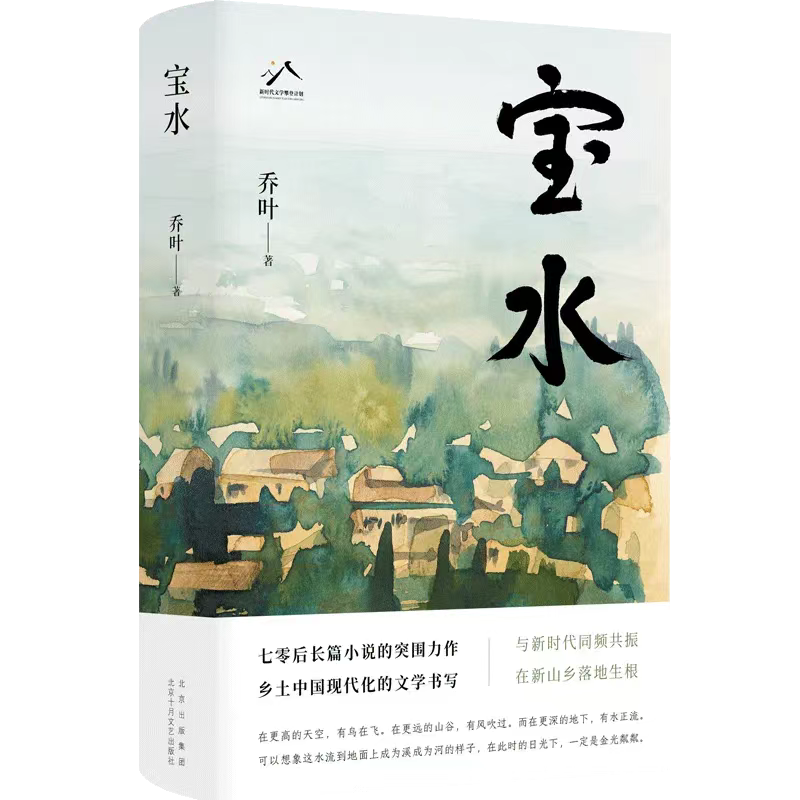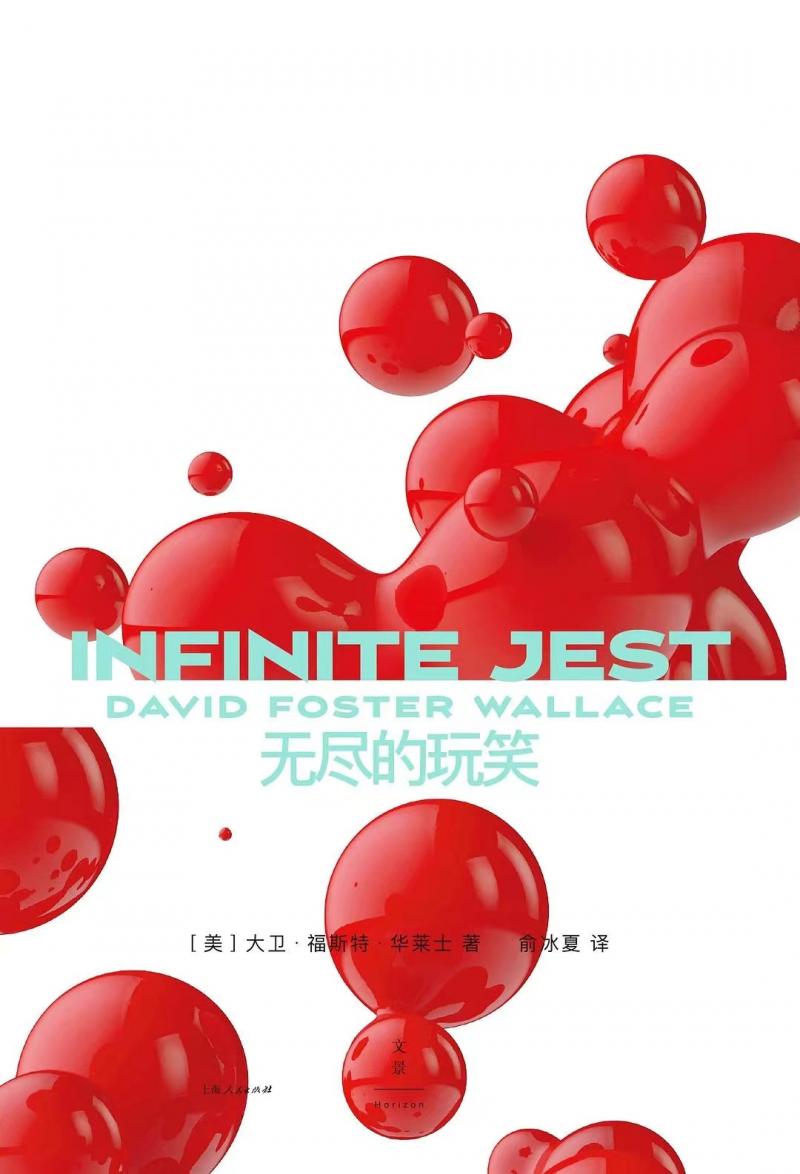主题:女性在当下
时间:2024年4月20日
地点:浙江文学馆
嘉宾:易小荷 前媒体人、作家,《盐镇》作者
乔 叶 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长篇小说《宝水》)
俞冰夏 译者、作家
萧 耳 作家、前媒体人
主持:徐 洁 视频号“徐徐叨来”主理人
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上野千鹤子说:“女性是一种处境。”从波伏娃到上野千鹤子,几十年过去了,当下女性的处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依然要讨论女性主义?
4月20日,“看见·未见”第12届春风悦读榜文学沙龙在浙江文学馆举行。作家易小荷、乔叶、俞冰夏、萧耳围绕“女性在当下”进行了对谈。
“女性是人类进步的永恒”
徐洁: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上野千鹤子说:“女性是一种处境。”从波伏娃到上野千鹤子,几十年过去了,当下女性的处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依然要讨论女性主义?
接下来,我们进入“看见·未见”第12届春风悦读榜文学沙龙的最后一个单元“女性在当下”,有请第三组嘉宾作家:乔叶、易小荷、俞冰夏、萧耳。能不能结合自己的创作聊一聊对“女性是一种处境”这句话的理解?
易小荷
易小荷:刚才来的时候我仔细看了一下,现场应该是女生居多。我想起今年有一个做出版的朋友跟我讲,他们有一个私底下的统计,大部分文学活动或者文艺类的活动,一般来说女人是偏多的。我不由想起了另一句话——“女性是人类进步的永恒”(笑),我先赞美一下我们女性。
《盐镇》出来之后,我获得了一些荣誉,包括我很感谢组委会给我这个奖(春风悦读榜女性奖),但我不会刻意给我自己贴一个标签,觉得我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写作者。
我写《盐镇》的时候,并没刻意去做女性主义写作,我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一再说:“我觉得在任何一个社会,女性和动物都是打开这个社会最好的一个切面。这是我为什么选择女性群体的原因。”当然了,一个作品写出来就会有自己的命运——每个读者读出的东西不一样。我不会拒绝别人怎么去分析它,但我不会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
今天我也不想给各位灌输什么女性主义的理论,只是从一个女性写作者的角度分享一些自己的经历。
在此之前很多年,我其实很懵懂。这两年上野千鹤子很热,包括大家会读波伏娃,可能会更多接触女性主义的理论。但在此之前我们不大会去思考,女性在工作中有没有受到过类似不公平的待遇?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前是做体育记者的,有一年跟国家队去欧洲打夏季联赛,一个特别漫长且特别炙热的赛季(当时是为世锦赛做准备,所以整个赛程特别累)。当时只有我一个记者,所以我跟着国家队就西班牙什么的各个地方到处走。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中间休息吃饭,有人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易小荷,你以后不要再跟着我们了。”他说因为你是女的,我们这个队不管从领队还是到球员都是男的,这样很不方便。
可能在座的各位不太清楚,其实体育界之前历来都有这样的惯例,女记者不能上足球队的大巴车,要不然球队就会觉得触霉头了。
当时国家队领队就跟我说这个,那时候我就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觉得特别委屈在那里痛哭了一场。我完全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因为我根本找不到路,我完全是跟着大巴车到欧洲那个地方,没有地铁,也没有出租车,当时也没有Uber。
徐洁:真的就没有让你上那辆大巴?
易小荷:没有,我都不知道最后怎么回到酒店的。这样的待遇对我来说不是一次两次。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可以诠释为女性在工作中没有受到特别公平的对待。类似这样的事情,它肯定不是一件两件,它可能会化成某种潜意识的东西。
我一直说,一个写作者是有同理心的,她是什么样,她写的作品里就能反映出什么样世界。我并没有刻意,但是我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我写出来的东西、我关注的主题,或者我下笔的角度,肯定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就像同样写女性,托尔斯泰和伍尔芙写女性肯定是不一样的。
“女性写作更多是一种意识”
徐洁:乔叶老师是我们上一届“春风悦读榜”女性奖的得主,她的作品《宝水》去年也获得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请乔叶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个作品也是聚焦乡村女性群体。
乔叶:我在河南豫北乡下的小村庄长大,现在有说“山东、河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性吃饭不上桌”,我从小就目睹这个——女性家庭成员,在重要的场合比如宴席吃饭时是没有坐的位置的。现在据我所知已经基本改观了。
我从小属于性格比较泼辣那种,自从上学知道了“男女不平等”这个词,就经常拿这个干仗。老师老说要男女平等,我就经常觉得这个不平等那个不平等。从小就跟我家长干仗,觉得自己特别受委屈。后来长大了,才觉得在家里受的委屈算什么委屈啊——因为委屈你干仗,就是有一个非常正常的发声渠道了,表现方式其实也挺任性的。当允许你任性的时候,其实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大的不平等。这是我成年之后才认识到的。
后来我开始写作。我是2004年左右开始写小说的,那时与现在写作风潮也不太一样,强调“零度写作”“中性写作”(现在可能也还是强调“雌雄同体的写作是高级写作”),我就一来不希望写得有乡土性,二来不希望我写得很像女性。我要表现出我很酷,我很洋气,写作也致力于清洗女性痕迹。
但后来我想,为什么我要较这个劲呢?我本来就是一个女人,我就是一个女性写作。他们说女性写作有局限,男性写作没有局限吗?我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男性女性写作都有局限,局限不是问题,你怎么突破这个局限、拓宽这个局限才是问题。
我现在就忠实于我的性别身份,就女性写作了,实验一下会怎么样。我有意识地就在这个性别身份上深耕下去。
我觉得男性、女性都是人性。《宝水》里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人在人里,水在水里”。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是因为你在一个人的群体里,水之所以能够成为水,也是因为在水的集体里,它是有一个大的背景在的。
就像“故乡”是相对“异乡”才会有的一个概念一样,谈论女性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更完整的背景。有时候谈女性话题,容易狭窄化、偏执化,以一个极其单薄的角度去谈女性,我觉得这是危险的。
昨天跟小荷还在聊,看《盐镇》的时候,我想到“沉默的男性”部分。《盐镇》的故事如果换男性来叙述会怎么样?我会去想象这部分。
另外,强调“女性作家”,我觉得就像什么会议强调女性比例要30%或者怎么样,还是因为她少,她其实还是相对弱的。我们面对这个现实也没有什么不好。你先面对了它,再在不断壮大和不断生长中,会有很多的改变。
徐洁: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非常尊重女性的男性,但是女性有一些隐秘的需求他们不是不理解,而是没有意识到。有时候女性视角把这个表达出来,他们才会发现原来你们是这么想的、原来会有这样的处境。
乔叶
乔叶:张莉老师前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她说什么是女性写作?不是女人写了就是女性写作。女性写作更多是更深的一种意识。一个女性写作者整天写霸道总裁爱上我,这是女性写作吗?她说,不,这实际上是站在男性的角度,即便作者真的是一个女人,这个写作不是女性写作。而一个男性作家,比如苏童老师,他是一个男人,他写了女人,他不是一个女性写作吗?我觉得可能就是。
所以这里面不是性别区别。性别是最最表层的,一定要看文本,文本更深传达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意识,这是最值得信任的。
“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徐洁:俞冰夏老师是这次春风悦读榜“金翻译家”得主,您在选择翻译作品时,会特别关注一些女性题材吗?
俞冰夏: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与讨论女性主义话题,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女的,今天才坐在这里。因为我翻译的作家都是男的,我自己写的小说可能也跟性别没有关系。
也很少有人叫我女翻译家,因为搞翻译的好像不是一个很有人格的存在,很少有人从性别的角度去讨论翻译这个问题,这是事实。
对“女性是一种处境”这句话,我思考了两整天,还是没有理解。因为每个人活着都是一种处境。
徐洁:它就跟“诗意”一样。
俞冰夏:既然大家都在聊个人经验,我就说一下。我是一个上海人,上海女性意识是很强的,就我自己的家庭,我的外婆、奶奶、母亲,都在家里占据极其强势的地位。我们家里所有事情都是女人决定的、所有话语都是由女性主导的,但是你说我们的家庭很幸福吗?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各有各的不幸。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电影,葡萄牙导演奥利维拉有一个一直合作的女作家叫阿古斯蒂娜·贝莎·路易斯,这个女作家改写了一些男作家写过的作品,想把它改成更加女性化的视角。但这是20世纪中的事情了。
我看过一个电影《亚伯拉罕山谷》,其实是对《包法利夫人》的重写——一个小地方地主的女儿,一辈子靠操控男性得到快感。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是我们今天能接受的一个女性主义的视角吗?这个女作家把女人的歇斯底里、不讲道理,甚至一些在这之上的成分表达出来,女主角的身体有残疾,这其实是把一个完美受害者的形象完全颠倒了。你会很轻易发现这个表面上完美受害者的形象后面,有她自己极其主观能动的东西,这些东西并不一定全是善的,并不一定道德上是高尚的。
俞冰夏
所以今天我来也是学习一下,就是女性主义的视角是不是一个完全积极向上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只能是一个完美的人?女性其实对自身的完美有一种追求,《包法利夫人》中所谓“女人活在想象当中”,这是一种批判。这个女作家自己说“我也是包法利夫人”,她自己也有这种批判。
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很赞同这个东西的人。当然我有女性视角,这是无法否认的。但我也发现自己的女性视角有非常多糟糕的东西在里面。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东西,可能会是更好的一个女性主义谈话的基础。
徐洁:冰夏老师让我想到最近一句流行的话——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事实上女性说这句话,自我要求要比男性多那么一点。但也有一些作家说,这是不是一种自我PUA?自身的强化有点特别地高。
俞冰夏: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包法利夫人非常典型,她一直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实际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想象是可以的,我认为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都有美好的想象,男性肯定也是有的。谁不想成为最好的自己,只是男的不敢说而已。我的意思是说,活在想象中这件事需要更细致的解读。20世纪下半叶,很多文学作品是在解构这件事上作出了巨大努力的。但我们现在似乎回到了所谓前现代主义的一些观念,更希望在道德上得到一个具体的、可靠的、依赖的系统。
“我觉得波伏娃比萨特伟大多了”
徐洁:萧耳老师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她说她是“自觉的女性主义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自觉”是怎么体现在你的创作中的?
萧耳:昨天欧阳江河老师私下聊天的时候,教了我们一句成都方言——“不~存~在”,念起来很好听,要拐好几个弯。欧阳老师说这念出来是很妙的,感觉就像进到哲学里面去了——很多事情好像是可以消解的。
跟冰夏一样,我也是江浙沪独生女,从小根本就不知道男女不平等这件事。很多年以来我被保护得太好了,就是那种上房揭瓦的女孩,经常欺负男孩子。
后来慢慢进入职场、进入社会。我和小荷一样曾经都是媒体人,我最早进的一个部叫社会新闻部,我觉得我是为了性别平衡被派到那个部去的——当时有七个和尚,把我作为第八个,一个女生派进去了。
可能男性对女性有一种刻板要求,或者说刻板印象,他觉得你应该温柔地对待我们,女性要打扫卫生。我对这种要求特别抗拒,我就不干。然后跟这些大哥们关系都搞得很僵,因为太倔了,我就不愿意干这些事。让我去采访、去面对各种事情可以,但别因为我是女孩子,让我干各种琐碎的事,我不接受。
这时候我开始慢慢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女性,我不接受“你是女性你就应该做什么”。这是不存在的。
那存在的是什么?女性身份是有的。就比如今天我们五个女生坐在这里,你们三个是穿裤子的,我跟乔叶是穿裙子的。从裙子到裤子的女性历史就是一部革命史,大家去看整个时尚的发展历程,女性从穿裙子到穿裤子,当时法国作家乔治·桑穿男装、穿裤子,就是一种彰显女性的叛逆。
女性的独立精神,那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我穿着裙子并不代表我弱、不代表我就莺莺燕燕、没有特别刚、很爽利的部分。那完全是性别的刻板印象。
为什么我是一个鲜明的女性主义者?我在大学时就读了波伏娃的《第二性》,若干年以后我将波伏娃的七卷本回忆录每一个字我都认真读了,她应该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位精神导师。我为了波伏娃跟无数(当时是博客时代)男博友开撕,因为他们不喜欢波伏娃,我为了波伏娃跟他们“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我一直强调波伏娃比萨特伟大多了,女性占人类一半的人口,她对人类、对女性进步的推动贡献很大。萨特的存在主义只是一个很小的哲学流派,这么多年来不断有新的流派出来,一直到刚才俞冰夏讲的后现代哲学等很多很多。但波伏娃对女性进入现代性,进入独立,从“第二性”去走向平等的推动是非常巨大的。
我最近这几年写长篇小说,正好有两个都是女性题材的,但都不是刻意的,比如《林中空地》写女性的读书会,因为就像刚才小荷说的,现在主动在学习、谋求进步的,似乎更多就是女性。
萧耳
“女性主义想要发展必须要有男性一起成长”
徐洁:从《宝水》到《盐镇》,写的都是乡村女性她们被看见。其实被看见是幸运的,女性很多困境具体而隐秘,还有很多是没有被看见、没有被书写出来的。
各位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你们已经发现的更为隐秘的那些处境,或者接下来打算将它书写出来的?
乔叶:比如抖音对乡村的渗透与改变,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惊讶的。我在乡村看到尤其是做文旅乡村的好多女性,她们做自媒体,自己拍、自己发,也没有多少粉丝,但拍得兴致勃勃,组成小团队。《宝水》里我也写到小团队拍抖音。因为拍自媒体,她们有了母亲、女儿或媳妇这种身份之外的社会独立身份,甚至能构建一种属于她们个人的公共生活。她们并不意识到这是文化,但乡村的文化属性在她们身上突然有了着落,她们可以不再以谁的老婆、谁的媳妇、谁的妈妈的身份出现。
甚至她们都有孙子孙女了,突然披着丝巾拍照、拍短视频。经常有人嘲笑说“大妈拍抖音”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换一个角度想,这对她们来说是一种灿烂的开始。像这种家庭妇女以前她是不被看见的,现在她们有这个途径被看见了,我个人觉得非常动人。对她们来说,这可能是一种生命力的重新展开。
包括她们做家务,比如做地锅鸡,以前就做给自己家人吃吃,现在展现在镜头面前,向一个广阔的外部世界敞开的时候,她所做的这些之前被淹没的家务,是被看见的,甚至被很多人照亮。然后下面有评论,她们很在意这些评论,用这些重新定义她自己,这些都是非常动人的。所以,我觉得多媒体时代固然有很多问题,但同时它也给了很多机会。
易小荷:我想说的是,女性主义在漫长发展过程中没有取得突破,是因为缺少同盟,女性主义想要发展必须要有男性一起帮忙,大家一起成长。即便我觉得我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写作者,就算我打上这个标签,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跟男性形成一种对立。
我在《盐镇》签售会上遇到过男性读者问我:“为什么你不写一本关于盐镇男性的书?”因为女性就是弱势群体,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如果不将它记录下来,不被人看见的话,男性也许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盐镇》出来以后,最让我诧异的一个反应就是,很多人会过来跟我说,你写的就是我身边的人。
刚才几位老师都讲了,江浙一带是非常富庶的地方,包括萧耳说你小时候跟人打架,其实我也是在城市出生,虽然我们是小城市。最早去到盐镇,我特别特别地诧异,这个地方离我的家乡只有十几公里,但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一个镇上人人都很羡慕,觉得她很能挣钱的女人,她还是当地的媒婆,某种程度上她很受尊敬、很有社会资源的,但人人都知道她被家暴。
我在盐镇采访了100多个人,并非如有些人所想——我是故意选取苦难的样本,并不是,而是大家告诉我说这个镇上大部分女性都遭遇过家暴,不同的只是程度轻重、是很早以前的事情还是现在的事情。这件事让我特别诧异。
另外让我很诧异的就是受教育程度。我们现在已经实行义务教育制了,但盐镇那个地方就是有那么逼仄,有一个形容说“划一根火柴的功夫,那个古镇就可以转一圈”,这就决定了它的镇民见识狭窄。
书中梁小青这个人物,我第一次跟她聊天时完全没有想到她这么漂亮、谈吐非常好、1987年出生的一个女孩,她的父亲就可以因为她爷爷说了一句“家里风水不好,不能出读书人”,就不让她去读书。她完全是自学成才,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和独立的美甲店。到现在为止虽然她的婚姻未尽如人意,但至少她是一个独立的女性。
“一个女性她可以就是她自己”
易小荷:其实我们回想起来,我们从小到大都经历过一种社会上的PUA——对男性,就会要求“你是一个男的,你将来长大了养家糊口,你要娶妻生子,你要赚钱”;而大部分的女性——不代表所有的样本,仅是我周围的我得到的样本——我们得到的规训是:“你是一个女生,你将来要嫁一个好人家,你的老公要是公务员或者要是经商的。”女性很小的时候就被这样的舆论诱导,就会走上一条当时看着轻松,但最后还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独立的一条道路。
近两年《盐镇》受到了一些关注,拿到了一点小小的成绩,我也会参加一些颁奖晚会。就有好朋友跟我说:“你参加颁奖晚会为什么要化妆,为什么要穿晚礼服?”我说这是主办方要求的。但她就说:“你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像一个女作家,你看看人家林徽因、张爱玲,就算人家怎么穿,人家还是像一个女作家。”我就跟她说:“为什么要因为女作家是什么样子,我就变成什么样子?难道不是我是什么样子,女作家就可以是什么样子吗?”
有一个女性主义者先驱,我一下子有点忘记她的名字,好像是叫斯迪姆,她说她40岁的时候有个人上来跟她聊:“你看上去很好,你一点也不像40岁的样子。”她回答说:“没有。这就是40岁的样子。”
我想说的是,一个女性不管是40岁、80岁,她可以很优雅、很漂亮,她也可以不优雅、不漂亮;她可以化妆,也可以不化妆;她可以穿裙子,也可以穿裤子;她可以满脸都是皱纹,也可以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一个女性可以是千姿百态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一个女性,她可以就是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