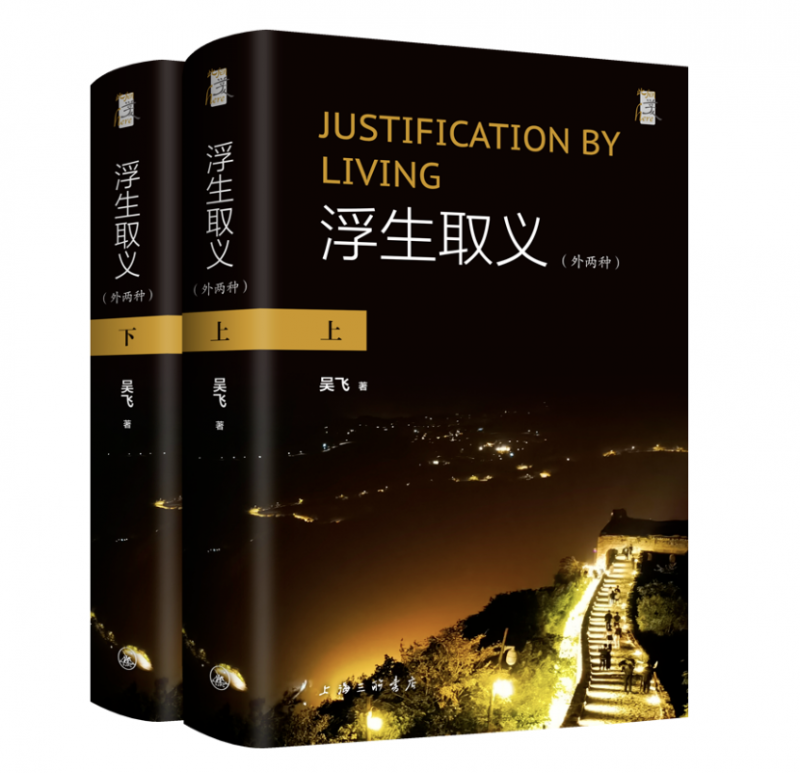《浮生取义(外两种)》(上下两册)
本书是吴飞教授《浮生取义》一书的修订版,并附以他研究自杀的另外两本著作《自杀与美好生活》和《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全面呈现他自杀研究的最主要内容。
内容简介
本书是吴飞教授《浮生取义》一书的修订版,并附以他研究自杀的另外两本著作《自杀与美好生活》和《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全面呈现他自杀研究的最主要内容。
这项自杀研究源于21世纪初费立鹏团队对中国自杀率的重新测算,发现中国自杀率属于世界最高的之一,却与西方国家一般自杀规律颇为不同。吴飞为了深入研究中国自杀问题,首先详细梳理了西方自杀学的哲学基础,形成《自杀与美好生活》一书,然后通过细致深入的田野研究,以“过日子”和“做人”解释中国自杀大多起于家庭纠纷的现象,并进一步思考中国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和正义问题,形成《浮生取义》一书。《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则是对两项研究中主要思想的简要呈现。
这三本书初版已经过去十多年,中国自杀率也早已降了下来,但人们对“过日子”和“做人”的思考并未改变,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也仍然存在,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已。
内容摘录
我的自杀研究(本文为《浮生取义》绪论 )
距离拙著《浮生取义》初版已十年有余,不断有朋友提到,希望能够出个新版。这次承蒙上海三联书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慷慨协作,以及黄韬、徐建新先生的辛勤努力,我三本研究自杀的专著《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自杀与美好生活》《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合刊为一,方便读者参阅对照。十多年过去,这些旧著本来应已随时间速朽,却承蒙诸位朋友不弃,认为还略有参考价值,我是非常感激的。
自杀研究,是我从1999到2009年十年之间从事的主要工作。1999—2005年在美国读书期间,导师凯博文教授希望我以中国自杀问题为博士论文题目,我在认真了解了费立鹏大夫的研究之后,决定接受这个题目。随后,一边准备回国做田野研究,一边广泛阅读关于自杀的理论著作。前者是这项人类学研究必备的材料,后者是理解自杀问题的理论思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无法从现有的自杀学理论中找到一个解释入口,虽然在田野研究中陆续收集了不少自杀案例,对如何下笔仍然一筹莫展。经过了广泛阅读之后,我发现了奥古斯丁,意识到,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一卷中的自杀论述,开启了现代西方自杀学的基本倾向。无论是神学、法学、医学的,还是社会学的自杀论述,都可在奥古斯丁那里找到根源。而奥古斯丁之前希腊、罗马的自杀论述,反而和东方社会如中国、日本、印度对自杀相当正面的态度颇为相似。中国社会中的自杀之所以不能完全被现有自杀学理论所解释,应与这种差异有关。我意识到,要对中国自杀问题有一个恰当的解释,应该首先对现代西方自杀思想的源流有一个深入研究,理解其基本精神,然后再看中国自杀现象为什么无法用它来解释,并在对照中找到中国自杀现象的解释方式。
由于奥古斯丁是西方自杀思想的真正转折点,我决心认真研究奥古斯丁的思想,而那时我也刚刚学习了拉丁语,于是就决定翻译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边练拉丁语,一边深入研究自杀思想转折的深度原因。这是我奥古斯丁研究的起点。在哈佛的几年,除了完成自杀研究的博士论文外,我主要的用力方向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和基督教思想,而所有这些多多少少都与理解西方自杀学相关。我整理思路,其间也杂七杂八写了一些东西。在对西方自杀问题有了一个基本理解之后,我开始思考中国自杀现象的理论解释,特别认真地阅读了余华的《活着》,并完成一篇解读,由此逐渐找到了门径,最后通过“过日子”与“做人”这两个中国式概念,对主要发生于家庭中的中国自杀现象有了一个解释框架。我提交给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The Elegy for Luck,对应的中文题目是《福殇》,围绕命运和幸福问题展开。毕业之后,虽然已经有加州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和我联系,但我并没有马上想出版,而仍然在进一步思考相关问题。就在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2005年,《上帝之城》也译出了一个初稿,对奥古斯丁思想有了初步的理解。
2005年初,我回到北大哲学系做博士后。那年春季的一天,甘阳老师在清华大学做了著名的“通三统”演讲,演讲结束后,和甘阳、汪晖老师以及若干位朋友到五道口的“雕刻时光”小聚。两位老师我虽然此前都有联系,但这回是第一次深度交流。当时,我向他们讲了自杀研究的基本情况,汪晖老师觉得这题目非常重要,他当时任《读书》杂志主编,就邀请我写一系列文章,我后来写了“自杀研究”札记四则,在《读书》上连载。北大博士后的发表要求是四篇核心期刊论文,而此前我还没有任何发表,这连续四篇文章正好满足了要求。但更重要的是,这给我一个机会系统梳理自杀研究的基本想法,为进一步修改打开了思路。随后,甘阳老师准备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组织“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我便以这四篇文章为主体,略作扩充,将我为农家女项目写的报告和此前曾写过的解读《活着》的《死也要活着》编在一起,以《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为题出版。
在完成四篇札记之后,我开始全面整理自己的思考。按照当初思考的顺序,首先还是梳理西方自杀学的历史,于是完成了《自杀与美好生活》一书,写作此书的同时也在修改《上帝之城》的翻译。此书与《上帝之城》上册同时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项工作为我后来的西方思想研究提出了很多重要线索。
然后,我再回过头来整理中国自杀的田野研究,思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决定以正义问题为中心完成这本中文书稿,遂将题目改为《浮生取义》。完成之后,也相应地调整了英文稿,由加州大学出版社换到了鲁特里奇出版社,我的本意,英文题目译为Justification by Living,既与中文题目对应,又借用“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之说而形成中西思想的对照,但英文编辑认为这个题目太晦涩,于是改成一个更直观的题目:Suicide and Justice:a Chinese Perspective。中英文版基本同时出版,但由于题目并非完全对译,曾有不少朋友以为是两本不同的书,这是此处必须澄清的,两个版本基本相同,只是因为英文版字数限制,加上编辑有一些特别的要求,故略有删改。
我一边整理书稿,也一边在思考,这项研究完成之后,该做什么研究?自杀研究已经使我意识到,家庭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关键。其间经历了我姥姥的去世和女儿的出生(相差只有五天,因而未能参加姥姥的丧礼,甚为遗憾),我突然意识到,要理解家庭文化,礼是关键。书稿交上去不久,我就试图去做民间丧礼的田野研究,虽然很快就发现,丧礼与自杀是相当不同的研究领域,似乎很难以相同的方式去研究。
总之,自杀研究对我的重要意义,远较此前曾做的天主教研究要大,因为它不仅开启了我中西平行研究的工作方式,而且为后来的各种思考确立了基本问题意识。我后来所做的各项研究,都是按那时候开启的思路进行的。
虽然远离自杀研究已经很久了,但还有不少朋友会提到十多年前我的一些观点,甚至仍有一些媒体希望我谈自杀问题,但我尽可能婉拒。这并不是因为我对自杀问题不再关心,而是因为我对自杀问题的关注本来就是文化和理论性的,现在已经有三本处理自杀问题的著作,针对此一问题已经没有更多可说的了。此后许多朋友在自杀研究领域继续努力,不仅深度跟踪了这一问题的现实变化,而且还在为解决现实问题献计献策。加拿大医生费立鹏二十年如一日地关注着中国自杀和其他精神医学问题;身在纽约的张杰教授解释自杀问题的扭力理论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展;年轻学者刘燕舞先生对自杀问题的深入研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徐凯文教授对大学生自杀问题的分析与干预都做出了令人尊敬的贡献。对他们的工作,我都抱有深深的敬意。
必须提到的是,中国自杀率很快就降了下来,当然,这既不是因为精神医学的效果,也不是因为任何自杀干预的作用,应该也并非因为农村的农药控制,而是现代中国社会精神文化变迁的结果,恐怕不可给以简单的评判。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我们的国家依然在非常复杂的文化语境下,完成着其现代性的建构。虽然离开了自杀研究,我希望通过对其他问题的研究,推进我对现代性和中国文化的理解,服务于这种建构。
这次非常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善意。借此机会,我再次阅读了三本书的书稿,改正了一些字句和明显错误的地方。我的朋友舒炜多年前就告诫过,对于旧作,不应“给小孩脸上画胡子”,因而,我并没有特别修改书中的主要观点。其中最大的改动,是将阿甘本的homo sacer的译法由“神圣的人”改为“牲人”。我很长时间都拒绝“牲人”的译法,直到今年,读到吾友张旭教授的《什么是homo sacer?》一文。张旭令人信服地指出,如果将homo sacer译为“神圣的人”,那就是完全没有读懂阿甘本。虽然他应该不是针对我说的,但我读之非常汗颜,并且仔细思考了他的论证,承认他是对的,深感学术诤友之可贵,并以终究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而喜悦。
多年以来,很多师友对我做着类似的批评与鞭策,是我得以不断修正错误的真正原因。在此,特别感谢凯博文、曼斯菲尔德两位教授对我在美国学习的支持,感谢甘阳、刘小枫、汪晖、陈来等老师多年来的提携与教诲,感谢李猛、吴增定、张旭、杨立华、唐文明、张志强、冯金红 、赵晓力、渠敬东、周飞舟、强世功、陈壁生等朋友的鼓励与批判,感谢我的学生们与我的深度讨论,也特别感谢我家人的宽容与支持,尤其是内子卢奕,对我这次修订提供了很多建议和帮助,使我愈加体会到人伦生活的沉重与可贵。希望我未来的研究,能够对得起他们所有人的付出。
吴飞
2022年10月20日于仰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