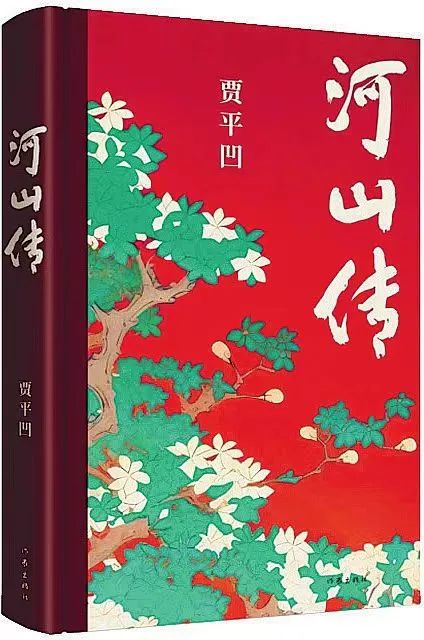贾平凹长篇小说《河山传》:是写实,也是寓言
文|张学昕
《河山传》是具有深广的象征性意蕴和时代隐喻的作品,如此前《废都》《秦腔》《古炉》《山本》,甚或《秦岭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在叙事中选择两位最重要的核心人物“河山”——洗河和罗山作为“传记”的传主,其叙事意图似乎已经很明显:通过两个小人物的命运、人性状写大历史,并采取对生活和现实的民间化、俗世化处理,将世相和人性的真实样貌呈现出来,我想,这或许就是贾平凹叙事的题中要义。也就是说,小说的整体结构和基本框架是以“河山”为共同的“经纬”,展开耐人寻味的叙述。
《河山传》发表于《收获》2023年第5期,单行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无论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秘史,还是个人生命史、命运史,若想找到打开人性的密钥,厘清人物精神和心理的核心层次,对于叙事文本的话语形态选择至关重要。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贾平凹写作发生学意义上灵感生成中的“神性”品质。其实,这里所说的“神性”并不具有无限的“神秘性”,它仍然是依赖作家的个人修炼和创造力而生成,让叙述更加无限地接近存在世界的可能性。对于一位作家而言,通常是他在重构一个文本世界时,必然要超越未经“整理”的现实,即在相同的生活中发现不同。写日常,却又必须越过日常的边界,写“过往”那些曾经描摹过的时空故事,不是“新瓶装老酒”,而是要屡写屡新。每一部小说,都可能是发自作家内心不断的喃喃自语,让文本成为作家创造的另一个新世界。也许这个虚构的世界,未必真的强于作家身处其间的世界,但是,它所呈现的事物一定是独特的意念、意识存在的产物。回顾贾平凹的写作,从最早的长篇小说《商州》开始,直到迄今的《河山传》,20部作品无不充满对人性、宿命、命运的深度探究和悉心描摹。可以说,对于人物生死和命运的描摹和呈示,是贾平凹写作永远的主旨和选择。在贾平凹的作品中,贯穿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意念,即许多人物都会有命运的起伏,变故可能随时发生。这就生发出叙事的传奇性,历史、现实的戏剧性就自然显露出来。仿佛莎士比亚的名句,“每个人都有上场和下场”,人物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被裹挟在时代的漩涡里,或许,这也是贾平凹一直在寻找的文本境界。因此,《河山传》中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悲剧性的元素和各色人物“粉墨登场”的情形,即成为那种“日常传奇”的美学形态,令小说呈现出自然性,更接近生活的原生态。
《河山传》把时间拉回至80年代,再向后延展到2020年,重新发掘这个始终处于变革时期的历史,勘察在绵亘的时间段里的人性状况。这种写法,既是“重构”也是“解构”,其中没有一点虚幻、虚妄的东西。着力让罗山和洗河贯穿整个小说,支撑着文本的结构,贾平凹试图让他们一起联袂穿越俗世、欲望的黑洞。不妨说,这两个人物,几乎成为他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重要“寄托”和叙事推动力。现在的中国作家,面临着对于过往的几十年间的生活究竟该如何再呈现的问题。文学到底应该怎样重新认识并表现这几个历史时期的人性嬗变?无论从道德、伦理层面,还是精神、灵魂和法律层面,这些问题,多年来经常困扰、束缚我们的想象和审美判断,而“超越性视角”则可以让叙述走上一条更符合审美规律的道路,而且还会增加叙事文本的审美张力。贾平凹的几乎全部文本,都在摹写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众生相,他执着书写秦岭五十余年,毫无倦怠之意,依然兢兢业业。这部《河山传》,再次让我们领受到他对生活、对秦岭大地热情而耐心的深耕细作。
现在,我们再回到《河山传》的几个“核心人物”及其关系的描摹。贾平凹的叙事娓娓道来,不急不缓,人物摹写的粗略和故事叙述节奏相生相伴。若从人物形象的层面看,贾平凹以洗河、罗山的个人“成长史”“发迹史”来深描漫长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人性、欲望,以及人与人之间种种新的关系、纠葛。作者无意呈现这两个人物显现出如何的“神性”,而是深入发掘他们的世俗性。或许,从“俗性”这个层面,更能够凸显人性最真实的两难处境,也能够彰显人在现实中的尴尬、荒谬和无奈。进一步说,探讨特定的历史情境里物质、金钱如何经过一代人的中介,彼此相互牵制与“怂恿”,进而展开令人惊诧的悲喜剧和闹剧,更能凸现出时代风云、社会变动不羁中人性的变故。或许惟此,才能在一个没有神性、充满“潜规则”的环境里,让文本暗示出信仰、悲悯和慈爱的惊人匮乏、缺失。另外,贾平凹文本里还蕴含着对现实的讽刺精神,也更为内在地“阐释”出生活和存在世界的“真实性”和反讽性。具体说,洗河的世界是从偶遇罗山开始的。没有罗山的出现,洗河在相当长的日子里,可能还要混迹、流浪在西安的街头干着爆米花的行当,继续顺应其难以想像的命运。在进入罗山的场域之后,洗河逐渐找到自己“混世”的感觉,一步步获得罗山的信任,成为罗山手中重要的棋子之一。因为,洗河与罗山之间,根本不存在商业、生意上的利益关系,洗河之于罗山,只有服从。可以说,洗河之所以能与罗山最后发展成较为特殊的“主仆”关系,并使得这种特殊性能够持续到最后,除了洗河的吃苦耐劳的韧性、厚实性格外,还有洗河身上的机智、忠诚。当然,洗河也十分清楚一个人该如何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洗河成为罗山真正意义上的“助理”之后,“名分”和机会,进一步给了他心理“进阶”的可能性和空间,“见多识广了,人也不再猥琐”。我们关注到,“进城”后的洗河,在许多方面不仅无师自通,而且懂得节制,一下子就呈现出生命的“新状态”。洗河还时时流露出善良的天性,当他已经学会熟练驾驶去外送材料或给公司买东西,司机沙武常常让洗河自己开。而罗山问起来,洗河总是说:“还不行,在学哩。”洗河怕罗山从此辞退了沙武。但是,“两来风茶馆”的女老板呈红与他的一段“交锋”,颇为耐人寻味,又可见出洗河与生俱来的“混世智慧”和过人的聪明。呈红同样来自乡里,却是试图“先入为主”地奚落、嘲弄洗河。洗河则已经生生要变成另一个自己,因此,无论表里,他对呈红的言辞反击都格外犀利。看来,穿越“城与乡”的边界,洗心革面,是进城者竭力想要逾越的底线。罗山与洗河一样,早已十分清楚自己要竭力摆脱乡土的尘埃,需要不断地在商海里凭借一己之力自我挞伐,或对自己所来之路进行检讨。
《河山传》的结构、文本体貌、叙事语言形态、人物形象几个方面,较之贾平凹此前的创作都有很大的变化,表现出“水与火”两种叙事形态的隐秘交融,愈发表现出激情与幽思同在,文人叙事的流风余韵,对“众生”的悲悯情怀,尽显其中,建立起具有极强文化感的审美空间。贾平凹在其文学叙事的整体格局即“世纪写作”中,将叙事维度拉回到1978-2020年,叙事时间跨度40余年,聚焦、演绎诸多人物在起伏跌宕、复杂的当代社会生活现场的状貌书写,视角比此前作品更具独特性。就文本结构和叙事伦理、叙事策略而言,贾平凹对于人物和故事的处理,更是不以两极姿态看待人与事物的变化。我们相信,贾平凹有能力更为出色地讲述现当代中国自己的历史和故事。当他创作的体量、能量、气量增大之后,他文字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更为自然。从《老生》《山本》《暂坐》《酱豆》《青蛙》到《河山传》,贾平凹的写作发生一次次质变,这一点我们不能忽略。归结起来说,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已经不像以往那样清新、叙事讲究,而恰恰是愈益无技巧化。或许,一个作家写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时,文字、叙述形态方面就是简洁、自然而浩瀚。总体说来,虽然《河山传》这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本位仍然是写实主义,但绝不局限于这个层次,尤其不能忽视它意味深长的寓言内涵。
《河山传》仍然是在竭力表现一个民族艰难行进的历程,尤其揭示人性的实际状况。贾平凹格外关注、审视人性的复杂性和变迁史,深度考察人的灵魂如何在不断变革的当代现实中产生“失重”状态。这是我们时代、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最为复杂的、波诡云谲的艰难岁月。应该说,贾平凹40多年的写作生涯,从未离开过时代生活的现场,除了《古炉》《老生》《山本》几部作品之外,从《浮躁》《废都》《秦腔》《带灯》到《极花》《暂坐》的十几部长篇小说,都是直面当代现实生活的。前面的若干部文本的故事讲述时间与“故事发生的时间”基本上是同步的,都是极其“贴着现实的”。那么,贾平凹在当下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重返“九十年代”,并回到“新世纪”之初?贾平凹坦诚他在这部小说的写作中,不断对书稿进行删改,自我否定,还时常烧掉刚刚写就的部分手稿重新写来,这是以往几十年写作少有的。我想,贾平凹叙事的使命感、担当感,即作家“我有使命不敢怠”的写作伦理,让他既激情贯注,又如履薄冰。《河山传》中的罗山之死,那场可能性系数极小的意外,也许就是在毫厘之间,就完成了这个人物由生到死的全过程。在这里,我们愈发地体味到“他只有经历。但他最后的死亡,是他这些经历让他必须死去”这句话所充满的宿命感、沧桑感。贾平凹始终坚持、坚守自己的写法和叙事伦理,其文本精神深度模式和寓意的生成,正是他不断参悟传统,进而融合现代小说叙事精神的有效尝试。
转自《文艺报》2024年1月8日
张学昕,文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囯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文坛》《钟山》等期刊发表文学研究、评论文章300余篇。著有《唯美的叙述》《话语生活中的真相》《穿越叙述的窄门》《苏童论》《阿来论》《中国当代小说八论》等专著15部。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