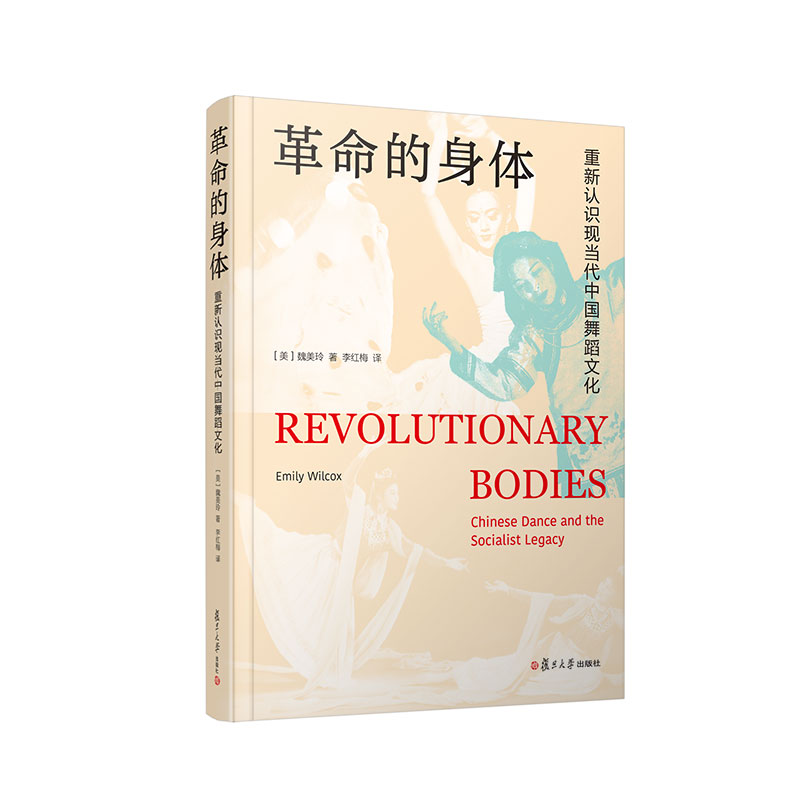在北京舞蹈学院敞亮的舞蹈教室内,我与其他二十位学生静立在一面墙镜前,学生多数是女生。我们身着白色水袖上衣,袖子末端连接着两倍袖长的长绸,宽约两英尺。我们静止不动时,水袖在地板上堆成一团,如一汪珍珠色的池水。我们看着邵未秋老师,听她讲解下一个动作:“袖子收放的重点是任由它自行运动。一旦发力,余下的就都交给袖子去做吧。”说完她转身面向镜子做示范。钢琴老师开始弹奏音乐,邵老师双脚并拢直立,双臂垂放身体两侧。四拍缓慢呼气后,她身体下沉,膝盖弯曲,同时目光下移。接着,又四拍起身,同时右肘逐渐向斜前方抬起,达到顶点后,猛然伸直手臂,手掌向下,手腕轻弹,同时五指张开到最大限度。此时水袖在运动中舒展开来,短暂地悬浮在半空。随着水袖的自然飘落,邵老师也顺着水袖移动的轨迹逐渐放下手臂。现在水袖已在她身前的地板上完全打开,于是她开始了动作练习的第二部分。右脚向后一步,右手手背上扬,小臂转动时快速后撤肘部,使手停在腰间,保持与地面平行。水袖就这样从地面升起,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像被施了魔法一般重回邵老师张开的手掌,整齐地层叠在她拇指与食指之间。一团绸布在手,她转过身来对我们说:“好了,现在你们来试试。”
水袖是数十种不同风格中国舞中的一种,这类当代剧场表演性舞蹈始创于20 世纪中期,至今仍流传于世界各地。在中国境内,“中国舞”通常又被称为“民族舞蹈”。在海外华语社会,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人们也称其为“华族舞蹈”。上述词语中的“舞蹈”与“dance”同义,也可简称为“舞”。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舞蹈学者与舞者一般公认中国舞可细分为两大类:中国古典舞和中国民族民间舞。最初,中国古典舞发源于统称“戏曲”的地方戏剧形式,如京剧和昆曲等。如今,中国古典舞包括早期的戏曲风格舞蹈(也包括水袖)以及近期形成的敦煌风格舞蹈和汉唐风格舞蹈等。中国民族民间舞最初由汉族风格舞蹈(如东北秧歌、山东秧歌、安徽花鼓灯、云南花灯)与少数民族风格舞蹈(如维吾尔族、蒙古族、朝鲜族、藏族、傣族舞蹈等)共同组成。如同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也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推陈出新。中国古典舞和中国民族民间舞有一个重要前提,就像业内人士所称,它们并非受到严格保护或重建的历史形式或民间形式,而是通过研究与创新形成的现代表演形式。
创建中国舞基于研究,而这种研究涉及广泛的表演活动,史料或有记载,社会也有体现。例如,距今约1500年的敦煌壁画是现今甘肃省的世界文化遗产,创立敦煌风格中国古典舞的艺术研究者们常要从那里的人类与天神舞蹈画像中汲取灵感。而创建汉族民间舞的艺术研究者则要从当代节日、庙会的娱乐活动和仪式表演中寻求启发。多数情况下,专业舞者会综合利用各种素材来创新舞蹈风格。以水袖舞为例,舞者既要研究当今戏曲演员的表演,又要研究玉坠、石刻、墓室雕像、绘画、诗歌中出现的水袖舞蹈。邵未秋显然在其水袖舞蹈中运用了当代戏曲表演形式,她的水袖设计、动作技巧、对呼吸及眼神的重视等都来自戏曲表演。邵老师的动作尺度与形态线条也明显借鉴了古代水袖舞蹈,其中有些动作十分接近于那些早期画像上的舞姿。
出于对新创作的重视,中国舞的实践者对自己做过的研究进行诠释,开创了舞蹈新形式。跟大部分古典舞编导一样,邵老师的水袖舞编排去掉了唱、念部分,明显脱离于戏曲形式,因为唱、念是戏曲整体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课堂舞蹈采用了八拍的钢琴音乐韵律,所选系列动作也无关叙事背景,同样摆脱了典型的戏曲音乐和舞台动作。另一个明显变化是邵老师的舞蹈环境有别于古代水袖舞,即她的舞蹈场所通常是学院教室、剧场舞台和电影制片厂,而古代舞蹈场所通常是皇室宫廷或供奉神灵的祭祀场所。在教学实践和已发表的文章中,邵老师都表达了对水袖舞蹈美学最初的理论建构,其基础是她对相近领域的研究,如中国的美学、传统绘画、中医及中国哲学。由于见解独到,她的课堂教学及教学法也被视为一种独特的知识与艺术创造。她在做出这些贡献的过程中,既学习已有艺术形式,又展示个人思想与做法——这就是中国舞的基本创建过程。
一般来说,西方舞蹈观众对中国舞的了解远不如对中国芭蕾和现代舞剧目的了解,尽管如此,中国舞仍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剧场舞蹈形式,且在世界各地都有众多追随者。据2016年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报告,在中国2015年正式演出的全部舞蹈(还包括国际舞蹈团的访华演出)中,过半数都是中国舞。这一结论与我过去十年在中国田野调查结果一致,其间我观察到中国舞在教学课程与表演团体中占有较大比例,拥有的资助和观众人数也超过其他剧场舞蹈表演形式。中国的舞蹈教师与编导每年创作上千部中国舞课堂及舞台剧目新作,地方政府和文化机构每年还会举办中国舞的竞赛和艺术节活动。整个中国有上百个正在运行中的以中国舞为主要内容的学位授予课程,以此为课题的学术研究数量庞大,且还在不断增加。中国舞不仅活跃在本国境内,也活跃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因此,尽管本书重点是讨论现当代中国舞蹈历史变迁与当代发展,但这一话题讨论也是更为普遍的跨国现象。
除剧场表演以外,中国舞还与一系列社会场所与活动相关联。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改编的中国舞已经融入商业表演,在主题公园和热门旅游景点向游客们兜售。业余者表演的中国舞在中小学和企业宴会中流行,此外还成为“广场舞”的核心内容——这一室外社交舞蹈的参与者主要是中年妇女,地点在公园等公共场所。此外,与中国舞相关的还有民间舞蹈艺人及其他仪式从业者所参与的法会道场、婚丧嫁娶、节庆表演等活动。我并未打算涉及所有这些场所,而是将研究重点限定在剧场范围内,关注舞蹈专业院校和舞团中的艺术家活动,他们的舞蹈创作主要是服务剧场。我做出这一选择,旨在将中国舞定位在与世界其他公认剧场舞蹈流派平等对话的位置上,此外还要确信,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舞蹈与文学、电影、戏剧、视觉艺术及音乐等其他领域具有同等重要性。
本书内容按时间顺序,从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前后跨越八十个春秋。这首先是一个历史性项目:通过仔细梳理文献,追踪中国舞在中国20世纪和21世纪早期的产生与发展变化。通过将舞者个人经历、编创剧目、学术争议以及众多机构团体编织在一起,本书将民族志意识融入历史性叙述中。本书把中国舞发展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超越于个人与集体、压迫与反抗、传统与现代或是具象与抽象之间的简单对立之上。在结构上,本书强调过程与成果同样重要,目的是突出舞蹈创作离不开舞台上下的长期辛劳。因此,每一章节都追溯了一个带来重要新发展的研究与创作阶段。第一章讲述了战争期间的舞蹈创作,舞蹈节目最终呈现在1949年首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第二章叙述国家舞蹈课程的设立以及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的成立。第三章描述了中国舞在世界舞台的传播,以及20 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出现的社会主义民族舞剧。第四章考察了中国舞与芭蕾舞之间的关系。第五章揭示了各类早期社会主义舞蹈活动如何为20 世纪70 年代晚期和80 年代早期的中国舞创作打下基础。最后,第六章展示了本书讲述的所有艺术劳动成果,将21 世纪的中国舞艺术活动作为前六十多年趋势的历史延续。
本书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不同观点。例如,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认为,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人占领区仍有各种舞蹈演出活动,充斥着多元演出人群,包括少数民族、外国流民、不讲汉语和非中国背景的人等,他们对早期中国舞的形成与创立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样的叙述可能与现存观点相悖,后者认为早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我认为中国舞在其中占重要地位)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延安实施的由当地汉族人倡议的政策成果。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我指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中国舞在中国国家舞蹈流派中取得主导地位,是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和倡导的广泛舞蹈风格之一。尽管中国舞在1966年后丧失了主导地位,同时迎来了革命芭蕾舞剧十年的盛世,但我认为芭蕾舞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过去数十年来社会主义对艺术试验与多元审美进行投资的回报。这一论点挑战了普遍存在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是铁板一块的,芭蕾舞一直都是中国革命舞蹈传统的主要创作形式。在第五、第六章中,我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舞延续了许多革命战争时期和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传统。尽管中国舞已经随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但本书认为当代意义上中国舞的产生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此外,本书还认为,这一时期的发展持续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舞的舞蹈语汇、编创方法、理论阐释及体制结构。
尽管本书按年代次序组织内容,随时间推移追踪单一舞蹈流派在历史上的出现和变化过程,但作者并不以目的论过程来呈现这一轨迹,或是把中国舞看成一个孤立的流派。无论从艺术定义还是从意识形态定义来看,我并不认为今天的中国舞一定要“好于”早期中国舞,因此,本书不赞同这样一个普遍看法,即改革开放以后的艺术创新要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更多。如同大多数在革命中诞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舞的政治斗争性也在逐渐减弱,这一叙述思考的核心一方面是中国舞在政治含义与用途上的不断变化,另一方面是对此过程中国舞审美形式的种种诠释。尽管当今的中国舞继承了社会主义传统,但并非各方面一视同仁地全盘吸收。从中国舞的非孤立性方面来看,我认为中国舞与其他相近的舞种之间一直都在进行深刻的对话。本书不同程度地考察了中国舞与20 世纪和21 世纪中国现存其他各种舞蹈流派之间的关系,在舞蹈之外,还探讨了中国舞与戏剧、音乐、视觉艺术和电影等其他艺术领域的关系。中国舞与戏曲之间的紧密关系是本书反复出现的主题,不过电影也起到了间接作用,因为现存最好的中国舞记载是以电影形式记录下来的。
尽管中国舞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发生过巨变,但我认为历史上的中国舞流派主要靠三个核心理念在持续创新和反复定义的过程中确立下来,我把这些因素称为“动觉民族主义”“民族与区域包容性”和“动态传承”。这三个理念除了指导专业舞者的艺术工作,还从理论和编创方面将21 世纪的中国舞与早期的舞蹈先辈们联系起来。这些理念不仅将中国舞定义为一种艺术流派,而且还明确了它的社会主义传统性质,最终赋予这一流派在不同时期的革命潜能。因为这些理念都是本书的重要主题,所以有必要在此对这些理念进行简要介绍。
“动觉民族主义”观念认为,中国舞作为流派取决于其审美形式,而非主题内容、演出场所或表演者。根据这一思想,中国舞之所以是“中国的”,是因为其动作形式——如动作语汇、技巧和韵律等——都源自人们对广义中华文化社会的表演行为所进行的持续研究和改编。在中国舞的话语中,这一思想通常用“民族形式”来表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20 世纪30 年代提出了这一词语,一直影响到今日的中国舞理论与实践。当这一思想提出时,“民族形式”主要是指新的、即将创作出来的文艺形式,能够表现当代生活,带来积极的社会变革,既坚持与时俱进又扎根本土文化,因此,动觉民族主义关注的是艺术形式问题,其前提是本土与当代艺术相互促进的思想。
“民族与区域包容性”观念认为,中国舞应该包括全中国各民族及各个地区的不同风格。民族与区域包容性观念刚提出的时候可能有些激进,但它主张中国的民族舞蹈形式不应当仅仅成为主流文化群体的表现形式,如汉族或富裕的沿海城市,相反,它应当包括民族和地理边缘化社会的不同文化,如少数民族群体、乡村以及内陆地区。尽管中国舞语境中还没有一个词语能像“民族形式”一词那样表达这一思想,但是民族与区域包容性是以“中华民族”和“改造”的思想为基础的,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中华民族”的概念从理论上认定中国人身份是多元文化与不同族群的历史集合。“改造”概念描述的是艺术家要转变思想情感,消除偏见,尤其是消除对待穷苦人和农村社会的偏见。
“动态传承”是一个文化转型理论,迫使中国舞艺术家去研究现存表演形式,与此同时,还必须对这些形式提出新颖的阐释。指导思想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文化传统的本质是不断变化,只有持续创新才能保持当代社会中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动态传承的基本涵义是指文化传承与个人创新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在中国舞语境中,描述动态传承的常用语是“继承与发展”,除了抽象限定艺术家的理论目标,还暗指一整套具体的创作方法。因此,动态传承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中国舞从业人员开辟了文化延续的新方向。
在20 世纪早期,数位知名艺术家试验了新的舞蹈编创方法,被后人视为中国舞的先驱。其中一位是裕容龄(1888—1973),她是中法混血儿,父亲是清朝外交官。她曾于1895至1903年在东京和巴黎学习舞蹈,后居住在清朝末期的宫廷里。1904年,裕容龄为慈禧太后创作了三支“中国舞蹈”,并在颐和园为她表演了其中至少一支舞蹈,即《如意舞》,这次演出还包含“西班牙”和“希腊”风格的舞蹈。在试验初期出现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梅兰芳(1894—1961),这位男性京剧明星主要扮演旦角,是中国最著名的艺人之一。1915—1925年,梅兰芳与戏剧理论家、剧作家齐如山(1875—1962)合作,编创了有大段舞蹈表演的系列新剧。这些作品不仅改变了京剧的表演传统,还使舞蹈在中国戏剧中变得举足轻重,成为新兴的民族认同象征。
裕容龄和梅兰芳都是中国舞发展的重要先驱。他们都基于现有素材进行了创新。以裕容龄为例,她的舞蹈灵感来源于她对清朝艺术藏品中的绘画研究以及与宫廷乐师的交流。同样,梅兰芳与其合作人齐如山从中国文学与民俗、佛教绘画以及唐朝的视觉艺术中受到启发,为自己的京剧舞蹈设计服装与动作。此外,裕容龄与梅兰芳像中国舞后期的舞者一样,都强调个性创造,认为自己的作品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期进行的现代主义舞蹈实验别无二致。
尽管裕容龄和梅兰芳开了先河,但他们各自的途径都缺少中国舞核心要素。首先,两人均未能具备中国舞重要特征的明确动作形式理论。尽管人们对裕容龄的编舞理论所知甚少,但她早期中国舞的现存图片与描述并不一定表明关注动作形式就是中国舞的本质特征。梅兰芳的合作人齐如山的确留下了大量理论资料,说明梅兰芳表演带有“中国”特色,其中他强调核心问题是戏剧再现模式(审美性高于现实性),而非动作形式本身。其次,两人均未在作品中明确涉及民族与区域包容性问题。尽管裕容龄的《如意舞》采用了满族发型与服饰,但它反映的是清朝主流宫廷文化的历史背景,而非中国民族或地理方面的多样性。同样,虽然梅兰芳舞蹈中的人物与情节来自中国流行文化故事,但他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却都是与汉族精英文化相关的儒雅人物。裕容龄与梅兰芳二人几乎都只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城市的中心地区演出,这一事实也将他们与后期的中国职业舞者区分开来,这些舞者来自五湖四海,演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我将当代意义上的中国舞产生的时间定于20世纪40年代,理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批舞者和舞蹈编导编创出一批舞蹈剧目并发表相关理论文章,阐明根据“动觉民族主义”“民族与区域包容性”以及“动态传承”三项核心因素构建的中国舞。此举涉及人士众多,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介绍了五位早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本书其他章节中他们也一直是重要角色,他们是戴爱莲(1916—2006)、吴晓邦(1906—1995)、康巴尔汗·艾买提 (1914—1994)、梁伦(1921—2023)、崔承喜(1911—1969),所有这些舞蹈艺术家像他们的先辈裕容龄和梅兰芳一样,都有重要的海外经历,推动着他们为建设中国舞做出巨大贡献。戴爱莲在特立尼达出生和成长,在伦敦开始自己的事业;康巴尔汗在喀什出生,在塔什干和莫斯科开创事业;崔承喜出生在首尔,事业从东京起步;吴晓邦在中国长大,去日本学习了舞蹈;梁伦在中国内地长大并开始舞蹈生涯,后来到香港和东南亚旅行。这些舞蹈家的个人路线在20 世纪40 年代和50 年代汇集在中国,除了崔承喜以外,其他人余生都在中国工作,我认为这五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中国舞创始人。
舞蹈《嘉戎酒会》中的戴爱莲
本书特别关注出生在特立尼达的戴爱莲,因为她是第一位在个人文章和表演中阐述三个中国舞核心因素的舞蹈家。第一章提到,她的这些思想及舞蹈作品诞生于20 世纪40 年代,也就是说,在她移居中国不久之后。她的作品轰动全国是通过1946 年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以下简称大会),那是解放战争时期在重庆举办的首场大型文艺演出。戴爱莲早期中国舞理论的重要记录是一次公开发表的讲话,题为《发展中国舞蹈第一步》,戴爱莲被列为作者并在大会开幕时宣读。当时各大报刊争相转载这份讲稿,它因此成为现存最早的中国舞理论文本之一。在这次讲话中,戴爱莲提出了动觉民族主义、民族与区域包容性以及动态传承三个早期理论构想。关于动觉民族主义方面,她写道:
三年来中国舞蹈艺术社为创作中国舞剧作过一番努力。故事内容是中国的,表演的是中国人,但不能说那是真正的中国舞剧。我们用了外国的技巧和步法来传达故事,好像用外国话讲中国的故事,这是观众显然明白的。可以说过去三年的工作是建立舞蹈成为一种独立艺术的第一步,不过就创造“中国舞”而论,那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因为缺乏舞蹈文化和习惯的知识,而采取了那个步骤……
戴爱莲继续解释了她认为的创建中国舞的正确方法,概括了民族与区域包容性以及动态传承的原则。首先,她描述了有许多人在对现存舞蹈进行研究,包括全国各地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传统舞蹈。接着,她讲述了人们如何利用现有资源进行舞蹈形式创新。戴爱莲的讲话是大会开场白,而大会本身也从结构与实施方面模拟了这一未来规划。演出节目中完全没有戴爱莲早期以芭蕾舞或现代舞为主要动作形式的编创作品,相反,大会包含的舞蹈作品都来自地方的表演活动,由不同民族与地区背景的艺术家们创作而成,代表了中国六个民族和诸多地区。根据戴爱莲的观点,舞蹈虽根植于地方表演形式,但可以展现新的艺术风貌与思想,按戴爱莲的描述,这一规划的目标是要“为舞台建立新的中国现代舞”。
舞蹈《长鼓舞》中的崔承喜
早期研究队伍中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崔承喜,这位朝鲜族女士是第一位在四大洲巡演的东亚舞蹈家,20 世纪30 年代誉满全球。第二章提到,崔承喜领导了基于戏曲的中国古典舞早期建设工作,她与康巴尔汗等人是开创了影响广泛的中国舞训练方法的先声。1945年,上海的一位新闻记者记录了崔承喜的一段陈述,同样也预示了中国舞的核心要素,特别是动态传承方面。据报道,崔承喜与梅兰芳有过一次对话,当梅兰芳请崔承喜阐述传统在她自己舞蹈创作中的作用时,崔承喜回应说,“完全依照从前人所传的舞踊我是不取的。有人说新的创造即是破坏传统,我却以为新的创造乃古之传统的正当发展。过去我们祖先的艺术创造,遗留下来成为今日之艺术传统,今日艺术家们之新的创造,也可成为后世子孙之传统”。
此处,崔承喜表达了一个新颖开放且自我指涉的舞蹈创作理念、舞蹈与传统的关系,以及舞蹈文化生产与再造中的个人作用。这一深思熟虑的知识体系激励着她本人与其他人共同努力去创造中国舞,他们不断编创新剧目,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不停演出,鼓励新一代舞者成为艺术家、理论家、教师、管理者和文化偶像。在本书中,我仔细研究了许多革命性身体,他们出现在这些舞蹈家演出项目中,并形成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舞蹈表达形式。在此过程中,我尽量公正地对待他们舞蹈编创的复杂性以及他们的远见卓识,说明他们如何凭借个人的胆识与想象力丰富了中国当代舞蹈史。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