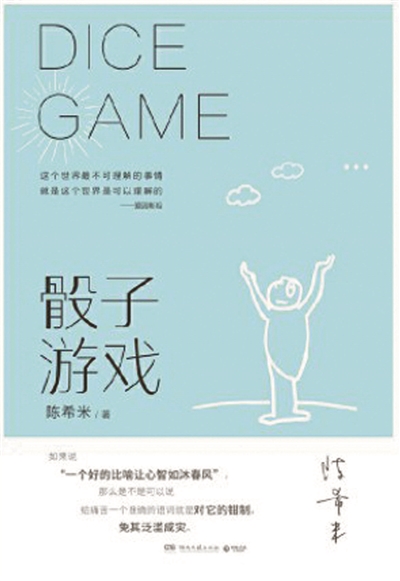一篇书评,但凡题目在脑子里忽然出现,后边要写的意思,也就大概齐有了。可书评之题常常不是“想定”(至少对我是如此),而是全书读过后刚放下或过了好一阵,就会像灵感降临那样突然闪现在眼前。可我又不认为这是灵感一现,而是此书内容经过阅读再沉淀之后对我的最深触动。
仅属于她自己的精神秉持
当然,我说这傲慢、偏见都是要加引号的。因为据我个人对作者之有限了解,她本人在生活中,从来不会显露出任何对待他人的傲慢和偏见——她甚至是退让加谦逊的老好人。
我这里要说的“傲慢与偏见”,恰恰是作者在其写作过程中,完全针对于她自己的。
倒也是。一个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并崇尚精神自由的人,必然对自己是傲慢的——再说白了——一辈子要是对自己的人生态度没有点内在傲慢;从来只会对外板着脸扮演有个性,而内瓤里无论是想还是做,都总在随波逐流暗恋时髦,那就不必再奢谈独立和个性了。再者,写作之深层其实完全就是代表作者对存在、对生死、对社会思考最后浮出海面的表达。而思考加表达如果在假扮个性后又是人云亦云、玩弄些最新潮流(其实是流行)的辞藻还要到处张扬聒噪,内在却丝毫没有一点个性偏见,那又还写个什么劲?
幸好,我在阅读《骰子游戏》过程中,“傲慢”“偏见”这两点都感觉到了。但陈希米当然不会像徐悲鸿那样直接喊出来“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她不是那样个性而只会在沉郁中默写着仅属于她自己的精神秉持。这也才让《骰子游戏》一书很有些与众不同。
随便打个比方:有一句老套哲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微笑”——本来也挺有意思的说法。但是被太多写家反复滥用之后,反倒成了一个最大俗套。而写作真正要紧的内心逻辑恰恰应该是反过来的——你必须以自己独持之“偏见”,坐实了(哪怕是误导读者)“上帝一思考,人类就微笑”这样的逆反;否则千篇一律只在俗套中跳进跳出,我还读你这书个什么劲?
且说陈希米之前一本书的名字:《让“死”活下去》就是这个意思。按古诗之训“死时元知万事空”,按世上寻常之想,死即是一切都绝断了后路,还咋可能再“活”下去?而让“死”活下去——偏偏质问、挑战的,甚至对之发出咆哮的,就是早被人们已经认成死理的通常逻辑。
“翻译”出另一层新意
对《骰子游戏》的真正阅读是在这本书出版很久之后,其中我最喜欢的篇目分别是:《练习死亡》、《迎接》、《荡漾的笑意》。
《练习死亡》一开篇,作者首先避开小说内容不谈,而是以中文意译起海明威名篇之题——
“乞力马扎罗的雪,第一次读过之后,与其说是记住了这个小说标题的发音,不如说这几个汉字总是随即清晰在眼前……乞,是标志性地与众不同的,除了乞丐,大约极少其他篇名会以这个字打头,深刻的记忆肯定由这个字起头。乞力,不妨解作乞丐之力,似竭尽全力,但又无能为力,似虽乞犹荣,又其实是绝望一跃。马扎罗,可以连起来,三个音节几乎必然连续发出,一个地名或者一个男人的名字——可乞力马扎罗才是。马,一种向前的姿势,大多数的时候是奔腾,也有时是稳稳地、默默地,以优雅的碎步。扎,联想到深挖、深深的根以至于深刻,还有力。罗,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消瘦的男人的感觉,于是这里有男人。雪,是冷,是美。某处之雪——必然是不同寻常之处或发生不同寻常之事之处。乞力马扎罗——的雪,一个有男人之力的地方的冷与美。”
在海明威所有长、短、中篇创作里,我个人最喜欢的只有两篇:《乞力马扎罗的雪》和《白象似的群山》。都是写男女之情——小说极其简短但内涵却可以令读者无限延展——两性之爱、之性、之情感、之敌意的不确实性,被海明威如号脉般凭空拿捏、切中曲衷。
可陈希米恰恰反过来:她完全甩开原小说被写得那样暧昧、含混、迷离;而是以奔腾激荡之中文之笔,对小说鞭辟入里、“翻译”出另一层令读者完全想不到的新意。初读第一遍,我嘴里不自觉随之念诵,竟感觉这不是小说评论或哲学随笔,而是我“被”进入了一番挥洒的诗意之“序”——就如贝多芬的《艾爱格蒙》,在悲壮辽阔中张扬起雄浑的戏性张力。
作者如此之“译”才让我一时幡然醒悟:原来在无数对该小说评论的男女之爱之外,还可以作出更深刻的底蕴翻新及别开洞天的解读和阐释。
成为树,就是成为意义
再说《骰子游戏》中的《迎接》——作者是这样以诗歌“树”而走进爱情的(受限于篇幅我只得断诗取意了)——
“一棵树,我总是从他的叶子,他的树干,枝条的粗细和力度,叶子的形状和颜色,四季的姿势,开花或者凋谢的节奏和时辰,来想象他的意味,他的象征,来认出他,认识他,爱他。走过一轮四季,看雨转晴过,听风鸣雷闪,看够他的绰约和悲惨……
“那些干净蓬勃的树,那些高傲孤独的树,那些温柔逶迤的树,斑驳苍劲的树,……重生的树,新的生命缓慢地挺进着,……干净的空气和蓝色的天,让树这样细致地丰富着。
“我在世界各地寻找树的姿势,每一种美的样子我都刻了下来,只要那种美震撼了我,只要我舍不得离去,我就知道,他来了,……树,是他选择的轮回。”
我说不清也道不明,作者这是对树的充沛感发,还是将对人的亲与爱寓意深长于树的挺拔?再反复阅读其中,由是而想:凡哲学、哲思,都非要用推理、论证盘盘绕绕才能说明白吗?我看倒也未必——比如对《乞力马扎罗的雪》篇目的激情翻译,比如以充沛文学冲破哲学藩篱对树与人或人与树的酣畅抒怀,恰恰反而让我从中汲取到了更多的生命哲学之想。难怪歌德会感叹:“理论总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常绿。”
任何人都见过在骤雨狂风中,树木被摧拉撕扯到天旋地转呼啸尖叫就如哭号;但作者却是这样感悟着风与树的亲情:“树,……永远只跟风交流。那交流真是风情万种,变幻万千。风愈猛,树则愈勇,风妩媚,树婀娜,风的疲惫是树的沧桑,风的自豪是树的挺拔,风的哭泣是树的凋零,风的自由是树的孤寂,风的复返,是树的年轮,风的见识,是树的智慧,风是树的加持,树是风的定力……帕慕克的树说:‘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我说,成为树,就是成为意义。他(史铁生)也说他要选树的”。
看到了你眼睛里的笑意
最后的点评且留给此书的结尾之篇:《荡漾的笑意》。这篇和《彦和周围》一样,都是此书中被我一读再读的篇目。关键是文字被写活了——所以被写的人和事,就更加的栩栩如生、跃然眼中。
此文要说的事情经过很简单——
“赵莉是个雕塑家,为一个名叫史铁生的朋友做了塑像,开始于他死之前五年。赵莉,她并不知道他将会在五年之后死去。她做了一个初稿,一个未经烧铸的泥塑模型,通过电邮传过来给他看,她用的是粗犷的手法。他一看就认出了自己,就喜欢了。他从没有这样看见过自己,觉得真新鲜。
“但是这个雕像被搁置了,在铸铁厂浇铸好之后赵莉居然不自信了,在厂里放了三年。直到五年后他的死讯传来。赵莉终于从工厂取回了这座雕像,她‘静静地坐在被初春的阳光斜照的四年前完成的雕像前,无数次长久地对望‘他’,再一次清理它的每一个细节……”
我对雕塑艺术一窍不通,从来只限于观看。但我读过的两本与雕塑有关传记,它们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奥地利作家诗人里尔克写的:《罗丹论》;意大利乔尔乔·瓦萨里所著:《倔强的石头——米开朗琪罗传》。《荡漾的笑意》是我读到的第三篇关于雕塑的述评。必须客观地说:此篇和我读的如前两本传记一样出色。
陈希米这样写:“赵莉做的塑像,没有刻出眼睛,只刻出了眼镜,不透明的镜片。
“可是那么多亲近的朋友看了雕塑都说:神似!为什么?看不到眼睛,却神似?
“我们看到了你眼睛里的笑意。”
陈希米特别说到“被赵莉的这个雕塑作品感动的人,几乎只能是曾经亲眼见过他的人,认识他的人,熟悉他的人,听说过他的故事或者了解他的作品的人”。对这一点,我很为自己感到幸运:作为长久相识史铁生的人,“我们”之后将是死一个少一个。就像苏联卫国战争的战士那样人以罕为贵。
我见过赵莉为所铸造的那个“史铁生”——如果用“很像”“真像”去形容赵莉对这个雕塑的完成,就太委屈了她的如此“神之一手”。她确实没有雕出史铁生的眼睛——只有厚框的眼镜。我恰恰曾在一个大雪的白天,去拜访史铁生时,见过如下情景:被天上阳光和地上白雪强光反照,让渐步走近的我,完全看不见他的眼睛——只能看到他一脸温和敦厚的笑意。因此说赵莉雕塑的史铁生“神似”也还不够精准——是魂似才对。
陈希米所以定论:“赵莉的这个塑像,确实是‘他’。如果说在他死之前这个塑像没有最终完成,那么,在他死之后,就真正完成了,就好像‘他’的复活。”被赵莉所“复活”的史铁生——为我们和他的灵魂又建立起了一种新的联系方式——让我们可以无穷地琢磨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一切都是全新的发展。
“感谢赵莉——我竟听见被雕塑者这样说了!”
陈希米听见了史铁生对赵莉的亲自感谢!——也让我在诗意的凝想中结束了对《骰子游戏》的又一次重读。
文/何东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