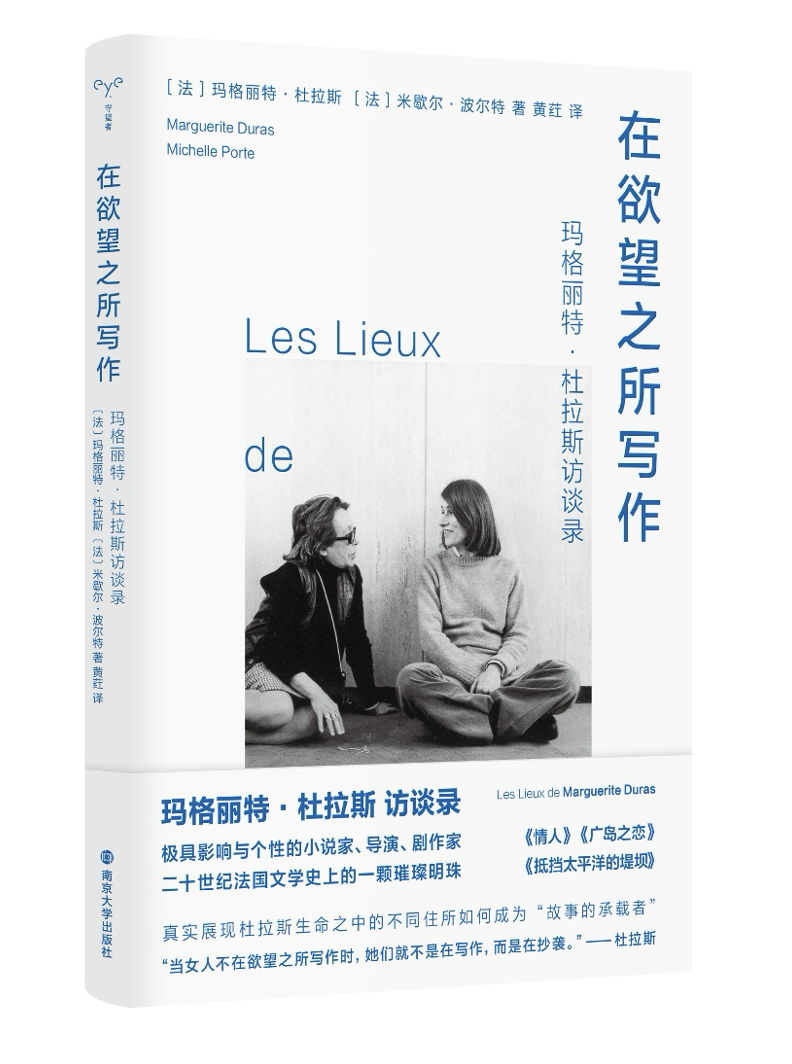玛格丽特·杜拉斯:
聊诺弗勒堡的这栋房子、聊花园,我可以聊上几个小时。我知道一切,知道以前的门在哪里,一切,池塘边的围墙,所有花草,所有花草在哪里,甚至那些野草我都知道它们在哪里,一切。
米歇尔·波尔特:
玛格丽特·杜拉斯,您写过:“我拍电影是为了打发时间。如果我内心强大到可以什么事都不做,我会什么事都不做。正是因为我没有强大到让自己无所事事,我才去拍电影。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关于我所做的事,这是我能说的最实实在在的话了。”
杜拉斯:
的确。
波尔特:
您是不是也会用同样的方式说:正是因为我没有强大到让自己无所事事,我才写书?
杜拉斯:
当我写书的时候,我不会有这种想法,不会。通常都是我停止写书的时候,我才会有这种想法。我想说的是,当我停止每天写作时,我才去拍电影。只有当我停止写作,我才停止,是的,我才停止某种……呃……说到底,发生在我身上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写作。但我最初写作的理由,我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了。或许和下面的理由一样。让我惊讶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写作。我对那些不写作的人暗自钦佩,当然,对那些不拍电影的人也一样。
波尔特:
您的很多电影都发生在一栋和外界隔绝的房子里面。
杜拉斯:
在这里,是的,在这栋房子里。每次我在这里,每次我都有拍摄的欲望。会有一些地方给你想拍电影的欲望。我从来没想到一个地方会有这种强大的力量。我书中所有女人都住在这栋房子里,所有。只有女人才会在一个地方住下来,而男人不会。这栋房子就曾住过劳儿·瓦·斯泰因、安娜玛丽·斯特雷特、伊莎贝尔·格朗热、娜塔丽·格朗热,同样也有各种各样的女人;有时候,当我走进这栋房子,我感觉……有很多女人都在这里,就是这样。我也曾住在这里,完完全全。我想这是世界上我住得最多的地方。当我说到其他女人,我想这些女人身上也有我的影子;仿佛她们和我是彼此相通的。她们在屋子里待的时间,就是话语到来前的时间,男人到来前的时间。男人,如果他无法给事物命名,他就会感到苦恼,感到不幸,感到无所适从。男人不说话会难受,而女人不会。我在这里见到的所有女人一开始都沉默不语;之后,我不知道她们会怎样,但开始她们都一言不发,久久沉默。她们仿佛嵌在房间里,融入墙壁、房间的所有物品里。当我在这个房间里,我有一种感觉,不要改变房间固有的秩序,仿佛房间自身,或者说住所并没有觉察到我在那里,一个女人在那里:她在那里已经有她的位置。或许我谈论的是这些地方的静默。
米什莱说女巫们就是这么来的。在中世纪,男人们要么去为领主打仗,要么参加十字军东征,住在乡间的女人则留在家里,孤独,隔绝,长年累月住在森林里,在她们的棚屋里,就这样,因为孤寂,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无法想象的孤寂,她们开始和树木、植物、野兽说话,也就是说开始进入,怎么说呢?开始和大自然一起创造一种智慧,重新塑造这种智慧。如果您愿意的话,一种应该上溯到史前的智慧,重新和它建立联系。人们把她们叫作女巫,烧死她们。据说有过一百万名女巫。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初期。烧死女人的陋习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
波尔特:
人们在您的电影中、您的书中看到的那些女人,我想到《娜塔丽·格朗热》中的女人,也就是伊莎贝尔·格朗热,想到伊丽莎白·阿利奥纳,想到《大西洋海滩》电影《巴克斯泰尔,维拉·巴克斯泰尔》最初的片名。里的维拉·巴克斯泰尔,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还不是米什莱所谓的女巫?
杜拉斯:
我们还处在那种境地,我们这些女人……我们还处在那种境地……是的。我们处在那种境地。并没有真正改变。我,我在这栋房子里,和这个花园一起,而相比之下,男人们永远都没有一个住处、一个居所。
波尔特:
关于电影《娜塔丽·格朗热》,您曾说过:在《娜塔丽·格朗热》中,我首先看到的不是电影,而是房子。
杜拉斯:
是的。或许因为一直在房子里,它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容器。好吧。我这里要表达的是一个意象,而不是一种想法。人们可以把房子看成一个庇护所,来这里寻找一份安全感。我呢,我认为除了这个,它也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的,除了常说的安全、稳定、家庭、温馨等之外,还会发生别的事情;房子也铭刻着家庭的可怕,逃离的欲望,种种想自杀的情绪。一切都在其中。奇怪的是,通常,您知道,人们都会回家等死。他们更喜欢在家中死去。人们一感到消沉抑郁就要回家。家真是个神秘的地方,但……我不知道现在城里的人们还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呢,我对家的认识就是和房子联系在一起的。我以前还是有过一幢房子的,在多尔多涅省,那时我六岁,但房子被我母亲卖了……要跟您说明的是,我是公务员的女儿,在我整个童年时期,我们不停地换住处。我父母每换一次工作,我们就得搬一次家。后来我在巴黎租公寓住。在这里,我第一次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而且……这有点儿像我就是在这里出生似的,就在这里,我把它打造成我的房子,以至于我感觉在……在我到来之前,在我出生之前它就属于我了。
波尔特:
您认为只有女人才能如此“完全地”居住在一个地方吗?
杜拉斯:
是的。只有女人才会在这里感到自在,完全融入其中,是的,不会在这里感到无聊。我想我穿过这座房子时不可能不去凝视它。我相信这样的凝视是一种女性凝视。男人晚上回到房子里,在这儿吃饭,在这儿睡觉,在这儿取暖,诸如此类。女人,则是另一回事,有一种狂喜的凝视,那是女人凝视房子,凝视她的居所,凝视屋里的东西,这些东西承载着她的生活,她存在的理由,实际上,对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这样,这是男人无法体会的。我曾经说过,当伊莎贝尔·格朗热穿过花园时,就是这个花园,她穿过花园这件事不会让您觉得奇怪。伊莎贝尔·格朗热在花园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比如一个房间,她不在别的地方,她在这里。她非常缓慢地在花园里行走,这看起来非常自然。如果是一个男人这样做,如果一个男人以这样的步伐行走,如此平静,如此安详,人们不会信的。人们会说:他在沉思,因为眼下他遇到了麻烦。人们会说:他在花园里踱步。人们不会说他在花园里散步。人们会说他去那儿想事情。过去,房子里的女人或许会担心看到男人这样,在公园里,像人们说的,为自己的思绪所困扰。在《娜塔丽·格朗热》里,这座房子,它是真正的女人住所,它是女人的房子。而且,一直如此,因为房子是女人造就的。和无产者一样:无产者的劳动属于自己,属于无产者。无产者的劳动工具就“是”无产者。同样,房子也属于女人,女人是无产者,大家都知道,千百年来都是这样。房子属于女人,就好像劳动工具属于无产者那样。
因为女人自身是一个居所,孩子的居所,她有保护欲,有那种用身体保护他们的意识,用她自己的身体,这一事实与她自身融入住处、融入居所的方式不无关系。这是肯定的。
我认为,有孩子和没孩子的女人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生产,我将其视为一种犯罪。如同丢掉孩子,抛弃孩子。我见过最接近谋杀的事就是分娩。沉睡的孩子出世,这是沉睡的生命,完全沉睡在不可思议的极乐之中,然后他被弄醒了。也许生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的体验。我们对此所知甚少。众说纷纭,其中有诸多偏见。的确,这就是谋杀。孩子就像一个幸运儿。生命的第一个迹象就是痛苦的叫喊。要知道,当空气进入孩子的肺泡时,会唤起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而生命最初的表现,就是痛苦。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