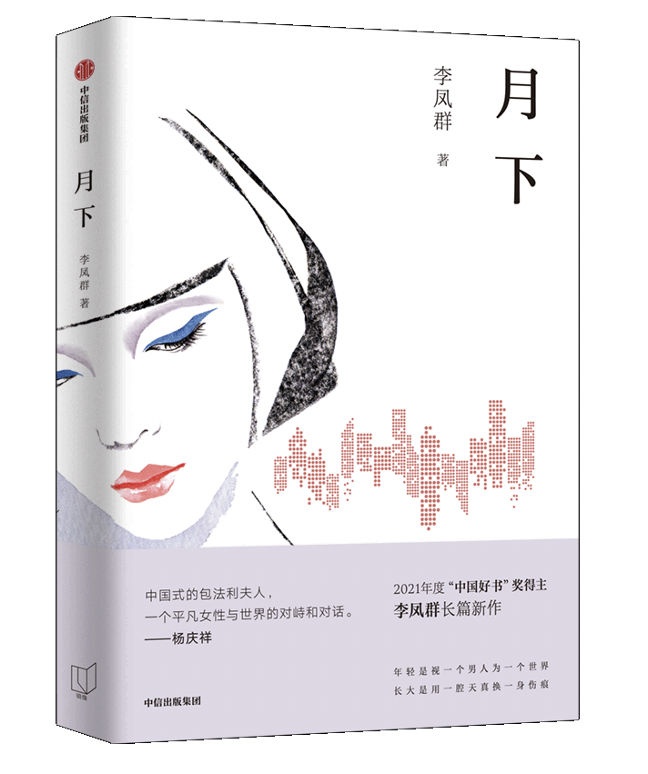11月4日,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书式生活,在常州经开区图书馆,举办了李凤群2023年长篇小说《月份》分享。活动中李凤群讲述了《月下》与常州这个城市之间的关联,三位女性作家共同回忆她们之间相互被看见和被听见的友谊,以及《月下》在女性成长之外,通过书中两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的描写,所折射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社会变化在普通人物中的深层体现。
《月下》李凤群 著;镜像×大方 2023年1月
作家相识——人海中意想不到的相遇是故事的开始
周洁茹(作家、浙江传媒学院驻校作家):
大家好,我在经开区度过了难忘的4年,想起来了以前是戚区。跟凤群我们共同的很珍贵的青春时代。我们是在常州认识的,在常州见到的第一面。那么请我们《月下》的作者凤群来讲讲与常州的联系是怎么样的。
李凤群(作家,“中国好书”得主):我来之前已经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我是1992年从安徽到常州来,然后2003年离开常州,然后我在全世界各地走了许多的地方,但是在2020年我写了这样一本书叫《月下》,《月下》里面有很多常州的影子,因为常州是我人生重要转折的地方。
我认识洁茹老师是在她非常年轻的时候,大概也就是14、15岁这个样子,非常年轻。那时候常州就已经开始着重培养作家了,她们杂志社做了一个作家培训班,像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都可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然后相处了一个夏天,那时候我们没讲上几句话,总共都没听她讲过10句话。到了1996年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常州新华书店碰到了。我们在新华书店的一个角落里相遇了,然后我认出了她,她也认出了我。但是所谓的认出我,我怀疑她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名字。然后就到了2000年,洁茹那时已经去了美国好像,我就在常州文化宫的小地下室看到了她的书《小妖的网》,然后我就指着这个书说我认识这个人,我说我也要成为一个作家,之后我就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大概到了2020年,突然有一天,香港文学的主编来跟我约稿,加我的微信,我很吃惊,她不认得我也不记得我。所以我这次来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故事,我和瑶琴也是第一次见面,所以我特别激动。
周洁茹:当时做《香港文学》的主编我是通过瑶琴教授找到你的,兜兜转转。所以今天很激动,我们三个人都很激动。
戴瑶琴(评论家、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我记得。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讲了三段故事了,一个是凤群和常州的故事,一个是凤群和洁茹的故事,下面我给大家讲我和凤群的故事。这告诉我们,在人海当中有很多种意想不到的相遇。
我和凤群是网上认识的,按照大家讲的话,我们还是网友。当时凤群写了一个长篇小说叫《大风》,当时我要承担《文艺报》年度海外华文的综述。我读到了这个作品,我的学生从新浪微博找到了凤群老师,当时她在美国,我们是这么认识起来的。我读了她的《大风》之后,紧接着我看了她的《大野》。凤群老师和我约过《大野》的书评,后来我又看了她的三卷本《大江》,然后到她的《大望》,再到今天的《月下》,这个是我们相遇的故事。凤群可以先聊一下《月下》。
《月下》的创作——被看到和被听到是前进的动力
李凤群:关于《月下》的创作有两个原因。我在写《月下》之前我是写“大小说”的,所谓的大小说就是写家族,写历史命运,比如《大江》《大风》《大野》《大望》,所以认识我的人就一致认为我不会写女性喜欢写的小说,这个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电视上经常就播放一些大女主的电视,逆袭、成功之类的,我不反对这样的东西,只是不那么有兴趣,我想表达一下真实的人生。比方说一个人一辈子经过哪些地方,见证过哪些事情,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在常州清凉路附近生活过,原来在常州服装厂工作,大约是清凉路的25号,然后我又因为写作被送到常州教育学院去读大专,那是清凉路的50号,我毕业以后应聘的一个工作做在三株集团,也在清凉寺巷子附近。短短的几十米的路程,实际上这条路是很多人一辈子也无法逾越的,那条巷子我反反复复走了好多年,我就非常想把这个巷子里的姑娘的命运写出来。我在那里面认识了好几个姑娘,开理发店的、本身家就住在巷子附近的,以及租房打工的,这个是《月下》的缘起。当然,《月下》里的月城是不是常州,或者说在书中我有没有表达出我对于常州的感情,就有待读者发现和理解。
戴瑶琴:我应该算是《月下》的第一批读者,当《月下》的雏形出来的时候,我已经看了这个作品。每个朋友读这个小说的时候,肯定会被小说的第一句话所打动,就是“余文真多么渴望被看见”。《月下》讲了一个被淹没在人群中的一个普通女孩,她发出的声音。
如果我们单纯来看《月下》的话,它其实写到了一个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她多么渴望被看到,一个是她多么渴望被听到。我想请各位朋友比较一下,到底是看到容易还是听到容易。按照这个小说的描述,我们会发现一个女孩在人群中被看到是相对容易的,更难做到的是她被听到,她的声音要被大众所发现,她的意见要被大众所吸纳,这个难度是特别大的。我不做过多的剧透,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女孩她怎么在她的成长过程当中经历了被看到被听到的过程,我觉得这是小说写得非常动人的一点。
刚开始的时候余文真用了很多种方法想让人家看到她,我们会想是谁中断了她的念头,我们会想是不是社会各种压力让她被看到的念头总是被打压。不是,恰恰是来自她的母亲,她的母亲跟她讲,像你这样的女人你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是余文真的母亲告诉她不要有那么多的想法,不要被看到,就这么过一辈子。余文真她最大的心理伤害和最大的一次打击其实来自于她母亲对她的否定,紧接着她做了一系列的努力想被看到。而小说当中的男主人公章东南也帮她实现了一个愿望,就是通过他的训练和辅导,让余文真能够被看见。但是我们看小说的时候会发现有一点很特殊,就是每一次余文真和章东南相处的时候都得偷偷摸摸的。这就给我们一个结论,余文真她确实被看到了,但是她是一个隐身的人,她是沉默的,她没有被听到,她非常想站在章东南的身边,能和他变成一个群体的人,她能够发出一样的声音,但她发现这个时候章东南不让她这么做。
于是我们看到两点,第一个她想被看到的时候,是她的母亲不让她被看到;当她想被听到的时候,是她的爱人不让她被听到。于是在这个小说当中,她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也是读者朋友在读的时候会觉得很难想象的一点,为什么余文真会尖叫?在小说当中有很长一段一直描写她在尖叫,她在给章东南打电话的时候她会尖叫。这个尖叫是她情感的一种宣泄,是她的一种表达。她没有地方表达,所以在电话中,她把这样的诉求给表达出来。
整个的小说她就一直在努力从“被看到”到“被听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经过反抗之后,她反而获得了一种释然。她觉得我不需要强求自己被看到或者是被听到的,这是一种女性的觉醒和成长,我已经不需要依赖外界对我的认可,对我的接纳,我首先得有一个自己的理解和接纳。于是这个时候她可以坦然得在人群当中,她不需要再刻意的表达什么。余文真获得的这样的心声,这种感受是来自于她经过了一个被看到和一个被听到的一个过程的探索。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女性,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她们也正在经历着,或者想经历着自己“被看到”和“被听到”的过程,“被听到”更加艰难。《月下》其实写出了这样的一段探索的心灵之路,这也是这个小说在写女性的成长过程当中,她用的这样的路径给予大家阅读的力量。我想听凤群谈一谈,这她是怎么来处理被听到和被看到之间的关系。
李凤群:我听入神了,我确实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解读。也有很多的评论家在谈这个小说,但我是第一次从这个视角来看到“被听到”是如此重要,振聋发聩。
因为我在很多小巷子里面生活过,小巷子里面很多母亲和女儿之间有一种像猫捉老鼠的游戏,孩子要做什么,妈妈肯定是要把她拉回来,拉到她认为的正确的道路上来。比方说我最近听到的一个段子,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个段子就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不能打,一打就打出心理问题,紧跟着就有一句很精妙的回答说,“如果过去的孩子打了没出问题,她为什么现在要打她的孩子呢”。实际上每一个母亲给孩子的带来的影响,会一代一代传下来。在所谓的正确和所谓的规范里面,这个女孩子被固定住了。
余文真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身处的巷子非常的狭窄,狭窄到左邻可以看到右舍的餐桌上的菜的多少,晚上在床上能够听到邻居家吵架、洗碗的声音,什么都能听得到。在这样环境里面生出来的孩子,她有一种特殊性。母亲对孩子的要求训练了余文真不被看见的习惯,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性格,那么到成年以后她的渴望就开始生发出来,当然她的爱情导致她最后不被听到,她之所以不被听到,是因为她身上的烙印打得太清晰了,跟她的平凡和道德感有关系。
但我通过这本书想要表达的是平常心是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住的一个准则,不被所谓的梦幻般的大好前程所惊扰、所左右,过我们平凡踏实的每一天,比虚幻的昙花一现的那种感觉要实在和重要得多。我当时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初衷。洁茹你怎么看?
周洁茹:刚才凤群说我们的第一面,她以为我没看到,她以为我没听到。其实我每一个触觉,我都在看你们,都在听你们,所以我是清晰地记得你的。
我们女性作家,我们互相是能够看见、听见的,我们是能够深深共情的。包括后面凤群要去写作,我表现得很冷淡,但是你不知道对于我这样一个人来说,我能跟你说了一句,“你去写”,这已经是我全部的力量和深情了。
李凤群:2000年左右我已经看到了洁茹的书,当时她的名气已经很大了,那时我还没有开始写。当时我在一个写字楼打工,中午休息的时候进了文化宫,那时候的书是摆在外面的摊子上的,我看到了她的书,然后我就写下了《非城市爱情》的第一段话,写完了拿给我们的单位的同事看,她礼貌性得说有点那味道。这让我想起来那个意大利作家写的《我的天才女友》,我们彼此似乎失去了联络。但我们却以未预期的方式重新相认。如果那一次没有看到洁茹的书,我可能就是一个白领,甚至可能是一个老板,因为我觉得我做生意也会做得很好。
周洁茹:你不能够认为这是别人带着你的启发,或者是一个突然的机遇,你不觉得她本来就在那儿吗?
李凤群:太微妙了,就在恰当的时机。因为我刚刚好在我28岁的时候看到了你的书,那时我可以有很多选择,每一条路其实都很难回头,包括我们的人生,包括孩子择校,包括我们在哪买房,在哪生活,找什么样的对象,怎么去生活,其实有时候不都是充满选择的。就是在那天中午我吃过饭,看到了你的书,我发现我认识的人在作家这个行业里面,现实中我打过交道的人她成功了。我曾经迷恋过路遥,但是路遥已经不在了。我认识的人写的书和一本遥远的书带给我的感动和激励,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周洁茹:跟凤群的写作截然不同的是,我的写作是一种即兴式的、碎片式的短篇,我长篇写得比较少,《小妖的网》就是相对长的。当知道你要写一个长篇的时候,我说“你去写吧”,现在觉得这句话太有意思了,太有意义和价值。所以我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凤群的每一本书、每一个字都带着“你去写吧”的力量。
《月下》的深度——真正的生活没有那么多戏剧化的情节,平平淡淡才是真
戴瑶琴:《月下》腰封上有句话是 “中国式的《包法利夫人》,一个平凡女性和世界的对峙和对话”,如果我们不知道包法利夫人是一个怎样的状态,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和世界进行一个对峙和一个对话。封底这句话可能对我们更有启发性,也是凤群自己写,“多数女性的痛苦被吞回去了,而极少数跑了出来”,她写到是余文真从哭泣,到低低的怒吼,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个过程就是女性的心理建设的三个过程,作者告诉我们女性成长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
《月下》这本书,作者在写性别和两性关系的时候,她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应该说是市面上这样写法比较少的一本书。我想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在90年代我们有部电视剧叫《外来妹》,当时是在中央台放的,应该算是爆款剧了,那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看电视剧。如果只记得里面六个女孩的命运和人生经历的话,那么这个作品我们再被发现的时候,它的意义就打折扣,因为这个电视剧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写特区建设的很重要的电视剧作品。
那么在这部作品在塑造两性关系的时候,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笔。就是有一个香港老板叫江生,然后女工叫赵小云。我们在看的时候会发现,江生其实是利用了赵小云,赵小云她是一个女工代表,然后江生不断培养她,给她机会,让她成为自己的副手。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江生的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用赵小云去对抗其她的女工群体,第二个是他把赵小云作为他和内地之间连接的重要纽带,因为他是作为一个港商来投资的。我们看过可能就忘了,也没有人再去开发这个故事。
但是现在有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讲中国式现代化。讲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段经历是写改革开放40年,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又重新想到了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它恰恰讲了一个男性塑造了一个女性,而这个女性原本是他利用的工具,最后她真的脱胎换骨了,站到了他的旁边,跟他形成了对峙关系。
当我看到《月下》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得想到了这个电视剧,我想告诉大家这部电视剧是对这种写法的一种升华。余文真和章东南绝不仅仅是情侣的关系,他们还有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余文真一直没有被看见,但是她在章东南的训练下,章东南让她干嘛?让她去学习,让她去了解各种知识,让她去学习各种礼仪,让她能够成为他群体中的一员,余文真在他的培训下越来越好、越来越丰满。到最后她能够有对抗章东南的力量,这个时候余文真她不甘心沉默了,她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她就是现在的赵小云。
所以《月下》写到了两性力量的一种关系,学生真的被培养起来了,而章东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依然是把余文真当作自己的学生,他依然是对她有一种控制,但他不知道,这个女性她自己已经完全可以独立了,完全可以超脱这种控制了,那么和赵小云一样。最后余文真也是,我不需要你在学什么,布置我什么,指挥我什么,我反而是一种反制,我可以给这个社会提供什么,我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我可以站到你旁边,和你平起平坐,而这个是当时的江生,现在的章东南都无法接受。她写到的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两性的细节关系——一种个人的成长。余文真作为女性的探索过程,它是一个个人的成长过程。当女性的一个成长史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更多丰富的侧面,看到了她们怎么去成长的,怎么一点一点站起来的,这个是特别有力量的一点。所以这是我个人读到《月下》的时候,我就马上能够想起我小时候看的这部电视剧给我的冲击力。
李凤群:我太触动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在小说的结尾,我发现最后章东南变了一个姿态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不痛快,觉得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应该是余文真要给予章东南重重的一击,但是小说里面没有,甚至余文真带着一种非常怜悯的心情起身离开。我现在听到了瑶琴的分析以后我突然就明白了,一个人的真正的成熟成长,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抛开一种偏见和仇恨。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章东南当然是施暴者,是施害者,也是一个不怎么道德的存在,但是章东南在余文真的觉醒的过程当中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是其她人无法替代的。
在这个时候就人有内心的一种那种纠偏的这种意识和自觉,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像电视剧里面一样,当仇人来到跟前的时候,没有一盆水泼过去,没有什么替天行道。因为真正的生活、真正的力量是来自于人的淡然,把自己所有负面的东西抛开,为什么好人是慈祥的,因为好人没有仇恨;为什么智慧的人是平静的,因为只有平静是智慧。我觉得小说唯一的成功的地方,是让余文真真正安宁下来,就让所有的灰尘落于大地上,平静下来。如果说这个小说给人一点启发的话,我觉得瑶琴刚刚就把这个点给她拎出来的。
作者能够掌握这个人物或者这个故事的结局吗?其实不是的,她连她的过程没法掌握,她连她的命运没法掌握,她连她两个人最后变成仇人还是陌路人,她也没有办法,作品中的人物最后有自己的走向、自己的兴趣、自己的路、自己的方向。有时候人家说你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你的作品完成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你遇到了知音,遇到了好的读者,她们会让你的作品再生发,发出一种新的能量和热量。
戴瑶琴:我们自己也在组织读书会,尤其是00后孩子读的时候,她们无法理解章东南变谦卑,原来是这么一个趾高气昂的人,到最后在余文真面前反而是弱势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对比。而且她们还不太理解的地方是余文真不会对章东南施以最强烈的报复,仅仅是通过一些电话的方式,她们觉得这个不是致命的一击,所以她们不理解的是这个过程。
章东南的怯懦和余文真的坚强,这个反而是一种生活的常态。生活没有那么多特别戏剧性的东西,突然这个男主人公要强硬反击,或者女主人公再致命一击,不是这样的。大多数时候是大家通过自己的心理建设和心理觉醒,强化自己各方面的力量而去化解这些东西,反而这个是生活的常态。
我们回到电视剧,最后江生的项目被小云代表的企业拿走了,他对她是多么的不屑,他觉得你只是我培训出来的一个女工,他当时还是把赵小云界定为一个女工。但是章东南不是,这是章东南比江生成熟的地方,他意识到余文真现在和我一样了,我们已经一类人了,她不再是比我低一等的,我也不能再给予她更多的教育,这个时候反而是达成了一种力量的平衡,这个是她两性关系的一种处理。
我在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我摘录了很多的原文,其中还有很多内容是和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是密切相关的。相对于一个女性主题的小说,这部作品它更是反映社会和历史深度的作品。
我还推荐大家去读凤群其他的长篇小说,如洁茹讲的,凤群是有创作的设计和规划的。和《月下》一样写女性的成长、女性的学习、女性的训练的是一个中篇——《天鹅》,《天鹅》的女主人公叫朱利红,后来叫朱利安,她其实就是余文真的前身。她已经经过了中篇的训练,那么到《月下》的时候,她人物会打磨得更加丰满。《天鹅》同样也写了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这也是凤群创作的一个特色。
大系列中,《大望》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偏离,《大望》会写到养老问题,更多放在人心和灵魂拷问。《大风》《大野》《大江》和《月下》这个是一个线索,这一条路其实是凤群对于我们中国的建设、中国的乡土的探索之路。这个是她作为江心洲出来的人,她对于乡土的一种思考,一种心灵之变,她把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和她的心灵之变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不能断裂得去看《月下》这个作品。《月下》它截取的是一段,她写余文真父母的工厂倒闭,在《大野》中可以找到呼应的,又比如说她在写余文真的爸爸再就业,她在《大野》当中写到父亲角色时也有再就业的过程,所以她对于社会的思考是演进的。
作家在每一个作品当中,她不是停滞不前的,她对于同个问题有着再推进、再思考。这个也是《月下》这个作品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学的一个意义。这个作品它并不是凤群写得比较多的乡土题材,反而是个城市题材。但是无论是城市题材还是乡土题材,我们现在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已经不能再用原来的标准去要求一个乡土,或者再要求一个城市。我们的创作是需要当下型的,它是需要和现在的生活和大家的思想观念碰撞的。所以《月下》这个作品其实是凤群对于城市发展的一个思考的呈现,同时它也是对于当下人心态的一种描摹、一种反思,甚至是对于社会上一些现象的批判。所以她的作品里面有历史性,有时代性,这个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这部作品也不能仅仅被认为是女性故事,女性只是一个切口,她要写的是我们整个的当下,它会击中我们的心灵。
那么我们在读文字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比较舒适,是因为作者和我们在一起,作者不再揣测。我举个例子,我是一个70后或者80后的作家,我不是去揣摩60后和50后作家怎么写的,我是在写我们这代人怎么想的。所以她是放在人群当中,放在大家当中,放在读者当中,她越有共情的,写出来东西是我们越是感同身受的。
“每一座小城都有无数个余文真”,用的这个词是“无数个”,是陷入人群当中的,所以这个也是小说的一个特色,就是作家能把自己沉潜进人群当中,这个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作品它是隔着的,要么想着我上一代人怎么写,要么再去接近我下一代人去怎么写,唯独在向前向后的过程当中,我遗忘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写。
在小说当中有一点,我跟凤群讨论过的,小说里有个关于地方戏曲的设计非常有意思,就是章东南的妈妈出场的时候恰恰形成了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一条线索。她妈妈作为一个地方戏曲的传承者,她代表着过去,但她现在依然在唱着。同时当我们看到章东南和余文真关系破裂的时候,完全不影响章东南的妈妈还在成长。我们在小说当中看到了一种对峙,是一种最坚定的矛和最坚固的盾之间的一种对抗。但是章东南的妈妈是超脱之中的,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这个也是凤群想要灌注进去的一种想法、一种特色。
李凤群:实在是太好了。在所有的评价体系里面有一点是我非常看重的,就是一个作家有没有在自己的时代里面,我知道有些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会往回写,写过去、写帝王将相、写发生过的定论的事情是非常讨巧和安全的。写当下、写没有定性的、写大家都不知道的才能够展现你的难度和韧性。我非常喜欢接受这样的挑战,我认为这恰恰也是小说的难度,你有没有嵌入到你真正的生活里面去,你有没有好好得去建造这种有血有肉有灵魂的这样一个房屋。
比方说小说里面就看这个月城,当时这些人生活在巷子里面,所有的人都在等着拆迁,后来也如愿以偿变成了四季阳光,但是当我们还在四季阳光里面兴高采烈得享受生活的时候,时代的大轮已经滚到别处,城东已经开发出来了,开发的进程度是在月城生活一辈子的人没有见识过的,是那样的不知所措。70岁的老母就参与进来,拿出自己所有的钱,要到城东去买一个学区房给自己的孙子,很显然你看到小说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房地产不太好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用一生在追随着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但是这个小说的难度就在这儿,你能不能够有勇气去介入,去跟时代共进退,你能不能够有力量去进入到每个普通的人的灵魂里面去,去过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我看到很多读者就给我留言说余文真就像她自己,或者说像我的姐姐,像我的妹妹。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真真切切地在生活里面,我们活着,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进来,我们不逃离、不游离、不躲避,我们就是英雄,我们就成功了。
为什么《月下》里面没有大喜大悲,因为我的悲喜不在一个作品里面,在我创作的这20年里面,我用20年的作品阶段性得展示,当你读完我所有的作品的时候,你就知道悲喜全在,没有一个人会被怠慢,没有一段感情会被忽视,没有一个人的成长不被看见。(完)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