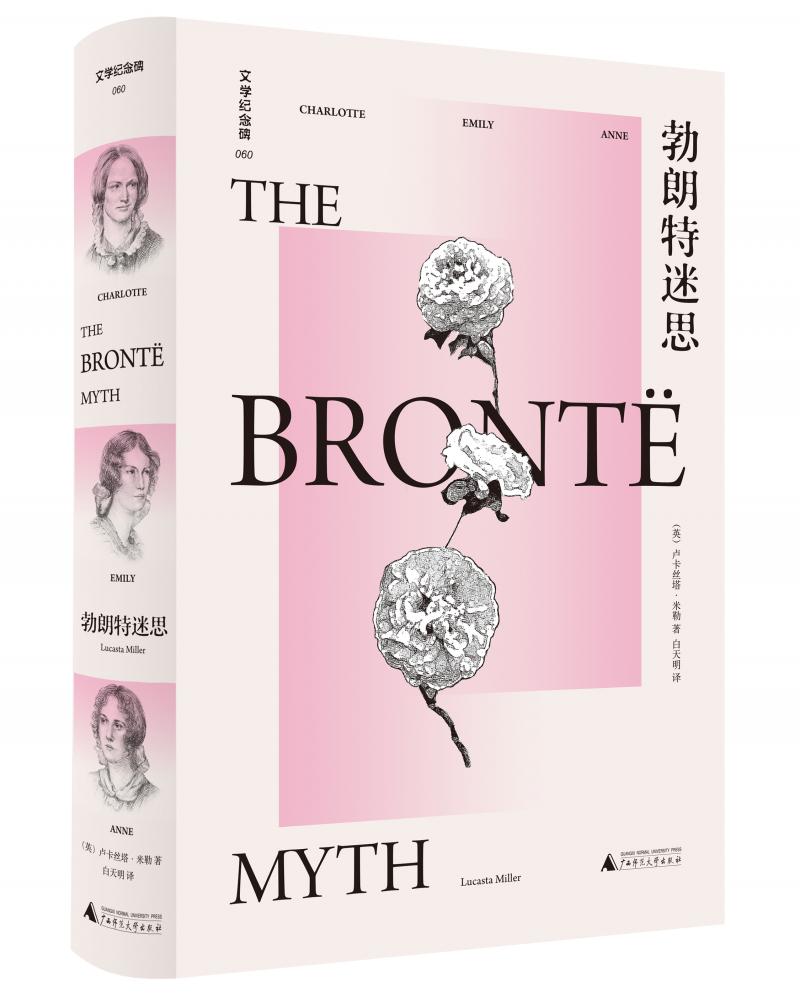《勃朗特迷思》最早出版于二〇〇一年,将近二十年前。它的研究和创作发生在那个网络尚不发达的年代。现如今,那个时代似乎早已逝去,但勃朗特姐妹仍是我们文化中不容置疑的存在。她们的家,即位于哈沃斯的牧师住宅,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就成为朝圣之地,又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变成一座博物馆,吸引了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西尔维娅·普拉斯在内的络绎不绝的游客。这种盛况经久不衰,并在二〇一六年夏洛蒂·勃朗特二百周年诞辰时迎来了又一次增长。如今在推特上,仍有大量用户以艾米莉·勃朗特为精神食粮。
二十岁的夏洛蒂渴望当一名作家并“成为隽永”(“to be for ever known”),对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位默默无闻的教区牧师之女而言,这样的梦想似乎难以实现。但她与妹妹们还是得偿所愿了: 年复一年,新的读者翻开她们的小说,走进她们的生平,让她们的梦想得以为继。
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的家庭故事早在一八五七年,即三姐妹中幸存到最后的,也是唯一一位在生前体会过声名鹊起的夏洛蒂去世仅两年后,随着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夏洛蒂·勃朗特传》付梓,而变得和她们小说中的情节一样家喻户晓。早早便撒手人寰的三姐妹一直盘桓在公众心头,在人们的想象中,她们在位于约克郡荒原边缘的牧师住宅中日咳夜咳,与冷酷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和注定遭受厄运的兄弟布兰韦尔生活在一起。
无论人们怎样讲述她们悲剧的一生,它始终扣人心弦。而在亨利·詹姆斯看来,这些在十九世纪末变得十分流行的生平故事不幸地掩盖了最初让三姐妹一举成名的小说。自那时起,文化就产生了数不清的所谓“勃朗特故事”,包括从学术评论到连环漫画,从传记片到芭蕾舞在内的媒体中的高雅和流行文化。
这本书并非简单复述勃朗特的生平故事,而是探索她们身后的故事,挖掘她们成为传记偶像的历史过程。它通过分析人们对勃朗特故事的不同讲述方式,来追溯它对于不同年代的人们都意味着什么,而故事的起点就是夏洛蒂·勃朗特在妹妹们去世后不久便发表的《生平说明》。这是一份耐人寻味且十分婉转的辩解词,旨在劝说公众谅解妹妹们创作出被当时的报界抨击为不道德的小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书也开启了一项研究: 勃朗特姐妹的名声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而不同时代的人们又是怎样在新的背景下重塑她们的生平故事。如此一来,它显示了她们在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具备持久的影响力,不仅影响了异想天开的怪人(历年都有不少狂热者声称自己受到了三姐妹鬼魂的探访),还影响了商业(你可以享用勃朗特品牌的饼干,我几年前甚至买过一副名唤“勃朗特”的胸罩,而如此命名或许是为了向她们不应得的名声——情爱小说的始祖——致敬)。在我最初创作这本书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疯传”(going viral)一词尚未被词典收录,但这本书就是有关“疯传”的:当作家的生活(无论是内心的,还是外在的)从她们私密的停泊之所挣脱并驶向公共领域时,会发生什么。
这本书的确打破了虚假新闻意义上若干与勃朗特故事相关的“迷思”,譬如艾米莉有一位名叫路易斯的情人,抑或是布兰韦尔创作了《呼啸山庄》。我对虚假传闻的溯源颇有兴趣,喜欢追问它们出现的原因。但我对“迷思”一词的选择还更加微妙。真实的故事一旦进入文化领域并被不断复制也能成为“现代迷思”(modern myths),而对每一个故事的定义都不仅有赖于其内容,还要依靠讲述的方式。
因此,这本书既是对勃朗特三姐妹的批评,也是对传记艺术的批评。我曾在二〇〇一年的序言中使用“元传记”(metabiography)一词来形容这本书。它涉及叙事以及隐含的且往往不被承认的文化环境又是如何塑造这些叙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位信仰弗洛伊德的心理传记作者对勃朗特姐妹的看法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道德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位女性主义者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位好莱坞导演的观点大相径庭。
这让我开始思考在我萌生想法时,对我采用“元传记”手法处理勃朗特题材产生影响的潜在文化。《勃朗特迷思》最初的一位评论家戏谑地评论说,我也应当接受生平研究。那么,我的生平来了。
和众多读者一样,我最初阅读《简·爱》时还是个孩子,大约就是简在小说开篇的年纪,十岁。我喜欢美国诗人阿德里安娜·里奇的说法: 它像一阵旋风将儿时的她席卷,等到了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时的年纪,她又在“需要滋养”的情况下回归这部小说。我现在想,十岁时的我到底读懂了这部小说后半部分的多少内容,但我始终坚信,英语正典中没有哪部作品能用如此大的冲击力表现一个困境中的孩子的视角,即G.H.刘易斯——《简·爱》一八四七年出版时最早的读者之一——所谓的“主观呈现的奇异力量”。我也重读了《呼啸山庄》,回过头来,我还是对当初的自己能从中读出怎样的内容而感到困惑。
我不确定自己最初怎样接触到了夏洛蒂、艾米莉、安妮的生平故事,可能是通过一本有关她们的儿童读物,也可能是借由我童年家中的书架上摆放着的一本菲莉丝·本特利的《年轻的勃朗特》(1960)。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发现了《十二个冒险家和其他故事》,这是一本出版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限量版书籍,摘自夏洛蒂少年时代的幻想作品。它现在就在我的书桌上。从扉页的签名和日期来看,它是我母亲年少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购得的。上一辈人总把自己手中的勃朗特作品传递给下一代,但每位读者总觉得勃朗特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秘密。
在勃朗特姐弟“信笔涂鸦”的启发下,儿时的我也偷偷在袖珍的笔记本上照葫芦画瓢,编造鬼故事。现存的一则故事中有一位名叫安托瓦妮特的女主人公,她的父母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她乘坐一辆马车抵达了一座位于康沃尔的我从未去过的废弃庄园,而迎接她的是她素昧平生的叔叔,十分神秘。锈迹斑斑的大门伴着不免吱呀作响的铰链缓缓打开。庄园里有一位好管闲事的管家和一位名叫厄休拉的恶仆,前者是《简·爱》中的费尔法克斯夫人和《呼啸山庄》中的内莉·丁恩的化身,而后者所到之处总传来诡异的尖叫声。安托瓦妮特无法安枕。皎洁的月光下,诗歌在她的耳畔回响着,带来了有关藏匿的宝藏的神秘讯息。她仿佛在恍惚中被带往了阴冷潮湿的地窖,这里有一个死气沉沉的男子,泛黄的皮肤皱皱巴巴,像是中世纪的羊皮纸,他正透过一个细窄的金属嘴吸食着鸦片。此人正是她的叔叔。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而现在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当初该如何收尾。
虽然我所钟爱的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的《秘密花园》一定混杂在故事中,但我还能从勃朗特姐妹以外的何处得到这种伪哥特的风格呢?这多少是个谜。我从未读过达夫妮·杜穆里埃以康沃尔为背景的小说《丽贝卡》即《蝴蝶梦》,也不曾闻听《奥多芙的神秘》的作者、哥特小说鼻祖拉德克利夫夫人的名讳,哪怕一位天真无邪的女主人公不明就里地被带到一处阴森的老宅子这样的情节早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就被她用到了小说中。激发我想象力的一定是勃朗特姐妹,但现在令我惊讶的是,我童年时代信笔涂鸦,全然因袭前人的做法恰恰说明文化是有历史的。即使我没有读过哥特文学的经典之作,我还是下意识地把它们吸收了进去。
我成长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通过儿童节目《蓝彼得》接触到了电视荧屏上的勃朗特故事,YouTube上至今还能找到这档不可多得的节目,它在孩子面前不摆派头,稍显严肃,现在看来就像是对当时英国广播公司致力于公众服务的广播精神的老套证明。凯特·布什的单曲《呼啸山庄》也在我十一岁的时候发行了。我看到她现身于《流行之巅》这档节目,并在干冰制造的缭绕烟雾中翩翩起舞,但她性感曼妙的律动却让我不敢苟同。勃朗特姐妹之所以吸引我和我之前或之后的许多内敛、书卷气的孩子,就在于她们内心秘密的幻想世界。其他一些粉丝便不像我们这般敏感了。自二〇一三年起,世界范围内的个别城市每年都会举办一场名为“最为呼啸山庄的一天”的会演,而参与者们则会集体再现布什演出时的律动。
我在大学修读英文专业时避免研究勃朗特姐妹,唯恐自己对梦境的剖析会将其破坏。《简·爱》却始终是我心灵的慰藉。有一次,在我乘火车回家的路上,当我读到简逃出桑菲尔德府,不知前路、茫然若失之际,对坐的女士微微前倾,碰了碰我的膝盖,并同情地问道: “很难过吧?”叫我难为情的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攻读英文专业学位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正值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鼎盛期,我们学着摒弃“自由人文主义”的幼稚信仰及其为人所不齿的假设。这种多愁善感在当时的确令我难堪。
勃朗特的传记和她们的小说现在成了我自我逃避时的读物,为的是消遣,而非下一篇要发表的文章。但我阅读的传记越多,我就越关注不同的传记作者都是怎样构思故事的。朱利安·巴恩斯在《福楼拜的鹦鹉》(1984)中质疑了传记“胖乎乎地堆坐在书架上,十分小资”的自足模样。《勃朗特迷思》的创作融合了我贯穿着抽象理论的教育背景和我个人对勃朗特姐妹的喜爱,而这种喜爱也滋养了在我之前的许多人的感受,即一种与三姐妹的十足亲密感。
二〇〇一年,“生命写作”(lifewriting)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说法,而现如今,开设“生命写作”学院的大学不计其数,这使得传记、回忆录和元传记都成了主流的治学目标。但我最初创作《勃朗特迷思》时却并非这般景象。后结构主义理论和所谓的“作者已死”似乎为传记和传记批评这些不被看好的文学体裁敲响了丧钟。后结构主义在最极端之时演变成了对真理的质疑和攻击,其中的相对主义则否定了所谓“事实”的存在。当时学界的一位批评家用十分不屑的口吻说道: “传记作者的身上没有本体论的焦虑。”
但与此同时,传记却在学界以外的其他领域十分活跃,得到了理查德·霍姆斯等人的大力倡导,并出现在A.S.拜厄特一九九〇年布克奖得奖小说《占有》中,后者讲述了一个有关当代文学侦探追踪一对维多利亚时代诗人的故事。在我杂乱不堪的文档中,有一篇我于同年为《新政治家》周刊所写的文章,我在文中通过猛烈抨击批评理论和当时风靡一时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来表达我激进的思想。我天真且强硬地说道,传记和旅行写作等非虚构体裁是新兴的创作形式。
回过头来,《勃朗特迷思》的元传记手法和在弗洛伊德理论盛行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诞生的心理传记一样,都是其所处文化时代的产物。这个时期的传统传记开始放宽限制,珍妮特·马尔科姆的《沉默的女人》(1994)和杰夫·戴尔的《一怒之下》(1997)就是两个例子。前者是对西尔维娅·普拉斯后世改编的研究,后者则是一部第一人称叙事作品,讲述了作者为了创作一部有关D.H.劳伦斯的传记而屡屡受挫的经历。传记体裁的边缘突出了传记的问题,这在让它看似受到质疑的同时,加强了它作为一种叙事形式的合理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期对传记限制的实验性放宽朝着两个方向或各种方向发展起来。它反对因循守旧的美文——这种美文源于维多利亚时代有关传记的看法,盲目地把传记当作颂词——并隐晦地融合了新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勃朗特迷思》试图把文化理论的积极方面——它质疑文化如何产生叙事——和对传记实践的欣赏结合起来,并以此弥补空白。它尊重实验,但对实验的过程保持客观的态度,并大声质疑是否存在一种“确切的”生平。
我所作的叙事是思想史上的一次实践,而勃朗特姐妹就是我的目标。它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关注夏洛蒂,第二部分关注艾米莉。我虽然也痴迷于安妮·勃朗特(她的小说不像两位姐姐的作品那样拘泥于浪漫主义),但让我大失所望的是,没有足够多的材料供我创作有关她的章节。简单来说,尽管她和艾米莉一样神秘莫测,但她所启发的传记作品微乎其微,不值得人们对她的后世刻画进行研究。奇怪的是,夏洛蒂有着翔实的生平记载,却在妹妹们辞世后毁掉了她们的书信和其他作品。这促使人们争相“解释”艾米莉的神秘,而安妮却被晾在了一旁。
如果我能重新创作这本书,我要做出哪些改动呢?从我开始创作这本书起,我就对勃朗特姐妹的文化背景(而非她们后世的形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她们成长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即浪漫主义者和维多利亚人之间的“奇怪停滞”期,而当时的文化背景帮助塑造了她们的文学理念。这也是我在研究了利蒂希娅·兰登(“L.E.L.”)的生平和作品后得出的结论。L.E.L.是勃朗特姐妹成长时期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一,她死于一八三八年,去世时手中握着一瓶氰化氢。尽管我知道夏洛蒂和艾米莉对她青眼有加,甚至临摹了她诗歌中的一幅插画,但我在《勃朗特迷思》中并没有提到她。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名不见经传,而现在看来,她对勃朗特姐妹产生的文化影响比我当初所知的要大得多。
我从开始创作《勃朗特迷思》以来,就反复阅读了《简·爱》《呼啸山庄》和夏洛蒂的杰作《维莱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它们的文化背景。这让我在赞赏这些小说原创性的同时,不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家们瞠目结舌的反应那样冷眼相待。不同于那些被改编过的好莱坞版本,这些书籍始终令人惴惴不安,充斥着冲突和矛盾,而这些冲突和矛盾也促成了它们的力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在道德评判方面逡巡畏义,这并不正确,但他们诚实地表露出了自己的不安。我仍惊异于《简·爱》这部作品,却与女主人公的第一人称视角愈发疏离;让我感到愈加困惑的是小说中残酷但没有得到解决的权力关系。
勃朗特姐妹的创意是(也该是)有感染力的,但问题始终在于非虚构体裁怎样描写她们的生平才堪称最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传记影片《魂牵梦萦》在事实方面不甚严谨,竟编造出一个三角恋的情节: 夏洛蒂和艾米莉都争相吸引教区牧师阿瑟·贝尔·尼科尔斯的目光(在现实生活中,嫁给他的是夏洛蒂)。虽然萨莉·温赖特最近的电视电影作品《隐于书后》(2016)更忠于现实,但它强烈的自然主义却无法涵盖主人公内心的幻想世界,毕竟她们的文学作品是借由幻想的媒介才得以问世的。
伊莎贝尔·格林伯格即将出版的漫画小说《玻璃镇》聚焦于夏洛蒂真实生活和幻想世界的交界处,这让我不禁联想到艾米莉取名“贡达尔”的幻想世界的潜力——据记载,她曾与安妮在通往约克郡的火车上分角色饰演幻想世界中的人物。艾米莉和安妮的手稿都散佚了,贡达尔的故事只能借由推测而被重构,但这也让那些富有创意的改编者有了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我们知道,贡达尔启发了艾米莉的一些绝佳诗作,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式的传奇,有着一位强大果毅的女主角,涉及权谋、情爱、战争与背叛。通过现代电脑三维动画技术,艾米莉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自己笔下的女主角,而贡达尔的大军则在约克郡的荒原上集结。我只是想想而已……
卢卡丝塔·米勒
二〇二〇年一月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