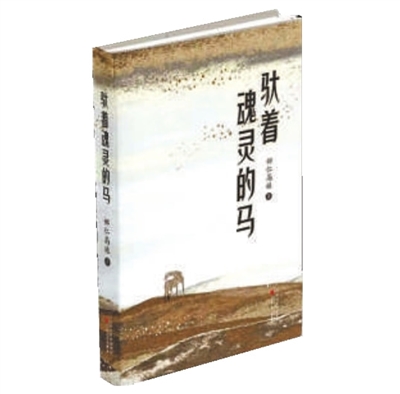在九月揭晓的第二十一届百花文学奖中,娜仁高娃的《醉马草》荣获短篇小说奖。评论家孟繁华这样评价她的创作:“她一直关注生活的幽微处,那些习不察焉的幽微处就是最能表现人性况味之处。”此前,她的短篇小说《驮着魂灵的马》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短篇小说奖。评论家贺绍俊说:“我们从娜仁高娃沙窝地的故事里,能感觉到有一座庄严的高山作为背景在默默地观望着。她并不追求强烈的动感,舒缓平静的叙述就像是静默的高山,凸显在你的眼前,让你感受到高山的无言却传递着无比丰富的言说和无比宽厚的温情。”
娜仁高娃最早是用蒙古文写作的,后来用汉语写作。她的小说《白驼》2012年首发在《草原》,这篇小说以沙砾般坚硬而有辨识度的文字,勾勒出沙窝地的轮廓,也带给了读者新鲜感。那之后,她的四部中篇小说《雌性的原野》《一个陌生女人的葬礼》《天脉》《马楠河左岸》相继亮相,库布齐沙漠的风、传说与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构建出一个既真实又神秘的独属于她的文学原乡。2018年,这位80后作家以《热恋中的巴岱》《醉阳》两篇小说摘得第十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
近年来,娜仁高娃以勃发的创作力,连续发表小说《阿拉姆斯》《苍青色长角羊》《苍色海螺》《透风的墙》等,她的作品如同沙窝地里旺盛的青草,不仅为当代小说注入独特的新的气息,也逐渐走进更广阔的文学视野,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
1
写作是要绕开“陷阱”,回归质朴
北青报:得知《醉马草》获得第二十一届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第一反应和心情如何?在你看来,奖项对文学创作的生涯意味着什么?
娜仁高娃:第一反应啊,当然是很开心,觉得自己好幸运。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当一篇作品见刊、发表后,与作者是处于“分离”状态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独立性。所以,当我得知《醉马草》荣获百花文学奖时,作为作者我为它能受到读者与专家老师的认可而感到欣慰。至于我自己而言,十多年的文学生涯好比是在限速的公路上行驶,纵然你有满怀的激情与热忱,也得放慢速度,遵循文学本身的规律前行。而各类文学奖项则是路旁的绚丽奇景。在这里,你会停住观赏奇景,同时也会偶遇与你同时间抵达这一奇景的人,你们会交流,产生共鸣或者分歧。然而,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面临的是道别,因为你们始终在路上。所以,各类奖项是一次馈赠,意味着可遇不可求。
北青报:《醉马草》的创作灵感来自何处?是生活中的某个具体事件、人物,还是长期对草原生活的感悟积累?选择“醉马草”这一草原植物想表达怎样的独特意象?其中眼盲小女孩和公羊“将军”的故事线,是如何构建起来的?
娜仁高娃:醉马草是一种有毒的植物,在年景不甚好,雨水特别少的大旱年,它的长势会很旺。它散发的气味还会诱导畜群不断啃食它,直至进入一种“成瘾”状态。在我家乡,有时候还会特意动员大家刈除醉马草,足见这种植物的侵蚀性与破坏性很强。短篇小说《醉马草》的地域背景是我的家乡,我们当地人称其为“沙窝地”。小说中“将军”的原型是我叔叔家的一只种公羊,这只羊脾气暴躁,除了叔叔,任何人都无法靠近它。偶尔家里来个客人,它都像条守门犬似的追着客人顶。后来,叔叔把它送给朋友。这位朋友为了调教它,把它独自拴在滩地,一连好多天。有一回,叔叔去朋友家,它老远便认出了叔叔,使劲儿地叫唤,叔叔不忍心又把它牵回来了。再后来,又有一个邻居在野地遇见了这只羊,然后便上演了人与羊的决斗。最后,这位邻居抓把沙子撒进羊眼后才得以脱身。叔叔跟我讲这些的时候,他眼睛里是闪着泪的。我记得,当时叔叔还跟我说了句,它呀,也是个爷们儿。
在草原上,牧民总会偏爱家里的某只羊、马、骆驼等,还会通过某种仪式,将某只家畜供奉为“神羊”“神马”“神驼”,以表达对自然界种种生灵的敬畏。这种风俗的根源是牧人心中众生平等的朴实价值观,同时也是万物有灵论的思想体现。短篇小说《醉马草》中的盲女身上所体现的恰好是这种价值观。一草一木皆与人类一样,具有生命的尊严与价值。
北青报:提笔写作的过程中,你是如何将草原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等元素,转化为一种质朴的、独属的叙事风格?
娜仁高娃:对于我来讲,故乡的一切就是我想要表达与发现的。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我觉得需要绕开很多“陷阱”。我所言的“陷阱”,指的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时时刻刻会遇到的、来自作者本人的无病呻吟与一意孤行。往往在那瞬间,我选择停下来。我担心陷入一种不理性的状态,然后以撒娇的心态,在盲目的自信的驱使下,用华丽的辞藻堆砌空心阁楼。毫不隐瞒地讲,我一不小心就会写出那样的句子。于是,我会删掉,让一切回到先前的空白、洁净,但是总会留下“蛛丝马迹”。为了克服这些,我常常回到故乡,或者到荒野、戈壁去。当我面对古朴的自然界,我会感到最简朴的愉悦。我发现,走在宁静的湖边,空旷的戈壁、草原,人会自然而然地压低嗓门,甚至不言语。不是自然界需要我们,而是我们的心灵需要自然界的滋润。每一块儿石头,或者每一棵树,每一条小河,都在提醒着我们要安静下来。而心灵的宁静,终归是我们最终的追求。因此,我想做的就是用毫无矫饰的语调、质朴的文字讲述这一切。
2
现实生活中衍生的故事,是生活的“翅膀”
北青报:百花文学奖授奖词中提到,“以惊人的克制与细腻,于无声处倾听灵魂的低语”,你如何理解这种叙事风格的评价?从《驮着魂灵的马》到《醉马草》,你是否在有意转换叙事节奏和语言风格,比如,有读者觉得读《醉马草》更简洁而不失意蕴深长。
娜仁高娃:其实,之所以克制,是因为我想较真实地呈现沙窝地牧人的典型性格。也许是地理环境的缘故,我家乡的很多人不善言辞,或者说不习惯滔滔不绝,而是习惯安静、内敛与自省。这种性格特征给人一种冷漠与木讷,实则上是一种内心的丰盈。假如,读者从一篇作品中感受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气场,直至与人物产生共鸣,这是对作者无言的赞美。
在我看来,一个写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应该对每一位人物的脾性、着装、言谈等等要有负责到底的态度。虽然,在写作中往往会因为一句对话而使人物不再按作者的预设发展下去,但是整体上作者还是要做到遵循人物的预设而选择恰当的语言、细节、情节等等,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个情感真实的作品。只有情感真实了,读者与写作者之间才是不存在鸿沟的。这不是写作者对读者的讨好,而是对读者的尊重。
对我本人来讲,每一次创作都是从零开始的过程,我没有有意转换或者调整创作风格,我只是想做到情感的真实与细节的真实,其他的我几乎是不考虑的。
北青报:你作品中浓郁的草原元素和童年记忆令人印象深刻,童年生活对你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娜仁高娃:我始终认为文学是一门想象的艺术。在我这里,第一个赐予我想象的翅膀的人是我太奶奶,也就是我父亲的祖母。我的太奶奶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所以,她的生活起居需要一个活的“手杖”,有那么一段时间,这支“手杖”便是我。听我母亲讲,有几次,我牵着太奶奶走到野地后,居然也把眼睛闭上,导致两人越走越远。这些细节我是不记得的。在我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太奶奶教我唱儿歌的瞬间,有的儿歌我至今还没有忘记,还有就是她给我讲过的民间故事。比如,她给我讲的一个年幼的孤儿被恶魔杀害掩埋后,在他坟头长出了一朵花,然后一头牛吃掉了这朵花,生下一个有银胸金臀的小牛犊,后来这牛犊与恶魔斗争,最后打败恶魔。我记得,自那之后,我真的是在牛群里找那种小牛犊。
童年时,我经常从我的太奶奶口中听到关于《阿尔吉布尔吉汗》《银胸金臀的牛犊》《阿拉姆斯》等民间传说故事。无论是用歌声、祭祀仪式、肩胛骨占卜,还是用民间故事,他们所表达的近乎都是对大自然的赞美与敬畏。
如今想来,是这些民间故事在潜移默化中给我呈现了另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相信这个世界的存在的。所以,我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喜欢捕捉现实生活之外的,或者说是现实生活的隐匿的衍生部分。它们不是魔幻、传奇的故事,从来都不是,而是生活的“翅膀”,具有冲淡、驱逐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不愉快事情的魔力。
北青报:通常你是怎样开始对一部新作品的创作,有怎样的写作习惯?遇到过哪些困难和挑战?又是如何克服它,完成它的?
娜仁高娃:很多时候,我的小说的雏形大多是一个非常细微的细节,一句话,一个眼神,或者是留在记忆里的某只沾满泥沙的玻璃瓶等等。我把它们有意无意地“埋”在心底,任其自由生长,耐心等候它们自行破土而出。当然,有时候也会硬写,但是往往会非常地吃力。我习惯在音乐声中进行创作,而且随机选好一首歌、一首曲子后无停止地单曲循环播放,直到结束创作。
文学创作是个体劳动,难免遇到很多困难。我不是说群体劳动就不会遇到困难,我的意思是,一个写作者遇到困难时是没有伙伴的,也没有退路,也无法逃遁,除非放弃。对我而言,在创作过程中最难的是找到合适的第一句话,或者开篇的第一段,如果找不到第一句话,一般情况下我是很难写下去的。
3
我习惯写沙窝地的人,因为他们给我一种亲切感
北青报:你的多部作品以家乡“沙窝地”为精神原乡,这片位于库布齐沙漠腹地的土地,为你提供了怎样的创作养分?
娜仁高娃:在我很多作品里出现的“沙窝地”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的出生地。它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北端,紧挨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齐沙漠大原野地。我们当地人称其为沙窝地。那里地形与山地相比虽然是平展开阔的,但是那里没有碧草连天的草原,而是处处有低矮的沙丘,很长的缓坡,植物多数也是耐干旱的蒿草、芨芨草、甘草、苦豆草等,地理上称这种地貌为荒漠草原。也许,那里的僻静与空旷会使人感到一种寂寞,但对我而言,那里是与我内心的悲伤产生共鸣的地方。比如,当我父亲过世后,我回到沙窝地,站在某个沙包上时,感觉那里的草木都因为父亲的离去而变得荒芜。
我想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有仅属于他自己的心灵故乡。幸运的是,我的心灵故乡与真实的故乡是同一个地方。那里有我的亲人,有我童年的伙伴,还有我从未见过的,但留下很多传奇故事的人。我觉得,归根结底,文学的核心是人。所以,我习惯写沙窝地的人,因为他们给我一种亲切感,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是他们的,同时也是属于我的。
北青报:作为年轻一代蒙古族作家,在创作中如何传承和创新蒙古族文学的传统?你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收获怎样的位置和价值?
娜仁高娃:刚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时,我是用我的母语,也就是蒙古语创作的。后来改为汉语写作。不管用哪种语言创作,我觉得很多写作者都是在不知不觉中从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了许许多多的养分,然后以自己的方式再现了那个民族独有的性格。在具体创作中,当我塑造某个人物时,我警惕的是“符号化”的人物。我希望我能在作品中塑造没有“符号化”的人物的形象。同时我也觉得,如果一个写作者塑造的人物涉嫌“符号化”,那是一种对自己创作的敷衍,也是对复杂人性的一种规避。
至于我的作品能够收获怎样的位置与价值,那不是我来回答的问题,也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一切顺其自然吧。
北青报:在将草原文化和沙漠生活体验转化为文学作品时,您如何实现文化内涵的准确传递,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产生共鸣?
娜仁高娃:也许从小生活在沙窝地的缘故,我对沙漠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很熟悉。所以,当我以沙漠为背景写作时,我会很轻松地表达我的发现。我追求一种心理上没有负担的创作过程,这使我会感到创作的过程比结局愉悦。我想这也是我一直坚持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我始终坚信,文学的“主人翁”是人。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朝代的人,在人性面前,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突出的差异。古人身上有的七情六欲,今天的人身上也有。无论何种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有人类的影子。所以,我想,只要你足够真诚,你的读者都会接纳你的。
4
文学负责再现,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
北青报:你曾经说,写作是一种与自己相处的方式,如何理解这句话?
娜仁高娃:有一次,朋友跟我讲起他失踪多年的叔叔的故事。这位失踪者是朋友父亲的亲弟弟,失踪那年刚二十出头,当时我的朋友六七岁。朋友说,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身边多了一个人,一个呆痴而言语不多,双手没有手指头的人。后来他得知这个人是他父亲的弟弟,他从北京徒步走了一年多回到鄂尔多斯腹地,他的手指就是在回家途中冻掉的,还有他的精神状况也应该是在途中遭遇什么而受了影响。
在朋友的记忆里,他的叔叔是某个夜里突然离家出走的。我朋友年近四十,这些年来他的父亲从未停止寻找失踪的弟弟。“我们一家子总是在谈论我的叔叔,我们都很想念他。”当朋友坐在沙发上以这句话结束他的讲述时,我和另外一个朋友都望向窗外。我记得很清楚,有那么几分钟,我们三个谁都没再说话。人与人之间的思念,那种深藏于心底,在午夜突然醒来时悄然而至、绵绵不绝,而又毫无盼头的思念,我想每个人都深切感受过。
有人说,当今时代因信息的高度发达,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思念”之美。但是,总有一些人,我们纵然将地球掀翻,也不可能再次相遇。而此类“思念”本身所带来的伤感,或许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永远都无法排遣的情愫。而这种情愫,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在一种旁人无法察觉到的时刻,走近我们自己。说到底,写作是一种与自己相处的方式,一种分析自我内心活动的过程,一种丰富自己人生经验的实践。虽然,我讲述的是朋友的故事,但我把那位我从未谋面过的“失踪者”当成了我心底的某个人。可以说,这些情愫也是诞生我的小说的催生剂。
北青报:我注意到,您的作品多发表在《草原》等文学期刊,从内蒙古走向全国。在这个过程中您如何看待作者与编辑的关系?同时,您参加过许多文学交流活动,这些交流活动对您的文学创作理念有何影响?
娜仁高娃:在文学事业的进程中,除了作者本身不可缺席外,编辑与评论家都不可缺席。三者密切相关,才会有某一个时期的文学的发展。我与《草原》结缘于2009年,至今我的多数小说都是在《草原》发表的。作为文学刊物,它给我提供了很多平台,这是难能可贵的,除了《草原》,还有我家乡的刊物《鄂尔多斯》,也在我初期创作阶段赐予了我极大的鼓舞。我觉得,一个作者与编辑最轻松的交往就是相互的信任,你信任我会尽力去创作,我信任你会中肯地对待作品。
这些年我参加的文学交流活动,多数也与《草原》相关。对我而言,每一次的活动都是一次与同仁们的交流与学习的机会,同时也是积累经验与整理创作理念的过程。
北青报:你的一些作品都体现出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深度思考,比如,《醉马草》中提到很多动物都有自尊等等。你认为文学如何承担其生态关怀的责任?
娜仁高娃:我觉得,文学不该承担任何责任与关怀,它负责再现。或者说,把人类生活与生活中的众多问题用艺术的方式展示给大家,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
北青报:获奖之后,未来的创作方向会有哪些新的探索?
娜仁高娃:在我这里,能获奖是件很幸运的事情,说明作品受到了认可,这点使我很欣慰,也很开心。然而,获奖不是我创作生涯中的分水岭,它只是幸运之神的降临。至于今后,仍是未知。每一次创作都是新的体验,都是从零开始的过程。所以,我仍在探寻的路上。
供图/娜仁高娃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