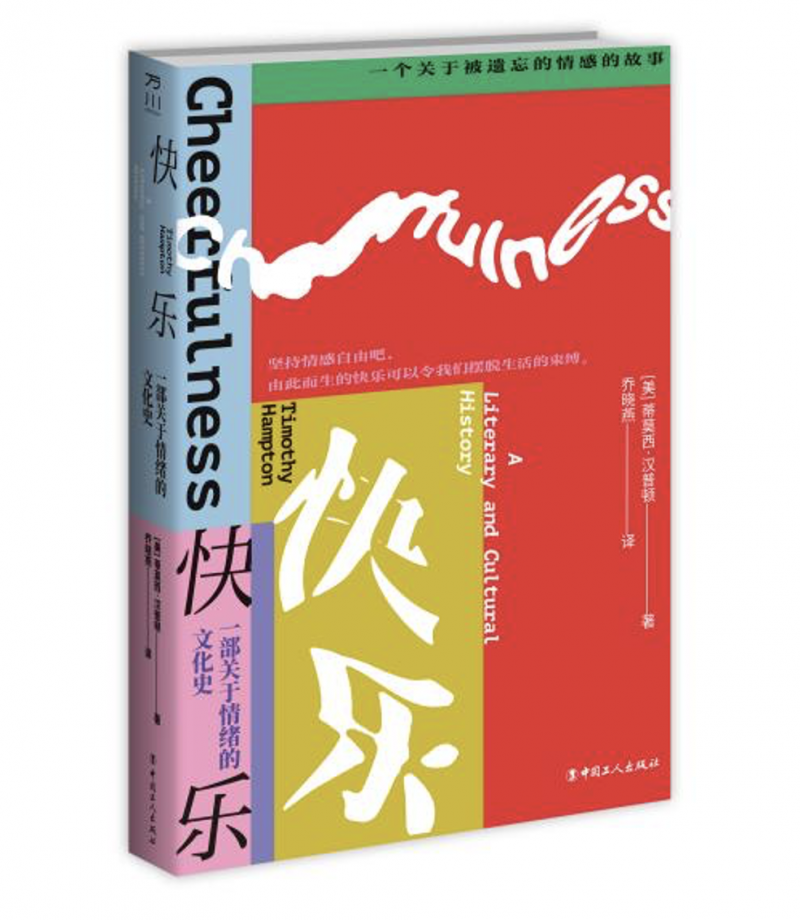在狄更斯的小说中,经济成功是建立在才华和勤奋之上的。科波菲尔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天资聪颖、持之以恒,当然也得益于富亲戚姨奶奶所提供的物质支持。狄更斯借用了古老的传奇情节线索——“捡来的”孩子原来是个王子——并通过改编使它适用于19世纪英国新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在奥斯丁笔下,快乐作为上层资产阶级的美德,体现在约翰·威洛比这个角色身上,并对其进行戏仿;而在狄更斯的小说世界里,快乐无法成为主人公的情感美德,因为赚钱这样令人尴尬的主题是不足为上层人士挂齿的。事实上,正如亚
当·斯密提醒我们的那样,“快乐”经济对个人所造成的后果是过度劳累和精疲力竭。因此,快乐必须由其他角色来体现。奥斯丁已经谈到,快乐这种性格特质是可以伪装的,成为一种在小群体中传播的表面价值,并以欺骗的形式存在。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快乐不仅是忧郁的反面,它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最核心、最积极的力量源泉。但它却不能由书中最快乐的角色,即叙述者自己口中说出。因此,狄更斯将快乐置于艾妮斯的快乐面容之中,古米治太太从忧郁到快乐的转变之中,以及汤米·特拉德关于找到理想伴侣的婚约秘诀之中。
然而,如果快乐由逆境中滋生而出,如果爱和野心与科波菲尔沉默的快乐形影不离,那么在小说的最后部分,我们终于看到他“变得”快乐,这不是一个富有野心的作家的快乐,而是一个爱人的快乐。在朵拉死后,科波菲尔回去拜访姨奶奶,当被问及文学创作的艰辛与收获时(“准是能实现理想,受到称赞,得到同情,还有许多别的好处,是不是? 好啦,你走吧!”),他反而答非所问地提到了艾妮斯,他听说艾妮斯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当得知消息为真时,我们看到整个小说中非常罕见的情形出现了:科波菲尔似乎完全不知所措、困惑迷茫。他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明白现在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情绪,但是这对于他来说太难了:“于是我就拿出更大的决心,让她看到我脸上非常愉快的表情。”随后他便得知艾妮斯要结婚了,于是拿出更大的决心:“‘愿上帝保佑她!’我愉快地说道。”此时的科波菲尔更像是约翰·威洛比,只是比威洛比更值得同情——他在即将来临的灾难面前,仍在努力显得快乐。说完之后,科波菲尔出发去找艾妮斯。只有此刻,在天塌地陷之前,他才能对她“直说”自己的想法。和姨奶奶的谈话让他明白了自己面临的风险。此时此刻,“快乐”是面对危机时的预期反应。然而,科波菲尔表现出的并不是一个被抛弃的情人的快乐,而是发出声音,来表达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他并没有像克鲁普太太所建议的那样,只是简单地振作起来,而是向那个同样爱着自己的人表明心迹。从这幸福的时刻开始,他可以愉快地回忆自己的生活了。
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快乐是小群体生活中的黏合剂。奥斯丁将快乐投射到与时间的关系中,使之成为女性行为的理想标杆。狄更斯面临的问题:在其他社会群体闯入(富有的斯蒂福兹对艾米丽的引诱),或者职业化的资产阶级自身能量(科波菲尔作为著名的大律师)的影响之下,小群体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分裂的?狄更斯写出了许多小群体内人们的生活,有的混杂在一起,有的甚至互相敌对,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化甚至暴力的世界中。休谟曾经说过,快乐可以使人拥有共同的体验,快乐像火焰一样在房间里飞驰,触动眼前的每一个人。与休谟相比,狄更斯笔下的群体则更为复杂,这些小群体生活在压力之下。古米治太太从一个闷闷不乐爱抱怨的人,变成一个快乐的帮手,从中可以看出快乐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其他小群体如裴果提先生的船屋,里面居住着淳朴的下层社会人民,象征着男主角儿童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情感机制,当它遭受威胁时,忧郁和懒惰就会转变为快乐和勤奋。在叙事主线中,这个形象得到了继续深化和扩展:当艾妮斯从开始的“恬静”转变为日常的“愉快”时,这说明男主角的情感生活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艾妮斯不再仅仅见证那些身处危机之中的人物如何经历情感挣扎(如奥斯丁笔下的埃莉诺·达什伍德观察着威洛比和玛丽安),而是通过承担见证者的角色,成为科波菲尔自我定义中的一股关键力量。看起来,野心和快乐是可以共存的,但需要一个起到调和作用的人物,这个人物不能是野心勃勃的男主角。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