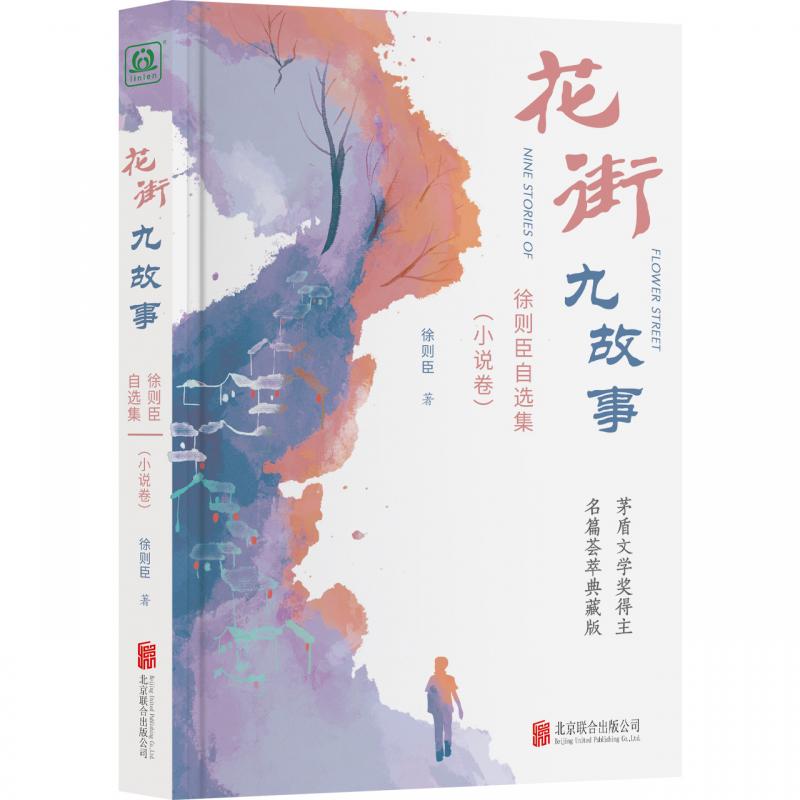文/朱轶
14年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有次在网络冲浪中,看到有人推荐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名非常西方,叫《耶路撒冷》,作者叫徐则臣,男,70后。
好奇之下,便从网上买来这部小说,很快就读完,并从此成为徐则臣的拥趸。
我一度非常兴奋,感觉年轻一代作家终于出了个像样的人物,这当然只能体现出我的孤陋寡闻与浅薄无知,年轻一代(70后)其实有很多不错的作家,只是大部分仍不为广大读者所熟悉——但我相信,徐则臣在这个年轻行列里,肯定属于前排。
也是自那以后,开始关注徐则臣的创作,从《如果大雪封门》到《王城如海》《北上》……看着他一步步拿下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心里很是为他高兴,也有种微妙异常的激动,好比自己曾看好的一支潜力股,正如当初所愿地那般开始爆发式增长。
《北上》之后,就开始期待徐则臣新作,直到今天。
可不曾想,新作暂未等到,却先读了一本徐则臣的小说自选集《花街九故事》。
熟悉徐则臣作品的都知道,花街是他创作的原点,也是他文学世界最初开辟的疆土。他来自花街,写花街,也从花街走向世界。花街于他,就如同苏童的香椿树街、莫言的高密乡或阎连科的耙耧山,是一个作家心心念念、难以割舍的根。
集子里九个故事,几乎都曾在不同地方看过,隔了有五六年,记忆难再重叠,个人经验、品味、眼光也已迥异当初,如今再看,这些文字、故事仍然有其动人心魄的地方,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1.《花街》
第一篇小说叫《花街》,或者说,把这篇放在开始的位置,除了名字的贴合,自然也有些其他意味。对作者而言,花街是个地方,是个名字,更是一个特殊的载体,它承载着旧日码头兴盛、衰败的历史,也见证了往日生活、人情的变迁。
它如同一个自足的社会,尽管面对着外部世界的冲击,尽管不断地迎来送往,却自有一套似乎亘古不变的生存、交际以及人情法则。
故事中,修鞋的老默,守着卖豆腐的麻婆。以老默的死亡为切点,来倒溯一段历史。背后的爱与恨、纠缠与执着固然动人,但作者真正想要描述的,其实是花街。在质朴动人的爱情背后,不断招摇着闪现着的,其实是水汽缭绕的石码头、湿漉漉的青石板路、挂在门楼上或屋檐下的小灯笼。
所谓花街,就是附着其上的、全部的喜怒哀乐的日常,以及悲欢离合的人生。
2.《如果大雪封门》
这是我最爱的小说之一。如果大雪封门,多么诗意的表述。
它也确实是一篇非常诗意的小说,无论是房顶上被风刮着在地上拖来拖去的板凳,还是天上伴随着鸽哨声、一圈一圈飞翔着的鸽群,还是在北京西郊巷子里奔跑、追逐鸽群的小人物们……都让人感觉到一种溢出现实的诗意。
大雪封门,多美的意象,对南方青年林慧聪而言,它甚至成为某种执念,为了在北京看一场大雪,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能够留下来,等到大雪落下的那天。这就有了某种诗意化的象征意味了。
最终北京下了场大雪,天地皆白,然而雪并没能够覆盖一切,北京林立的高楼,那些光滑的玻璃幕墙,依然像裸露着的脊背,森然地背对着他们,也冷漠地拒绝着他们。
但是在这里,现实的残酷是一方面,也早已定下了基调,开头被打成傻子、被接回家的宝来,隔三差五不断减少的鸽子,其实都昭示了小人物们大同小异的结局;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一种高于现实、尽管也为现实所困的理想。一个人在寒冷中所生发的温暖,尽管轻易就被寒冷覆灭,可这温暖自有其意义。
好比文字构建的世界,尽管虚妄、脆弱以至于轻易崩塌,但它多少也曾经或正在、甚至不断地为一些人提供庇护,无论这庇护是长久还是短暂。
3.《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埋头狂奔,或畏缩不前,或原地打转。但大部分时候,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条路是看不见的。
也有人会重新发现自己的路,重新上路,甚至爱上了旅途,在这篇小说里,虚指的人生路,和实际中的满世界跑,混为了一体。
小说的主人公起初喜静不喜动,害怕噪音,拒绝热闹,一心钻进自己的小世界,看书练书法;但他却有个喜欢旅游到处跑、并试图拉他一起跑的妻子。结果闹了矛盾以至于离婚,其实是发现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终究还是无法容忍彼此的差异,哪怕是打着爱情的幌子。
吊诡的是,离婚过后,主人公反而爱上了到处跑,让自己永远处于“在路上”的状态。
后来在一次旅途中,主人公遇见了一个女子,并得知了她的故事。丈夫蒙冤入狱,她每个月都去看望,自以为两人情比金坚,结果丈夫出狱后,性情大变,曾经的誓言、恩爱,就像突然过期的食物般变质腐烂。
作者在这里展示了另一个样本。
也许人在生命这趟旅途中,确实难以找到一个永久性的、安全稳固的落脚处,你眼下所能停靠的,或正在停靠着的,可能都只是这一程里的驿站、码头。
或许是我看得悲观,反正从这格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路上,也只能在路上。
4.《人间烟火》
如果说《花街》像是简练的序曲,这篇《人间烟火》就是曲折、铺张的四幕剧,而花街则像是一个大剧场。
它讲了一个家庭的悲欢,在命运肆无忌惮地撕扯下,人可以坚韧地活着。
也可以说,这篇小说就是徐则臣版、花街版的《活着》。
贯穿始终的,是花街上人情的温暖互动,是生活中那呛人的烟火气,沾染着普通人的苦乐与悲喜。
5.《失声》
《失声》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是发生在花街上的独幕剧。
姚丹的丈夫入狱,为了撑住和丈夫辛苦打拼建立起来的家,姚丹含辛茹苦,终于还是选择了在屋檐下挂起灯笼;后来意外从事哭丧,因自身悲苦,所以借他人之丧,哭自己之悲,效果竟出奇得好;
另一面,监狱里的丈夫因妻子久未来信,加之寄来的钱较之以前有所增多,猜测到姚丹许是干起了花街上的皮肉生意,为了见妻子,他不惜越狱,最终落得死亡下场。有点古希腊悲剧的风格与意味。
故事结尾,是姚丹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哭,这哭声虽大,却只有自己听得真切。
6.《大水》
这篇小说写得非常收敛,看似没头没尾,细节涣散,实则有一种叙述技巧上的探索,以一种受限制的儿童视角,展开一个貌似情杀的狗血故事。配合着大水漫灌的背景设置,构成了花街众生态的一幕。
结局颇耐人寻味。
7.《苍声》
徐则臣以儿童视角,把我们代入花街的特殊时期。
故事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对何老师的批斗游行,二是“我”的成长,前者的发展也是对后者的推动。在这里,徐则臣以较长的篇幅、较浓的笔墨,对故事进行了细密的铺排,同时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叙事特征,对某些特定事物的锚定式描写,它们既是推进故事的关键线索,也是来回照应、比对的某种参考物,以此表现人物。
更重要的是,借由这种方式,将故事中难以言说的部分具体化,用一个一个“道具”使之进入象征的层面。这一特征,在之前就有出现过,比如《人间烟火》里的“白蛇”。
在《苍声》里,这一设置就更加明显了,如何老师的礼帽、“我”家的狗,以及所谓“苍声”。
所谓苍声,就是生铁一般的嗓音,是成人的象征,以区别于童稚之音。
小说中的“我”,在经历了心爱之物被剥夺、身心被侮辱被摧残之后,在历经恐惧战栗之后,在流过了血与泪之后,在满腔血气被激起之后,终于一夜之间“苍声”了。
成长的代价,明码标价。
8.《镜子与刀》
镜子与刀,是一组独特的意象,构成了微妙的对比。穆鱼被禁足在阁楼上,九果则随乌篷船来到花街。两个男孩,用镜子和刀,通过反射的光来沟通、确认彼此,建立了超乎寻常的联系。这份连接突破了距离的限制,是两个孤独心灵自发地靠拢到一起,既是慰藉,也有寄托,因而具有了更纯粹更具穿透力的深度。
而这两者的对照也别有意味,镜子代表了内敛与敏感,可以静观自我,刀则天然地有一种锐利的锋芒,即使这种锋芒一时被压抑,但既然出鞘,迟早会见血,会展露霸道的一面。
镜与刀,阁楼与渔船,固守与流动,此地与远方,这些相互对峙又联系在一起的事物,以及背后的延伸,是跃然于文本之上、更具有启发性的象征。
9.《伞兵与卖油郎》
这是一个关于起飞与坠落的故事。
范小兵从小立志当一个伞兵,却遭到父亲严厉反对。父亲老范是退伍战斗英雄,由于打仗受伤落下残疾,不能行房事,导致妻子跟别人跑了。因此他拒绝儿子的梦想,一心希望儿子继承家族事业卖酱油。
可少年的梦想强大且无畏,足以抵抗任何和翻越任何阻碍。为了成为伞兵,范小兵想尽办法,他用雨伞和床单自制了降落装备,并进行跳伞训练,冒险的代价很严重,先是意外弄残了女孩刘田田的双腿,最终自已也摔伤致残。
理想终于坠落,成年后的范小兵,和刘田田结婚,并生下儿子范大兵。故事最后的画面是,范小兵上身直直的,推着酱油车走在巷弄里,旁边跟着儿子范大兵。
范大兵不仅腰杆直,两只手也甩得有力,迈着严整的军步,就像一个正走过阅兵台的军人。
在这里,范小兵与范大兵似乎重叠在一起,我们似乎看到了理想火炬的传递与交接。
一代人正在老去,一代人经历了失败,被现实冲撞得鼻青脸肿偃旗息鼓,但身后,依然还会有汹涌而至的人们,义无反顾地试图挣脱地心引力,发疯式地寻求兑现自己的梦,不在乎前面埋伏着的究竟是什么。
2018年,徐则臣在一次采访中说:
“我希望写出沸腾的短篇小说,哪怕它表面平静,但必须静水深流,暗潮涌动。
我希望写出压强更大的短篇小说,在它受力面积缩减的同时,力量也在增大,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能让你感到针刺般的锋锐与疼痛。”
对照这9篇小说,很多方面确实体现了他的追求,比如高度浓缩的情节处理方式,对个体存在状况的逼问,对现实与理想、历史与未来、精神与肉体的审视,都显示了他的问题意识,以及对人的强烈关怀。
在这个意义上,花街是这个世界的缩影,是过去也是未来。那些藏在影影绰绰船只间的、灰瓦门楼掩映中的花街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