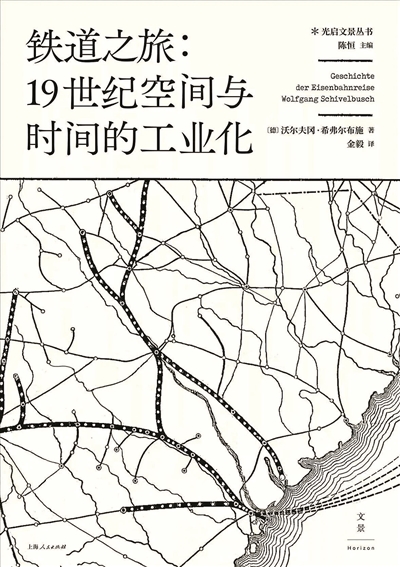主题:从铁路与火车看中国及东亚的现代性
时间:2023年4月7日晚
地点:融书房(上海浦东新区浦城路150号3楼)
嘉宾:
马啸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
金毅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助理研究员,城市研究者、铁路旅行爱好者
燕舞 资深媒体人,《社会科学论坛》编委
主办:陆家嘴读书会
铁路与火车是工业革命的产物。1780年代,瓦特改良蒸汽机并使其运转能够适应工业生产;18、19世纪之交,高压蒸汽机制成且可以用于机车,发展铁路进而成为普遍性运输方式的计划在19世纪初纷纷涌现,电报技术同期也日趋成熟;1812年,四轮轴承车厢技术获得专利;1830年代,第一辆卧铺车厢出现在美国;1850年代,铁路车厢标准尺寸确立;1880年代,铁路时间成为英格兰标准时间……
作为现代性的一种象征,铁路自清末以来一直在中国的国家统一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同治四年即1865年,英商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筑了仅供演示推广使用的小铁路。1909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正式建成……
那么,铁路这种大规模的集成机器和技术系统所表征的工业文明,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哪些时空观念的变化?人类如何在其中适应工业革命带来的新规则、新秩序?铁路与火车在150多年前又是怎样进入中国并艰难起步和发展?晚清民初的文学如何呈现这一新生事物?铁路与火车在日本的接受史和传播史又有哪些异同点?铁道在东亚国家具体是怎样塑造统一的时空、构筑统一的民族认同与爱国情感的?铁路一个半世纪以来是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又如何反过来塑造作为科层系统和经济系统的铁路?
2023年4月7日晚,“陆家嘴读书会”约请兼具铁路旅行爱好者与社科学者双重身份的优秀青年学人——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马啸、南大社会学院助理研究员金毅——对谈。
“铁道”用在欧洲
“铁路”用在美国
燕舞:两位海归才俊都是准90后的青年学人,中国的铁路事业在您二位成长的1990年代应该已经有了一定发展,能回忆一下你们青少年时期亲历的非学术研究对象的“铁路记忆”吗?
金毅:我小时候其实没有坐过火车,也没有见过火车。一直到19岁到北京上大学才第一次坐上火车。当时走到重庆站的站台上,看见这个火车是蓝色车厢的,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之前都是在电视上见的那种绿皮火车。我的家乡泸州直到2021年才通火车,当然一通就是高铁。我对火车感兴趣好像是一种弥补。从四川到北京2000多公里,可以选择不同的交通方式,后来渐渐坐火车坐得多了,慢慢地对火车越来越感兴趣。
马啸:小时候,父母会带我去铁路的道口看火车。在我的家乡宁波,上世纪90年代城市道路上汽车都不多。如果不是去坐火车,或者家里有人在铁路系统工作的话,其实很难见到火车——无论是前面的车头还是后面的车厢。所以,这个道口就提供了让我们见到火车这样一个平时不怎么能见到的庞然大物的机会。
回过头来看道口,它其实是挺戏剧化的一个场景。当时觉得能开车就很厉害了,但是这个车也必须在道口停下来。第二,道口的栏杆放下时会有“叮叮叮”的声音,它似乎在倒计时,会让你看到有一列车即将过来。这给当时娱乐活动不多的生活增加了一个很大的乐趣。
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去北京,2001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当时是坐的从宁波到包头的卧铺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燕舞:“铁道”与“铁路”两种说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听到,它们仅仅是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吗?
马啸:其实,日语中“铁路”的汉字表述是“铁道”。原来铁道部的机构名称可能是受了原来的日本铁道省的影响。看这两个词的中文表述,似乎一个更侧重表示物理上的铁轨或者说客观的存在,另外一个可能表示一种机构——它不仅代表轨道本身,还代表了运行、维护以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我们在讲到铁路跟地方的关系时,经常会用“路地关系”这样一个表述,里面这个“路”其实就是代表了制度或机构,而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铁轨。
金毅:《铁道之旅》和《铁路与中国转型》两本书里的概念表述的英文措辞本身就不一样,分别是railway和railroad。
《铁道之旅》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欧洲和美国的铁路是不太一样的,最核心的不一样在于,欧洲的铁道是在已经有大规模城市和很多交通活动的基础上,利用铁道把这些地方串起来;而到了美国,它当时是一个新创立的国家,铁路建设有在白纸上描绘图画的感觉。
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欧洲的铁路会经过已经建好的城镇、人的聚集点,会面临一个大家现在很熟悉的拆迁赔偿问题。因此,欧洲的铁路会选择尽可能少地占用土地,这样赔偿会少一些,它会去建铁路桥、建隧道;美国反而有点肆意在大平原上奔驰纵横的感觉,他们会选择很多展线,而不会选择欧洲这种处理方式。
当时学界研究的时候会做这种很微妙的区分,把“铁道”用在欧洲,把“铁路”用在美国。

铁路旅行的特质
就是旅行过程本身
燕舞:请两位简要介绍一下这次对谈涉及的“铁路”主题图书,尤其是《铁道之旅》《铁道与天皇》和《铁路与中国转型》的主要内容及其优劣短长。
金毅:我翻译的《铁道之旅》和《铁路与中国转型》,其实在框架和议题的选择上是有相似之处的。只是《铁路与中国转型》把这样的框架与议题应用到了中国这样一个语境下来讨论。它们都是比较宏观的介绍铁路历史的书,《铁道之旅》涉及很多维度——铁路是怎么出现的、铁路怎样改变人们的旅行、铁路怎样影响了当时的工业和城市的规划……它的每一章都会构成一个小的主题。
我特别愿意提到《铁道之旅》中的一个概念——“全景式旅行”。现在我们出门旅行,基本上都会在某社交媒体或者应用软件上去找一个目的地,它会跟你说这里那里有什么可看的,你是带着目的到一个目的地去旅行。去往目的地的这个过程可能对你来讲不是很重要,你反而觉得车上怎么人这么多、怎么花时间这么长、怎么车厢里有气味,等等。
其实,铁路旅行本身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质,就是旅行的过程本身,可以成为一种你自己的旅行经历,这叫“全景式旅行”——你没有办法选择及预期到你会看到什么,你就好像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然后景观在你面前缓缓移过,但是这个过程中你又会遇到很多精彩的东西。
对我自己而言,没有译《铁道之旅》之前,会觉得元宵节的晚上坐火车行走在秦岭山区,看到月亮投影到清姜河的水里,看到铁路沿线人家的门口挂着红灯笼,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经验。后来一想,这其实是我不加拣选,景观就这样突然呈现在我面前了。当我坐火车去厦门,看见朝阳洒在漳州附近九龙江的江面;或者从莫斯科坐火车回京经过西伯利亚,此前我并不知道西伯利亚是什么样子,最后在铁道上看到了贝加尔湖。
“全景式旅行”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解释力的东西,就是不加选择,你没有办法预料到你会碰到什么,但是你偶然邂逅的这些东西会触及你的某些感官。《铁道之旅》的作者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教授有点偏文化研究,他对铁路的观察是非常柔软但又敏锐的。
再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好像觉得火车站、高铁站是城市里很普通的基础设施,但沃尔夫冈教授觉得这是一个城市的入口——货流、人流从铁路进入城市,再通过这个入口流动到城市里面,火车站就成了接口一样的东西。由此,你可以去重新思考火车、铁路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它们怎样改变了城市,等等。
德国哲学家的理论、概念
日本社科学者的实证研究
马啸:《铁道之旅》和《铁路与中国转型》给我留下的一个很深印象,是两位作者用的不同材料。
沃尔夫冈教授是一位受过哲学训练的文化学者,这本书里他所用的这些材料之广泛,超出了我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所能想到的范围。比如,他会使用别人日记中的一些记录、当年报纸上的一些记录,这些文字材料的时间跨度跟地理上的跨度是非常广的,有英国、法国、美国的,也有德国的。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还阅读了很多医学类期刊,引用了《柳叶刀》上的研究——关于长期坐火车可能会对乘客的身体还有精神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大部分社会科学学者往往在一个很细分的领域做研究,熟悉一种语言、一个历史时期就很不错了。如果要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边界,对于这种广泛材料的使用是非常难的。
柯丽莎教授这本《铁路与中国转型》中也用到了非常多的研究成果。我特别羡慕的一点是,她除了使用惯用的历史学科的档案研究成果之外,还很难得地进行了一些实地研究——2005年左右她在中国一些城市进行了实地访谈,比如,涉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铁路制度的一些变迁,可能官方档案之中的正式记录相对较少,但比较幸运的是,2000年代初她来中国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很多亲历者,像解放军下辖的铁道兵们仍在世,她对他们进行了很多口述史访谈。
像金毅老师他们这个学科的社会学学者利用口述访谈比较多,但柯丽莎教授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能够综合运用那么多材料,我特别佩服。作为一个在美国的学者,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她用上了所能遇到的几乎所有材料,从而给我们展现了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铁路发展的历程。
《铁道与天皇》的作者原武史,更像是一个研究大阪的专家,这本书的日语原书名,强调的是作为市民的大阪和作为帝都的东京之间的一个差异与竞争。他写书的初衷是想从铁路的视角,来看大阪这个城市跟传统认知上由政府或者官僚主导的日本政治中心东京有什么样的区别。它的切入点是大阪几条非常知名的私铁。
日本对铁路有不同的分类,大家经常听说的新干线,是属于Japan Railway,是日本的国铁。还有很多由企业投资运营的铁路,即所谓私铁。这些铁路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世纪。《铁道与天皇》的一个重点,是追溯了其中一条“阪急铁路”的历史。它最早叫“箕面有马电气轨道”,再后来叫“阪神急行电铁”。
可能这是日本社会科学学者做研究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作者特别注重事实的记述。作者后记中也说他自己是一个“铁道宅”,他可能不太在乎那些社会科学的理论。而沃尔夫冈是一个在德国受训练的哲学家,他是另外一个“极端”,他特别注重理论和概念。比如,《铁道与天皇》和《铁道之旅》两书中都提到了为什么火车站特别适合建设百货公司,原武史就直接讲述阪急百货哪一年规划、哪一年建成、吸引了多少客流,沃尔夫冈则会说百货不同于零售业,它更追求量而不是利润的边际,所以火车站作为汇集人流的地方具有优势等。由此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德国的社会学者跟一位日本的都市研究学者,哪怕都是研究同一个命题,仍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视角。
国人对于铁路在内的现代技术的接受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开放、更包容
燕舞:文学文化史研究的前辈学者陈建华先生在《文以载车》中提及,“晚清文学里轮船称霸”“晚清李伯元、吴趼人等人的小说里,最常见的是船”“火车发明之后半个世纪才来到中国,在华传教士或清朝旅外官员做了大量宣传,已视火车为恩物”,而著名科技哲学专家刘大椿教授在《晚清铁路认知史论》的推荐序中指出,“即使在19世纪的欧美,铁路也是现代性生动而引人注目的标志”。那么,铁路在19世界60年代进入中国时,它真实的冲击和影响到底是怎样的?与在日本的最初接受情形有何异同?与在工业革命的故乡英国的接受情形比起来呢?
金毅:柯丽莎教授在《铁路与中国转型》里提了一个蛮有意思的观点,她认为中国并没有一种很强的“卢德主义”——即破坏机器的倾向——发生在火车上。
我们知道的情形可能不太一样。我总会讲两件事,第一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非常害怕火车,听说洋人要在北京城向她展示火车,她觉得这个东西不吉利,就让太监拉着这个机车在轨道上跑一跑,让她感受一下坐火车的感觉。这似乎说明慈禧对铁路技术是有敌视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上海的吴淞铁路算是中国比较早的一条铁路,建起来就被拆掉了,好像有各方面觉得它不吉利或者说有其他一些因素的考虑。这两个例子似乎说明,我们早期对铁路与火车似乎是不接受的。
一方面,确实有这种情形。柯丽莎教授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跟马啸老师讲的地方怎样去争取高铁过境是正好反过来的——孔子的后代当年如何不让铁路经过他们的故乡。1904年,从天津到南京浦口的津浦铁路(即后来的京沪铁路)勘测线路时,原计划是要经过山东曲阜的,离孔林很近。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代表家族联络一批大员,上述光绪帝陈诉修路会“震动圣墓,破坏圣脉”。在他们看来,孔家封地会因铁路的穿越而损失不少,折合成地租是很大一笔钱。最后,津浦铁路真的就让了这么一个大步。现在的京沪铁路也是不经过曲阜的,而是经过旁边一个有点距离的城市兖州。这类例子确实存在,而且涉及当时的上层精英,他们出现在我们各种记录、描写当中的概率会更高一些,更容易让我们去关注到这类事情,让我们觉得他们对铁路与火车的发展好像是一种敌对态度。
但是,铁路在中国的铺展是很广的。一方面,建国之前铁路虽然会影响一些区域,但是它的实质性影响是很有限的,大部分民众对此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态度的。铁路真正影响到的区域,比如涉及工厂、矿山等这些地方,那里的从业者对开始采用铁路的技术是持欢迎态度的。所以说,一方面是慈禧在北京害怕铁路,但在1200公里之外,张之洞在汉阳铁厂就把铁轨造出来了。我想,当时炼铁的原料运输也会用到铁路。
一个跟我家乡四川有关的事件是1911年的“保路运动”。慈禧当时刚刚去世也没几年,社会精英已经对要争取国家路权有很强的认识。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孙中山很快在建国方略里面大量地进行铁路规划,也是意识到了铁路的重要性。其实,国人对于铁路在内的这种现代技术的接受,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开放、更包容。
其实中国人对于铁路的纳入
还是持相当实用主义的态度
马啸:在铁路刚刚进入中国的前几年,确实发生了若干起敌视铁路的事件,但这个敌意背后其实有很强的当时的政治背景。一个例子是前面金毅老师提到的吴淞铁路被拆除。另外一个就是把铁路与西方侵略者关联起来,认为铁路是代表西方力量在中国的呈现,所以当时有一些破坏铁路和火车的行为。
诚如柯丽莎教授在书中所说,其实中国人对于铁路的纳入还是持一种相当实用主义的态度。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记得柯教授说在1895年,当时英国已经有23000公里的铁路,而中国只有500公里铁路,所以,在整个19世纪,哪怕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铁路在中国仅仅限于环渤海地区以及现在的长三角地区,还有东部一些很少的区域。刚才金毅老师也提到,晚清中国第一条具有跨省意义的长距离铁路——津浦铁路的建设,给沿线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燕舞:电报技术在19世纪初期也日趋成熟,它作为新生事物对铁路的传入有什么影响?
马啸:沃尔夫冈这本《铁道之旅》里引用了韦伯的一句话——“如果把铁路比作一个人身体中的肌肉,电报就像是他的神经”。早期的铁路并不是被一个单独的机构独占,不同机构都可以在上面运行火车,这样显而易见会造成很多安全问题。到后来才变成一个统一的机构独占,运行列车和经营铁轨的才变成同一家。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错误的想法,火车司机被认为是“旱地船长”——在很长一段人类历史中,在现代雷达或其他探测仪器出现之前,船长的航行经验是特别重要的,比如他可以通过观察星象、天气之类来判断自己的方位从而来应对非常复杂的海况。但火车司机并不是船长这样一种传统职业,像前后车站的火车调度或者避让等难题,并不只是靠经验就能解决的,它需要非常精确的信息。在电报没有出现之前,仅仅依靠人的经验,是很难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的。
柯教授的《铁道之旅》里提到过,中国铁路系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摒弃专业主义和要求人们回归经验主义的很短暂的一段历史,那段时间中国火车的事故率出现了上升。专业信息对铁路的安全运行十分关键,火车司机不是传统的船长,他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执行者,电报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金毅:大家现在坐火车时往外看一看,会看到一个接触网。因为我们的铁路基本上都是电力铁路,沿线要用输电线。如果你要坐火车进行“全景式旅行”,你的画面里头总是会有一根线——其实是电线。这个现象并不是新的。内燃机机车年代,沿线线路不是电线,是电报线,就是传送信息的。从铁路诞生,它就和电报系统是密不可分的。几年前翻译《铁道之旅》写译后记时,我就想起英剧《唐顿庄园》的开篇,里面讲贝茨先生坐火车去唐顿庄园,看到火车的蒸汽喷出去,旁边就是电报线。电报传送信息到唐顿庄园,称“泰坦尼克号沉了”。全球就这样联系在一起了。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