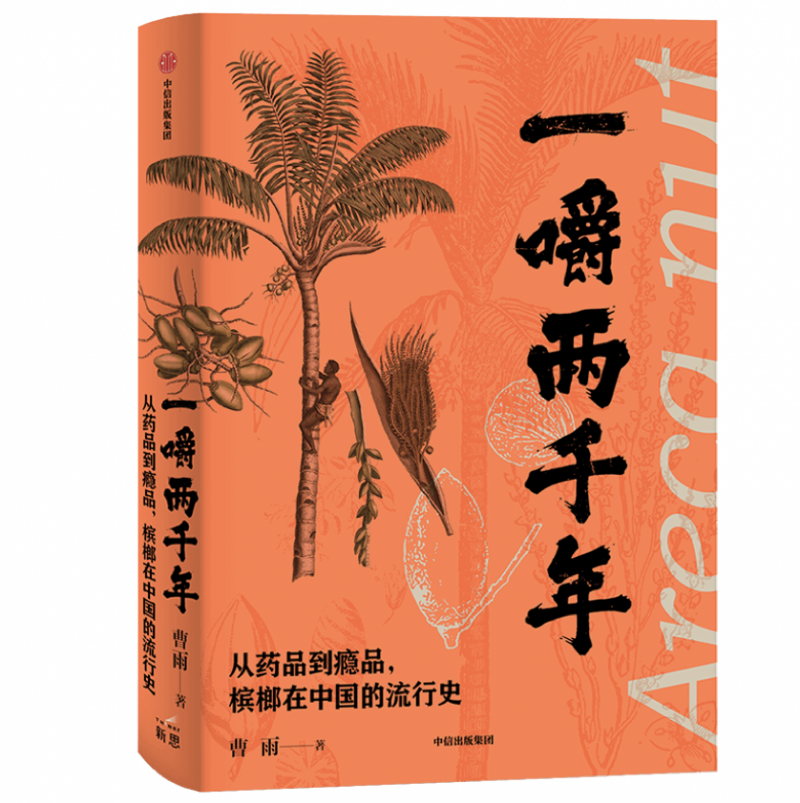槟榔在其流行区域里的各种文化中,都有一致的男女情爱指向。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南岛文化中,在僧伽罗、泰米尔、印地等印度文化中,在越南、缅甸、泰国等中南半岛文化中,槟榔都是重要的男女定情物和结婚必备礼物。槟榔在中国文化中的定情物地位也并无不同,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详细介绍了槟榔在岭南婚俗中的重要地位。中文最早关于婚俗中使用槟榔的记录则见于三国东吴万震记载的“婚族好客,辄先逞此物;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 ”。
南唐后主李煜早在《一斛珠· 晓妆初过》中就将槟榔作为情欲的象征物:
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这阕词写的是李煜与大周后之间的情爱之事,烂嚼红茸一段,把嚼槟榔的女子妩媚风骚的身姿神态描绘得活色生香,可谓是艳绝无双的文字。
关于槟榔在古印度文化中的定情物象征,我们可以从《善见律毗婆沙》中的一段记载一窥究竟:
折林者,男子与女结誓,或以香华槟榔,更相往还饷致言:“以此结亲。”何以故?香华槟榔者,皆从林出,故名折林。若女人答:“饷善,大德饷极香美,我今答后饷,令此大德念我。”比丘闻此已,欲起精出不犯。若因便故出犯罪,又因不出得偷兰遮罪。
《善见律毗婆沙》是从斯里兰卡传来中国的佛教早期律藏经典。此经翻译于南齐永明六年(公元 488 年),原经是巴利文本,成书不晚于公元前 250 年。由此可知古印度男女定情普遍用香花和槟榔二物。这里说的律法是关于僧人欲念及泄精的解释,因为香花、槟榔有定情的喻义,若僧人与女子互相赠送此二物,女子又将这些礼物视作定情物,僧人得知该情况的当下如果马上终止行为,那么即使泄精都不算犯罪;如果僧人知情后仍继续调情,那么即使不泄精也算犯了偷兰遮罪,如果泄精则算犯了最重的波罗夷罪。
佛经中这段记载恰与《红楼梦》中贾琏与尤二姐勾搭的一段文字互成注解:
贾琏又不敢造次动手动脚,因见二姐手中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了带了来,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贾琏便笑着欲近身来拿。二姐怕人看见不雅,便连忙一笑,撂了过来。贾琏接在手中,都倒了出来,拣了半块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又将剩下的都揣了起来。
这里贾琏向尤二姐索要槟榔,很明显是要与尤二姐亲近的意思。尤二姐的回答也是半推半就,她知道槟榔有着定情物的意味,也有心与贾琏勾搭,但又怕贾琏心意不坚定,故而说了句“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 ”,最终还是丢给了贾琏。贾琏得了尤二姐的槟榔,如同得了允可上身的纶音,自然是心花怒放,挑了半块吃剩的槟榔,调情意味更加露骨了。
在这两处文本中,槟榔作为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槟榔何以在诸多文化中具有一致的男女情爱喻义?这种喻义是南岛语族自嚼食槟榔习俗源起时便有的,还是由于槟榔本身有使人发热、解除神经抑制的功效,从而被诸多文化一致赋予的呢?
一件具体的物,若要在文化中产生喻义的映射,一开始通常依赖它本身的物理性质。比如说辣椒和姜,本身具有辣的刺激属性,因此被赋予了果断、勇敢的人格化喻义,再从这个喻义出发,延伸到政治文化的层面,则有了革命、反叛的喻义。槟榔的喻义也是从它本身的物理性质出发的。由于它能够使人发热、兴奋、解除神经抑制,故而对人有了催情的作用,进一步地延伸到文化的层面,便是定情物,便是婚礼中必备的交换礼品,而槟榔的偷情意味也是从定情物延伸而来的。
嚼食槟榔的习俗起源于南岛语族,后来习得这种习俗的古印度人、古中南半岛人和古代中国人,都是通过与南岛语族的接触而获得槟榔的,而他们赋予槟榔的喻义又出奇地一致,因此很有可能南岛语族早已发展出了一整套关乎槟榔的礼俗体系,后来得到槟榔的民族,不但获得了这种物本身,还习得了一整套关于槟榔的喻义系统。此外,古代中国、印度、中南半岛诸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还在不断地印证和强化这套关于槟榔的喻义系统,使得这套系统更加固化和强势。比如说前文那段佛经中关于槟榔定情的描述,其影响力便能够广达整个佛教文化圈,从而进一步强化槟榔的文化形象。再比如由中国文化自发阐释出的“槟榔无柯”,象征忠贞不贰,这种喻义是其他流行嚼食槟榔的地方所没有的,进一步地强化了槟榔在婚俗中的地位。
前文还提到了《儒林外史》中一段关于槟榔的文字,即汤六爷在逛妓院时大嚼槟榔。从这几处可知,槟榔在岭南以北的地方往往有一种偷情的意味,与岭南地区的槟榔喻义有细微的差别。槟榔在岭南的婚俗中有正式的地位,常被用作定情和订婚的礼物。因此在岭南文化中,槟榔往往伴随着光明正大的男女情爱和婚配之事,并没有偷情的喻义。这种细微的差别,也显示出槟榔的喻义在中国发生的流变。槟榔在岭南以北地区并不是平民可以日常消费的物品,进而导致了槟榔在社会礼俗中的“正式”地位有所下降,也就是说,槟榔作为一种稀罕的物事,被用作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确定,出发于槟榔与情爱的关联,又超越了正式礼俗的边界。
槟榔在岭南婚俗中的“正式”地位体现在它的四次出场:第一次出场是在提亲的时候,男方家将槟榔及其他聘礼送往女方家,俗名“过礼”(岭南)或“ 下定”(江南),正式的名称是纳征;第二次出场是在婚礼上,“凡宾客至,无论长幼,新妇必起立奉槟榔”,这是新妇迎宾的礼节;第三次出场是在婚后一二日内(圆房后),女方家人要将一担槟榔送至男方家,名曰“担槟榔”;第四次出场是在新妇第一次归宁的时候,通常在婚后数日内,夫家要准备一担槟榔与新妇一同回娘家酬谢,名曰“酬槟榔”。在东莞,第三次和第四次互赠槟榔时,娘家亲戚和新妇要唱槟榔歌。婚俗中槟榔的四次出场都是以多为好,越多越能体现两家的财富和地位。岭南婚俗中使用槟榔可以上溯到三国时期,下至民国初年,盛行了约1 700 年。
在当代越南人的婚礼中,槟榔仍然是必备的礼物,与容媛所记录的民国初年岭南婚俗几乎完全一致。不过在越南婚礼中,槟榔会出场六次,比岭南婚俗中槟榔出现的频次还要高。第一次是定亲的时候,夫家须赠一对耳环、一盘槟榔、一对白蜡烛;第二次是“请期”的时候,须带一串槟榔;第三次是“祭红绳礼”,即祭祀女方祖宗的时候,香案上须摆放槟榔;第四次是婚礼时,证婚人须手捧槟榔,伴郎头顶一盘槟榔;第五次是合卺礼时,新郎须将槟榔一分为二,与新妇各食一半;第六次是回门的时候,新婚夫妇到女方家拜认亲属时,须携槟榔赠人。在岭南和越南的婚礼中,槟榔都是相当正式的必备礼物,是礼节所必须,也是庄重的。
我们将槟榔在中国南北文化中的这种细微差别,放在文化人类学的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可以得知某种“关联物”在文化中的地位会根据它的普遍性和可得性而发生变化。当一件“关联物”普遍而易得的时候,它往往能够用于建立较为正式的、常态的社会关系;而当一件“关联物”供应不太稳定的时候,它便会被用于建立一种非正式的、隐秘的社会关系。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中大费笔墨描绘的“库拉圈”交换体系:一般性的两种“关联物” —红色贝壳项圈(soulava)和白色贝壳臂镯(mwali)—通常在集体参与的仪式中进行流转,而具有特殊意义的宝物(vaygu’a)则只在特定的小圈子里流转,有时候还充当给妖怪和神灵的祭物。由此可见在“库拉圈”交换体系中,常见的贝壳礼物具有相当稳定和正式的社会礼俗意义,而比较罕见的珍稀礼物的社会礼俗意义则不太稳定,往往根据具体的场景而发生变化。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