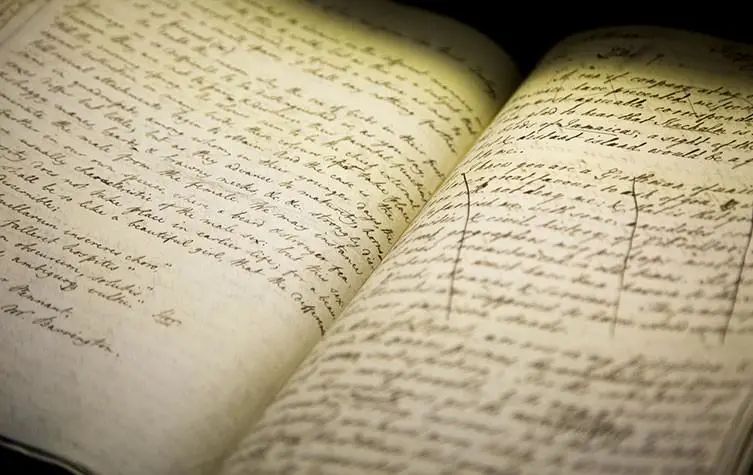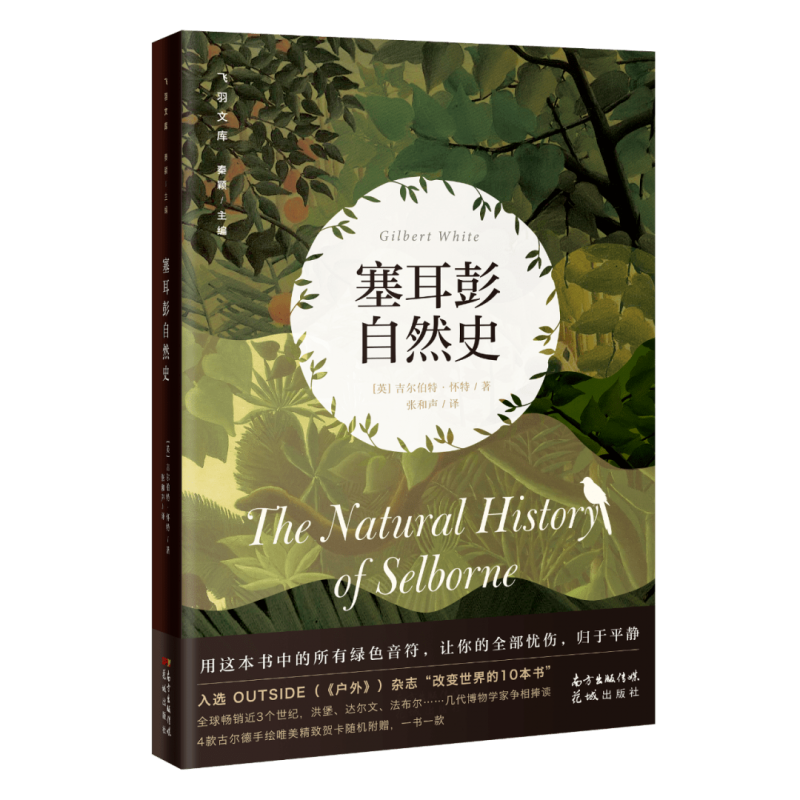几个世纪以来,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成为了经典,究其原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书中出现的塞耳彭代表着一种观念和思潮,它是一个象征或者一个符号。它是一个人对那种久远年代人与自然关系的领悟与思考,这种思考和领悟能激起人对地球及其蓬勃活力的无限热爱和向往。
今天的文章,带来作家李青松对于这部经典的解读。在他看来,在地图上,塞耳彭仅仅是一个村庄,但对于生态文学来说,它是一个起点,一个举步迈向世界的开始。
《塞耳彭自然史》手稿
这个夏天,我是在一个叫塞耳彭的村庄度过的。在那里,我结识了一个手拎灰色手杖,穿着齐膝短裤,经常出没于山谷和森林中的人。
酷暑中,我手捧着他的书,不禁感慨万端了。那本书的名字叫《塞耳彭自然史》,它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异域,那个安然地在不知邪恶的荫蔽之处蜷曲着的,远离城市和物质喧嚣的村庄。我仿佛置身其中的某个农舍里,正在静静地消磨慵懒的时光。
山丘、教堂、牧场、牛羊、荒野、草垛、小径、溪流、麦田,还有鸟鸣——这些乡村的事物都是塞耳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熟悉了那里的白嘴鸦和野鸽子在橡树林的飞舞和歌唱;熟悉了那头十七岁的母猪老迈的体态和浪漫的爱情故事;熟悉了那里的蚯蚓为农作物的丰产,而辛劳地在土壤上钻孔、打洞和松土,劳作不歇;熟悉了那里的猫头鹰叫声所具有的表现力,什么情况下会发出呼呼声,什么情况下会发出嘘嘘声,叫声别致,宛若人声。
《塞耳彭自然史》,花城出版社2021年3月版
当然了,我对塞耳彭的地形,也是了然于胸的——就说山吧——有诺尔山、巴尼特山、巴斯特山和波茨岗山。正是由于这些山的存在,使得塞耳彭免受了每年夏天暴风雨的侵扰。因为暴风雨到达这里之前,就会因山的阻隔,而转向东边或者西边。有时候,也会被劈成两半,一半去了东边一半去了西边。这里的云朵躁动不安,总是想法太多,但是那些云朵一触动树梢和山尖,腹部就会被刺破,突地一下就瘪了。晴空万里,不见了踪影。
塞耳彭有人口670人。
村庄掩映在森林遮蔽的山谷中。村庄东西走向,只有一条街道,弯弯曲曲,长不到一英里,阔不过十步。村庄有两条小河流经,西端那条经常干涸,而东端那条却汩汩涌流,四时不竭。村口有一口水井,深63英尺。井里的水清冽而甘甜。不过,我从来没喝过。
村庄里的人多数都是农人。男人除了种田,还会伐木、剥树皮和打理啤酒花。女人呢,不但纺线织布,也下地除草,到九月份就去摘啤酒花了。此时,村庄的上空整日弥漫着花香,令人心醉。
这个叫塞耳彭的村庄里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我结识的那位朋友——怀特了。他是一个谦逊而安静的人,他是一个寡欲而少言的人。他于1720年出生,1793年去世。73岁,终生未娶。去世时的那座房子,就是他出生时的那座房子。那座房子是用石头砌成的,青石红瓦。共两层,窗户装了玻璃,卧室在上面那层。书架上摆放着许多书。有的书页里夹着蝴蝶或者树叶。
怀特的父亲是律师,祖父是牧师。他毕业于牛津大学,毕业后回到塞耳彭,一边做教堂执事,一边对当地的植物和动物进行考察研究。后来,他做了教堂副牧师。据说,当时没有牧师,他实际上是主持教堂日常工作。可是,在他的书中对教堂里的事情只字未提。
1789年,《塞耳彭自然史》出版,开始没太有什么影响,后来居然成了读者最喜欢的英文书。到目前,已经印刷了一百多版。有可靠证据显示,它是英语世界重印频率排名第四的图书。《塞耳彭自然史》是一本书信集,一共66篇,记述了塞耳彭的动物、植物、物产、自然现象以及古迹和风俗。笔调简洁明快,语言清新灵动。
那些信是写给他的两个朋友的——一位是动物学家彭南特,另一位是律师巴林顿。这两位朋友都比怀特的年岁小,但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独特的建树。《不列颠动物志》就是彭南特所着,而巴林顿在古文物和博物学研究方面,也是赫赫有名。
可是,有一点我始终存有疑问——怀特的信,除了少数几封外,很少看到就某一问题他与那两位朋友展开讨论,也很少看到那两位朋友具体回信时都说了什么。给人感觉,当时,怀特给朋友写信的热情,远远高于朋友回信的热情。不过,怀特在信中很少披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更不涉及政治和宗教。怎么能不涉及呢?——也许,这就是怀特的原则。对此,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
怀特除了在大学读书和在牛津工作的一段时间之外,几乎一生都在塞耳彭生活,他注意力突出地集中在这块窄小的天地,集中在教区的自然和田野。
《塞耳彭自然史》中,候鸟和留鸟是主角。渡鸦、戴胜、燕子、柳莺、野鸭、鹌鹑、啄木鸟、大山雀、金丝雀、长脚秧鸡等反反复复地出现。他能辨别一些鸟的叫声,能根据踪迹和气味判断田鼠是否在洞穴里,对青蛙、猫头鹰、乌龟都有独特的研究。怀特最早发现,蚯蚓是鸟类的食物。蚯蚓通过松土,这种慢腾腾的虫子还能帮助农民为田地通气和施肥——他说,这是一个自然的卓越安排,也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智慧。
在怀特眼里,塞耳彭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着统一的生态整体。他始终注意塞耳彭有多少种生物,习性如何,并了解它们是怎样联系并在怎样的自然状态中生活的。怀特认为,自然的产物,如果不是全部,也是部分为了给人类提供一种良好而有益的环境而存在的。“造物主对我们如此慷慨”——他在作品中,以燕子为例写道:“它们是一种最不令人讨厌的鸟类。它们不触动我们果园的果实,燕子依附在我们的房舍屋檐下,用它们的季节性迁徙、唧唧声以及它们的机智,令我们惊喜,而且还清除我们由蚊虫和其他让人讨厌的昆虫所带来的烦恼。”
由于时代的局限,还很难说当时的怀特就已经有了自觉的生态意识。在怀特的作品中,他坚持认为,对自然的考察和研究应致力于更重要的目的,使野生动物和植物有可能为人类生活提供最大程度的舒适和精致。怀特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忽略了植物。他说,植物对人类至关重要——有了植物,我们才能有木材、面包、啤酒、蜂蜜、油、亚麻和棉花等。植物不仅强健我们的身心,振奋我们的精神,还能使我们免受严酷天气的困扰,让我们有所可居,有衣可穿。他在塞耳彭的荒野漫步时,每每留心有研究价值的植物。有时,也采撷一些,或者做成标本,或者记录在案,日后深入研究。
几个世纪以来,《塞耳彭自然史》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书中出现的塞耳彭代表着一种观念和思潮,它是一个象征或者一个符号。它是一个人对那种久远年代人与自然关系的领悟与思考,这种思考和领悟能激起人对地球及其蓬勃活力的无限热爱和向往。字里行间表达的是,怀特急于把整个自然与塞耳彭教区融为一体的心情,也表达了他想通过外部调节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渴望。
塞耳彭的自然,非常接近于完整的状态——那是一幅丰饶、稳定和具有温暖情感的风景画。没有罪恶、恐怖和焦虑,城市的喧嚣、压力和困惑被置于遥远的地方,跟这里无关。它是一个自然且自在的世界,人一直使自己适应它。而不是反之。
达尔文朝拜过这里,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巴勒斯也专门来塞耳彭访问过——“这里具有家的氛围”“就像火炉边的角落一样舒适而宁静”。
就是在《塞耳彭自然史》出版的那一年,法国巴士底狱监狱被巴黎的革命者占领,华盛顿就任美利坚合众国首任总统,人类政治发生了一系列变革。然而,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似乎对塞耳彭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塞耳彭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一系列独立部分的组合。塞耳彭遵循着自己的法则和逻辑,拒绝一切与美无关的事物。
可是,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工业革命开始了——这种技术革命背后的推动力,当然是人的直接生产和财富的欲望。“让两片草叶长在之前长着一片草叶的地方。”技术革命从不列颠传播到美国,甚至更远的地方。当然,离伦敦不足一百英里的塞耳彭不可能幸免——怀特的那种对自然的永恒和稳定的田园牧歌式的认识,将永远不复存在了——作为诗和远方的塞耳彭也不会有了。工业化进程及其技术革命,造成了自然和乡村生活的各种不适。技术为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怀特告诫我们,技术如果忽视了自然的复杂性和整体性,那是很危险的。自然的整体性质不同于它的各个部分的总和。用实验室里的方程式和模型来研究自然是错误的,自然是不可挪动,不可腾移的。
怀特的观点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同时也带有深沉的怀旧的情感。它唤醒了人们心底某种沉睡已久的东西,让我们意识到了,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人也归属其中。这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塞耳彭自然史》成为了英美生态文学的经典范本。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大概就是始于怀特吧。自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与人体不无相似之处。在生态文学看来,每一个自然的组成物,每一种植物或者动物——都只能是被看做参与并依赖于这个整体。
这里,强调内在的联系和依赖性,而且它还描述了一个美妙的道德憧憬,远不仅仅是生态文学的主张了。在生态文学看来,它往往还包含着对个体的否定,而强调生命共同体意识,强调协作和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一种思想的产生绝对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定的文化氛围。《塞耳彭自然史》产生在英国这样一个有些另类的乡村自然有它的道理。
就英美国家而言,十八世纪以来,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自然观,一种以生命为中心,一种以人类为中心。从实质看,两者的分歧在于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这两种观点体现在自然伦理中,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标准也是不同的。以生命为中心的自然观主张,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观主张,自然是供人类索取和利用的资源。
怀特所持的是哪种自然观呢?我想,无论是谁,只要读过《塞耳彭自然史》就不会认为这还是问题吧——我们要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地球,而对技术要持怀疑态度。是的,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没有比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更重要了,没有什么事情比改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更能影响人类的幸福了。
当初,也许连怀特本人也没有意识到,几百年后的今天,他被推到了英美首个生态文学作家的位置。他创造了一种文体——自然随笔。尽管那是书信体的自然随笔。此后,艾默生、梭罗、缪尔、巴勒斯、奥尔森、贝斯顿、利奥波德,乃至卡尔逊的文字里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怀特的痕迹或影子。生态文学有很多定义,我们必须进行认真审慎选择。生态文学似乎成为了一种创作运动,饱受争议,遭受指责,在理论上被各种观点摇撼,甚至蹂躏。这不是什么坏事,这说明在这个时代不能无视生态文学的影响力了——可能,这也意味着时间开始了——我们到了靠生态文学引领文学走出纷乱喧嚣困境的时候了。
在此,我们应该向怀特致敬!
在地图上,塞耳彭仅仅是一个村庄。它是怀特的塞耳彭。但是,对于生态文学来说,它是一个起点,一个举步迈向世界的开始。
李青松/文
刊于2021年8月26日文学报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