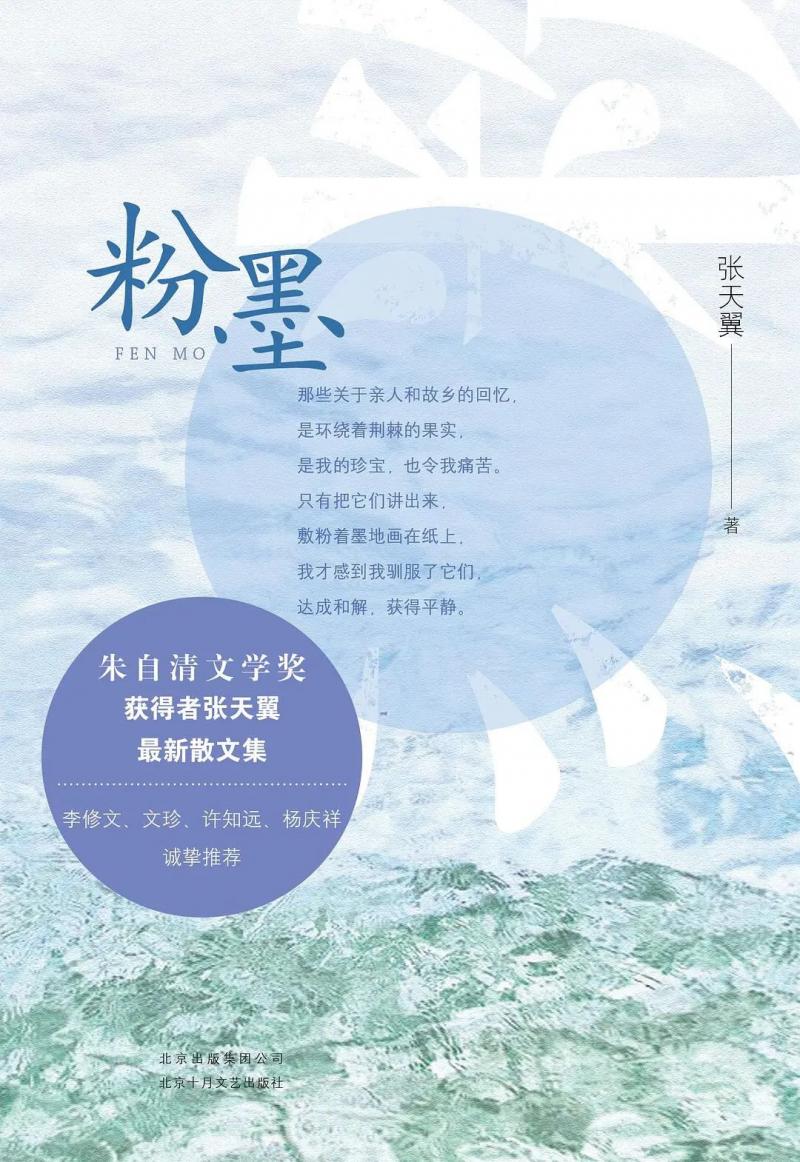01
透明
在朋友家读到一册绘本,这样写:爷爷越来越透明了,他把东西藏起来让我们找,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到就藏在他背后。后来他就彻底成了透明人。人们以为爷爷死了,不过有时空中会传来爷爷说话的声音,大家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姥姥死的时候,当透明人当了快十年了。
小时读到李密《陈情表》,“母孙二人,更相为命……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想,他的奶奶活了九十六岁,真是高寿,大概是舍不得孙子吧,所以总挣扎活着。人到了九十六岁,该老成什么样呢?我的姥姥能不能活到九十六呢?
后来姥姥也在高寿这条路上蹒跚前行。八十了,八十五了,九十了,九十五了。每回过生日时大家都说,您老人家肯定能活过一百岁。百岁人瑞,政府会给发钱,为这个您也得努力。
她笑嘻嘻的,好,好,我就没皮没脸地活着,活到一百岁,真成老妖精了。又自言自语,一辈子没拿过工资,活出岁数来,政府还会给钱啊?
她死的这年九十六岁。
到底没熬到拿政府的“工资”。
寿则多辱,此言源于《庄子》,“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周作人晚年把这四字刻做一枚闲章,无限沉痛。巴金说:“长寿是一种惩罚。”活得越短,越没机会露出纰漏、丑态、昏聩。
衰老像夜晚一样徐徐降临,光并不是一下子就散尽,死神有惊人的耐心,有时他喜欢一钱一钱地凌迟。壮年时的余晖犹在,八十岁时,姥姥的食量仍是阖家之最。她独个儿住在老房子里,自己伺候一个蜂窝煤炉子,自己买菜做饭,虽是踮一对小脚,行如风摆杨柳,但还利索得很。她对大家都很有用,儿女们的孩子尚小,都得靠姥姥帮忙看管。六个外孙、孙女、外孙女,都经她的手抚养。于是她是有实质的,有威信,说话一句算一句,小辈们都不敢不认真听,稍有点嬉皮笑脸,姥姥脸色一沉,扬起一只大手,“打你!”喉咙里冒出不大不小的一个霹雳,威风凛凛。不听话者难免心头一凛,收敛起嬉皮笑脸,承认错误。
后来她越来越老了,城池一座一座失守,守军一舍一舍败退,退至膏肓之中。她不能再为家人提供利益,只能彻底地索取,因此她逐渐透明下去,世界渐渐看不见她了。她的威严熄灭了,儿女上门的脚踪逐渐稀了,孙儿辈异口同声地说工作忙,好像都在同一家公司,一年来两三趟,其余时间就算开车路过也不进门。春节团聚的时候,敷衍地拎一箱牛奶,进来叫一声姥姥或奶奶,这就算交差。她记忆漫漶得很了,一个孙女站在眼前,她要把所有孙女名字都叫一遍,才牵带得出正确的那个,像贾母一连声地喊“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宝钗黛玉湘云……”
然而她也不生病,生病的老太太倒会有众人环伺探望的排场。她只是没尽头似的老下去,用不存在的方式,又存在了十年。
除了行动能力,在最后十年中,她也渐渐失掉正常交流谈话的智力。与人说话,一句起,一句应,一句止,她就很满足了,慢慢点着头,像回味这次对话似的,眼睛若有所思地转向别处。
有时,她想主动与人沟通,就拿手去碰触身边的人,叫着,嗳,嗳。脸色有点巴结地笑,郑重地问出一个问题,如:我有点不记得,想了半天了一一你今年多大?
这当然是可笑的。被问的人和旁边的人对此都有默契的认识,他们面面相觑,嬉笑着,拿不认真的嗓音说,您看我多大了?
她仍是认真的,我想你是十九,还是二十?
被问的人呵呵大笑,姥姥,我都三十五啦。
然后人们继续管自说话,不再看她。他母亲说,在你姥姥眼里你年年二十。他则说:我倒希望我女朋友也这么看我,哈哈哈······
剩她独个儿咂摸那一点愕然,并陷入喃喃慨叹,哎呀,我外孙三十五了?当初我带你的时候,你整天哭,搁不下,只能一只手抱你,一只手捅炉子炒菜······
人们都同意:跟她说话只要敷衍过去即可,谁让她活到这样老,老得跟世界文不对题。这世界必须被井井有条地划分,分奥运会和残奥会,分治活人的医院和敬老院。
衰老是谁都要经受的最后一项残疾,除非你幸运地蒙召早退,逃出这环链条。
但她偶尔能记住一些事。几年前我有了男友,带回家,告诉她此人名字叫“楷”,小名叫“大楷”。这样见了几回,她居然记住这个人了,却把名字错记成“大海”。
于是每次见我回去,先很惊喜地问,咦,你回来啦?
然后问,大海呢?
我多高兴她能记住他,但仍要纠正,不是大海,是大楷。她也像发现一件新鲜事,恍然大悟地哦一声,原来是大楷不是大海啊。下一句就启用新名字,大楷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我答说,他放寒假回他们家去了,说下次再来看你。
过一阵,我到厨房去跟母亲说了话,或是去拿了本书再回来。她一见我,叫着我的小名,又很惊喜地说,咦,你回来啦?
接下来再问,大海呢?
我再答,他放寒假回他们家去了,说下次再来看你。
有时小薛陪我一起回家,进门来先坐到姥姥身边,笑呵呵地,很响亮地叫:姥姥!她也很凑趣很响亮地回答:嗳!大海,你来啦。并立即伸手拽住他的手。
我免不了在旁说,是大楷。
小薛反倒转头冲我说,姥姥要叫大海就叫,你不要纠正她。
旁人就一阵笑,说,对,对,大海也很好听,你姥姥本来是海边的人,叫大海才亲切。
后面这些,她可就没听了,只顾看着小薛微笑,将他的手放在手心里,另一只手来回摸他的手背。见大家笑着议论,也抬头咧嘴看看,懵懂地笑,说:啊?
后来她的听力不太好了,人间把她又推远了一步。
有时她会陷入沉思状态,陷得很深。盘腿坐着,小脚放在腿弯折叠处,手撑着额角,眼睛盯着墙,浑浊的眼珠停滞了,犹如哲学家整理胸中哲思。
大家围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以这个行动表示孝敬。所有人当着她的面议论她,毫不避讳,也不用压低声音,就像她只是一座标本。
她大女儿抽着烟说,其实咱妈是个很自私的人,她心里只有她自己。她外孙说,咱姥姥攒钱攒一辈子,也不知道攒了多少。
连母亲也不例外,虽然口吻和主题大多是爱怜:瞧你们姥姥,嘴唇还是红彤彤的,头发也没怎么黑,这个岁数的老太太,哪个有这么漂亮。
连我,我也不例外,我也参与这种不动声色的残忍,我问起家里一件禁忌,姥姥最近没提起大舅吧?她是不是心里早就明白······
大舅,她的长子,五年前死于心脏病。谁也没告诉她。她偶尔问起,口径一致:上外地工作去了。
她就再不提了,不问六十多岁的人还做什么工作。她那年代的女人都这样,不言不语地接受一切遭际和安排,不追究,不盘问。但大舅死后三年她说了一句,打电话让他来瞧瞧我吧,我想他。
自那次请求没有如愿,她再也不说“让他来”。
过年的时候,亲戚们提着点心盒子当具,来访查证一下,哦,老太太还真硬朗,不简单,真不简单。也就走了。
能看得到她的只剩母亲,因要赡养她。查探她的变化,亦步亦趋地跟随她衰老的步伐调整食物饮水,摸索实时变更的身体规律,每一夜,每隔一小时起床服侍她小便。
生命和岁月交给的能力,她按原本的顺序一样一样还回去。五年前,很难出门了,用轮椅推到外面花园里,还能搀着别人的手走两步,走到池子边看人用馒头喂金鱼。后来不再出屋,不过还能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再后来彻底不能行走,但还勉强能站立。再后来站起来也不能了,三年里整日只倚枕坐着,由母亲把她抱到马桶上。她的食量逐渐减少,食谱逐渐缩短,需要多费牙齿之力与肠胃之力的美味一项一项与她道别。本来她还能喝几口黄酒,后来终至一喝酒就腹泻。
筛子眼越来越细,兴致、乐趣都被筛出去了,日子惟余越来越纯粹的萧索。
最后半年,她吃得像个初生婴儿,粥,牛奶,一点点肉糜。
到临终两个月,粥和牛奶亦被肠胃拒绝了,只剩了饮水,蜂蜜调制的水,糖水。再让她喝两口牛奶,下午就泻一床。她常跟母亲说,想吃肉,想吃虾。母亲铺张出一大桌,她还是摇摇头不吃了。仅余的生命力负隅顽抗,又把这座孤城苦守了两个月,直至弹尽粮绝。
最后一次回家看她,她的精神已不够把眼皮撑足。眯缝眼看我,仍笑,喊我乳名,声音又虚又小,像一片揉烂的纸条。阳光照着她,能透过去。
我拉起她的手,攥一攥,又放下,然后做了一次从没跟她做过的动作:握着她硬邦邦硌手的肩膀,嘴唇碰着她颧骨,轻轻一吻。那皮肤薄得像一层膜。
她眼皮下闪出一星欣慰和快活,低声说,哟。然后问,你回来待几天啊?
我说,明天就走,你等着我,我再来看你。
她半迷蒙地一笑,代替回答。
英文中有这么一种表达:Somebody is dying,某人正在死去,进行时。原来真有这么一种状态,无法再称之为活,也不是死,这便是“dying”。
倒数第二样能力,吞咽。除了每天几口水,她无力吞咽更多东西,再多就累着了。
到世上来学会的第一样本领以及丢掉的最后一样,都是:呼吸。
初夏的上午,她咽下最后一口呼吸。
02
钱财
我和姥姥,还有几种对话。
这一种是最长的:我在她身边坐着坐着,她忽然像想起顶重要的事,低声问我,嗳,你现在是上学,还是上班了?
念书的时候,我说,上学。后来毕业了,就说,上班了。
如果我回答上班,她就笑一笑,问,上班挣多少钱呀?
我说,一千块。
她非常讶异地一探身子,多少?多少?
我再说,一千块。其实当然不止这些,不过因为我知道她下面的话,所以故意把钱说少了。
果然,她拍着巴掌说,嗬,一千块,真不少,太不得了了。我们那时候,刚进厂子,干学徒工,每个月只有十六块钱。哎哟哟,一千块!挣大钱了······
感叹完了,又有点促狭地冲我笑,说,嗳,跟你打个商量,你挣大钱了,给姥姥一点吧?
我说,没问题!她便满足地将身子往后一靠,说,我说笑话呢,姥姥哪能要你的钱。
我说,为什么不能要?我这就给你拿钱。
第一次拿钱的时候,母亲把我阻止了。她并不避开姥姥,说,你给她钱,是给我找麻烦,她数不清时,稀里糊涂的又要闹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钱是她的梦魇,是全家共同的梦魇。
她是那种把一生献给别人的人,唯一快活的时代是在山东老家当闺女。她爹是渔老大(亦即“渔霸”),祖上传下花锦也似一份家业,家中养着好些艘打鱼的船,又雇有好些佃户在田里做工,呼奴使婢,甚有气象。姥姥是大小姐,出去溜达买些针线花朵,身上从不带钱,只说一句,记在账上。到节下,店铺自会到她家收账。
后来,姥姥她爹迷上了抽鸦片,几年就把家财败光了,无奈将长女下嫁家中长工的儿子。后来我姥爷北上到天津打工,在熟食坊当酱肉师傅。姥姥跟过来,在天津养育起四个儿女。
当家人工资不多,家里吃饭的嘴不少,一对三寸金莲的文盲妇女,不能出去工作,丈夫还有挥霍、赌博的毛病,后来儿女们生活不如意,赡养费都给得稀松,这辈子她在钱上一直没松快过。对于失掉钱财的恐惧,日日腌心,熬炼出一个幽灵盘踞在心里。至耄耋之年,记忆昏茫,理智再也禁锢不住那个幽灵。
母亲说,人老了,性格真会大变。以前多温柔多自尊的人,现在说变脸就变脸,六亲不认,只认她的钱。
她一生积蓄到底有多少呢?谁都不清楚。
大舅给她做了个白铁匣子,她将钱都放进去,匣子靠一把锁锁住,钥匙放在她随身的小钱包里,而钱包,有时她搁在大褂口袋里,有时又塞进裤子口袋。
这种复杂的保险系统,壮年人亦未必时时能脑筋清明。她经常趁无人时开匣子,点钱,点清楚数目才放心,但装钥匙的钱包或许随手一放,或许塞在床褥下就忘记了,或许竟一时糊涂锁进铁匣子里去。总之是,不见了!
随后,这就要开闹了。先是默坐垂泪,继而不吃不喝,继而喃喃咒骂(“狠心贼,杀千刀的,不得好死”等),继而长号大骂,直至阖家聚会,劝解安慰,但肯定是劝不动解不开,磐石无转移。一定要哭骂竟夜,震动邻里。
由于她一直跟母亲父亲和我一起住,母亲服侍她更衣,换洗被褥等事,最有作案时间和作案机会,所以当她闹起丢钱来,首当其冲的疑犯就是母亲。
从我十三四岁起,她大概隔几个月要闹上一次,哭骂的内容如“我知道你缺钱,可我的钱都是一毛一毛攒的呀,你偷你妈妈的钱包,真忍心啊,真下得去手啊。你是要你妈妈的命啊······拿出来!你把我的钱拿出来,我不计较你!不拿出来,我跟你豁命·····.”
后来,她会迷迷糊糊地在脑中编造自己的财物,找不见,就说是被偷了。她曾比划出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存折,说里面存着八百块钱,丢了。
在起初数年中,母亲也经常哭,哆嗦着手辩白自己,但姥姥毫不动心也根本不理会,就像定了格的机器,只反复呵那几句话,“偷你亲妈的钱包,真下得去手啊,你是要你妈妈的命啊。你把我的钱拿出来,我不计较你……”
在那些时候,我真恨她。她不再是那个笑眯眯慈爱的姥姥,是个冷漠无情、蛮不讲理的老婆子。
于是趁大人不在的时候,我独自跟她理论,从强作镇定的理论,至于边哭边喊。她始终阴着脸,沉浸在自己的忿恨中,末了轻蔑地瞥我一眼,说:你什么都不懂,闭嘴。
闹丢钱的剧目,一直上演了十几年。到九十多岁,她体力终究不行,闹不动了,便采取冷战的方式。比如,父亲下班,走到卧房里来问候她,她劈头冷冷的来一句:恭喜你啊。
父亲自然问恭喜什么。
恭喜你发了财啦,你媳妇给你偷回钱去了。
父亲一笑,回身走了。
其实她已经十多年没出门买过东西,钱早就失去通货的基本意义,对于儿女来说,钱是哄她开心的道具,以及尽孝的证据,对她来说,钱是供幼儿搂在怀中赖以获得安全感的娃娃,以及······生命意义所系。
这就是为什么母亲不愿我给她钱。她说,我经常给她一大叠十块,她数一数,那样倒更开心。
但某一次,我总算给了姥姥两百块钱,两张红彤彤的纸,搁在她面前床单上。
她将那钱好好看一阵,笑道,真没想到,我还能花上外孙女的钱呢。说着把钱放到床头柜上,让钱票靠墙立着,像展览一份奖状似的。
过一会儿,她喝几口茶水,就忘记了。一转头看见钞票,盯了一阵,有些疑惧,低声唤着母亲,这钱哪儿来的,怎么放我这了?是你的吗?怎么不赶紧收起来。
母亲大声说,那是你外孙女孝敬你的,给你买巧克力吃。
她重新快活起来了,哟,给我的?好好好,那我赶紧收起来吧。
母亲知道她一将钱收进她的白铁匣子,这事就算彻底被抛进深渊了,忙说,你先别收,别收!搁那看看多高兴。
她连连说,好,我不收,看着。又一拍手:嘿,真没想到,我还等到花上外孙女的钱了。当初,巴掌那么丁点小的人儿,现在都挣钱了······
当然,再过五分钟,她还会再问,这是谁的钱。
母亲就这样陪着她,一次一次回答她,逗起她一次一次高兴,和一次一次感叹。
我跟母亲说,姥姥爱忘也有好处,别家孩子孝敬长辈钱,长辈只当时惊喜一次。姥姥呢?总跟她说,她就能惊喜好多好多次。
半年前某晚,我刚好在家中。母亲给她掖了掖床边被褥,她立即疑心是搜她的钱。
开始时是和颜悦色的,喊母亲名字,三闺女,别逗我玩了,把钱还给我吧。
听闺女说“我没拿你的钱”,立即虎着脸低吼,你敢说没拿我的钱!我亲眼看见的!一千块钱,我塞在褥子下面,你一下就抄走了!说着还案件回放似的,抖着手将被褥掀一掀,模拟“一下就抄走”的动作。
怎么解释自然也不顶用。我没拿,我亲眼看见的。我刚才只是帮你整理被褥,不对,你是偷我的钱。这样的车轱辘话来回说一个多小时,她就开始哭号叫骂了。
后来我和母亲躲到另一间屋。隔两扇门,还隐隐听得见惨痛哭声。此时已经凌晨一点。
母亲反倒安慰我,没吓着你吧?她隔几个月照例要闹一次,我习惯了。
我依偎母亲坐着,心里居然涌上有些阴暗的忿忿:为什么偏偏我的母亲要受这个折磨?那些能过安逸日子的人,那些品香、饮茶,大谈境界、诗意、春雪秋叶的人,你们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你们不必耗尽时间与心力服侍、招架这样一个高寿的老娘。
但这事情该怎么了局呢?母亲悄悄跟我说,要不,你偷偷拿一千块钱放在她褥子下面,然后假说是帮她找到了。
她又说,你总看电影,应该会演吧?我被母亲逗笑了。她从抽屉拿一叠钱给我做道具。我笑道,剧组里演戏用的都是假钱,哪有用真钱演戏的,人家照单全收,假戏真做,你岂不亏本?
母亲的话让我不笑了:以前他们曾出主意,说偷偷找假币来,几万几万的,随便给老太太玩,我不同意,怎么能那样糊弄她。
为治亲人的精神疾患演演戏,比如王熙凤骗宝玉要给他娶林姑娘,倒也有前贤可效。如今对姥姥来说,钱,就是她念兹在兹、何日忘之的爱人。
我捏了捏钱,硬着头皮进屋去,她正沉浸在哭泣的余韵中,小孩子似的捧着脸,一下一下抽搭。我递毛巾给她擦脸,背过身把钱塞到被褥下,又柔声说,我来给你找找吧。她抽噎着说,你找不到的,我亲眼看到让你妈拿走了。
我用身子挡着,飞快地把钱塞到褥子下面,又给她掀开被褥,很惊喜地说,咦,你看这是不是你的钱?
她睁开通红的眼,张望了一下。我暗忖这事总算可以了结了。她看了一眼,眼里的光黯下去,一甩头,凛然道,不对,不是那个,我的钱有八千多。
我无言败退。
母亲一摊手,那真没法了,总不能现在去银行给她取钱吧。你去睡,我陪她熬着。
到两点多钟,还听得见隔壁房间的声音。
天光大亮,我一睁开眼就翻身下床,到隔壁去张望。只见她面色平静地坐在床上,母亲正给她擦脸,擦手,梳头。她又慈和地笑着唤我,来,坐我这来,咱吃早点。
她全忘了,昨晚的风波。
那是她最后一次闹丢钱。此后,她的体力与精神不再允许她这样折腾。
03
缘分
姥姥老到需要人陪伴照顾之后,就跟着母亲了。
有时提到那种轮流赡养老人的多子女家庭,母亲总说,那家人怎么舍得啊。
母亲的朋友,姓佟的一家,家主壮年谢世,所幸贤妇一鼓作气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做夫妻总共十几年,竟养下十个儿女,在这桩女人行当上,也算做出壮举。到晚年果然颇不寂寞,十个儿女平均分摊365日,老太太宛如游牧民族,逐温饱而居,由城南徙至城北,城北徙至城东。
据说十个儿女共有一恨,恨老娘当年没再生一对双胞胎,那样一户一个月,正好没得吵。游牧的日子过了几年,有几户就后悔,要退股,理由也都很惨痛,有的下岗了没工作,有的儿子要高考。
老太太不堪屈辱,自觉为儿女清除太平生活之障碍,仰药自杀。头一回救了过来,送在医院里,奈何她求死之心坚定,夜里偷偷拔掉针头,终于如愿以偿,去跟老伴团圆。
但若说不轮换,谁真能心平气和、不攀不比?
都是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娘又没格外多喂我一口奶,赡养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凭什么大哥/二姐/三妹就可以不管,偏要我受累?······就算闺女儿子心地纯孝,又难保姑爷儿媳也绝无二话。日子长了,难免气不平,不平则鸣,比如,你嫌我饭不好,那去你二儿子家吃吧。最后还是难免轮流赡养。
所以,独生子女制也许有种种弊病,但赡养老人是责无旁贷。政策要求父母们孤注一掷,儿女们必须无怨无尤。
母亲又说到“缘分”。说,我和你姥姥有缘分。
其实这缘分不是那缘分,不是非要在雨巷里逢着一个撑油纸伞的大闺女,或者谈拜占庭美术湖畔诗派谈得倾盖如故,才叫缘分。因为亲人不一定特别亲,混沌之中的游魂一点,赖母亲肚腹生发成形,又踏过母亲产道,挣扎落草,甫落地就多了一满屋子亲人,表的堂的,昆仲叔伯,想推也推不掉。投在马槽里还是投在磨坊里,自己做不得主,更不能事先专挑沉稳睿智的男子当爹,温柔醇厚的女子当娘,仁义能干的当兄弟姊妹。幼小时候,看爹娘兄妹都好,都顺眼,等长大了,自有了主意脾性,互相看着就没那么顺眼了。
只说周树人他家,母亲鲁瑞虽是乡妇,但颇能识文断字,三兄弟也个个做着大学问当着大教授。有的鼎鼎大名,有的鼎鼎中名,有的鼎鼎小名。但母亲并不了解儿子,单是硬要给大儿娶妇一举,就弄得老大和许氏朱氏一生悲剧。棠棣之间,亦颇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龃龉,终至星散各地,甚至写文章明讥暗讽,不恰之情,犹如冰炭,如此的“浓于水”,还不如旁人的“淡如水”。
就算不闹别扭,要忻合无间也难得很,虽说聊起天都很热络。彼此的至亲是同一群人,话题绝不会匮乏,但这里又要分谈得来和谈不来。
谈得来的,觉得对方句句说到心里,一件件事务怎么处置,一桩桩故事怎么评价,都互相点头激赏。亲情之外还有一股义气,对方有难,必定一力承帮,病痛之中收拾矢溺也不以为腌臜,反而觉得欣慰,觉得不如此,无以显示亲厚一一这才叫有缘分的亲人。
可惜很多彼此间真有情意的人们,不肯吐露亲爱之意。相互淡淡地说话,从外表上绝看不出有多深感情。即使亲如母女,一个亲吻也会觉得别扭。
国人羞于表达感情,惮于肢体接触。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子还曰:辞达而已矣。《世说新语·雅量》专门宣扬喜怒不形于色的文化。我小时就知道,动手动脚不是文雅闺女的模样。
某纪录片,离家出走二十年、音讯不通的儿子忽然回到家中,向老母涕泣叩头,老母木呆呆地看他,不说话,只慢慢地点头。阖家围坐,吃二十年来头一个团圆饭的时候,老母坐在儿子身边,筷子也不摸一摸,始终看着儿子吃饭。
母亲是幺女,姥姥四十岁上才生了她。她特别希望娘能跟她亲昵些,娘却总不许她偎上来亲昵,在她有记忆之后就再没抱过她。幼儿都留恋母亲的乳房,她说记得一回发烧,夜里病得厉害,姥姥才安慰似的撩起衣襟,允许她抚摩一下乳房和乳头。对小孩子来说,那就跟登仙似的。但只摸一下,姥姥就拍开她手说,好了好了。
姥姥跟大姨二姨都没“缘分”。大姨来探,茶水两杯,母女对坐,姥姥淡着脸,不怎么动,也不怎么说话,连便溺都不要大姨帮她弄。二姨三四年不来一次,连姥姥去世都只是打个电话了事。
四个子女中,她最疼大舅。为什么呢?她二十岁“于归”,头生子一落草,姥爷就北上做买卖。从此数年,只每年寄回些零星小钱。婆家本不甚殷实,养孙子还勉强,对吃白食的媳妇难免摔锅打碗。
大舅五岁时,姥姥携他到天津寻夫。有过这一段同甘共苦的年月,当娘的对子额外亲爱器重一些。不过她心里也知道,娘对儿子的情思多半是单相思。最靠得住的还是温和的三闺女。
母亲说,她临死前几个月,说了很多一辈子没说过的知心话儿。
死前一夜,她最后一次要起来坐坐,脊梁骨硌得疼,母亲就抱着她,让她倚坐在自己身上。
她坐了一阵,说,你别让我靠着你了。
母亲说,这样你舒服一点。
她轻声说,我舒服了,可你就累啦。
这是她最后一句话。
本文节选自《粉墨》作者: 张天翼;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品方:新经典文化;出版年: 2018-4
来源:凤凰网读书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