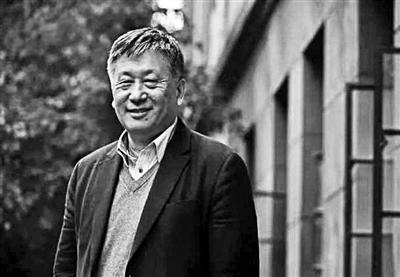主题:我和我的同时代人
时间:7月7日19:00-20:30
地点:百度直播
嘉宾:西 川 诗人,翻译家杨 照作家,文学评论家
孙甘露 作家
苏 童 作家
张亚东 音乐人,跨界艺术家
主持:梁文道 理想国首席顾问
梁文道
照苏东坡那个方式写作文,在今天通不过
梁文道:我们今天这样一场论坛是由于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而来,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青年文学。
今天是高考考语文的日子,我有一个感觉,大部分人这辈子跟文学创作最有那么一点点哪怕是间接关系的,恐怕就是作文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透过学校里面的作文学习,从此爱上写作,踏上写作之路。但是有些人考完作文就算了,比如高考作文都考过了,“以后这辈子都不要再写作文了,天啊烦透了”。
我见过一些小孩练钢琴,我以前在香港常常见到这种场景,我真的亲耳听过有母亲逼着儿子去考钢琴试,“你好好学,你考到八级之后,你这辈子都不用再弹钢琴了”。你都不知道他学来干什么。
所以我想先请问几位,你们自己过去的作文经验是怎么样的?你觉得作文跟你的文学创作有关系吗?先从离我们最接近的西川老师开始,您还记得您高考作文写了什么吗?
西川:完全不记得了。我以前写作文,老师会拿出来当范文,我自己就觉得很得意。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要写的不光是作文,我小的时候写过儿歌,而且在全校的大会上朗诵过。我自己就觉得,我每学期必须写一首儿歌,在全校的大会上朗诵。
梁文道:这是当年的志愿。写着写着就成了诗人。
西川:也不是,成诗人是有另外的原因了。
梁文道:孙甘露老师,你在上海,你还记得你高考作文写了什么吗?
孙甘露:我没有参加高考,所以没有高考作文。
梁文道:那你小时候做作文吧?
孙甘露:做作文。我记得以前在课堂上,好像老师也是把它拿出来作为范文来读。但是有一个情况,做课堂分析的时候,我的分析通常在老师看来是错误的,通常人们说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我归纳提炼出来的好像跟标准答案不一样,这是令人非常沮丧的。
梁文道:所以今天考试的同学们,你们可以放心了。就连孙甘露老师过去都把握不住中心思想、段落大意,表示你没有跟规矩做好,错误了,你后来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西川:我有一次写了一个作文,我是学的苏东坡。苏东坡有一篇小文章就一句话,我也自己逞能写了一篇作文,就一句话。老师把我臭批一顿,给我特别低的分。但是我自己拿着苏东坡的《承天寺夜游》,我说你看苏东坡都可以这么写,我怎么不能这么写?结果老师没话说了。所以我找了一个大靠山,找到苏东坡。但是如果照苏东坡那个方式写作文,在今天通不过。
孙甘露
四十年后才把作文题审清楚
梁文道:苏童,你以前中学作文跟你的创作有任何的关系吗?
苏童:高考作文,西川忘了,我还真没忘。我参加高考是1980年,那年高考作文题目我还记得很清楚,今天说起来叫材料作文——给一段材料,关于达·芬奇年轻时候画素描老是画一只蛋,让你发挥写一篇作文。我跟甘露、西川一样,我认为我的作文是强项,会得很高的分。但是事实上,我的语文才拿了70多分(那时候是100分制)。虽然后来我靠数学、地理拿高分,还是考上了北师大。但这一直是一个谜,因为语文那些综合知识我有把握,肯定答得没什么大问题,不会扣那么多分。20多分扣在哪儿了?很明显是作文。
今天谈高考作文,四十年前这个血案我梳理清楚了——我审题审错了!我今天可以根据这篇材料得出两个出题人希望你走的方向,一个是勤学苦练,另一个方向,一切都要从基础做起,这个我提都没提。我相信我的分是丢在这个方面了。四十年以后,我审题审清楚了,可惜这篇高考作文已经远去了。
梁文道:亚东,你是一个音乐创作人,你以前念书的时候,对作文这件事情有感觉吗?
张亚东:我上学的时候,每到课间很多同学都会把我围起来听我讲故事。他们知道我在编,但是听得都非常当真。我想也许小的时候有编故事的能力,只是因为选择音乐,没有那么多尝试。但是或多或少跟文字的关系一直是有的,比如我要写一封信和朋友交流,或者是阅读,这就是一种习惯。我觉得是以另外一种非专业的方式一直参与文字。如果你可以在文字或是音乐里找到那个感觉,大概你就再也不会丢掉。不一定成为职业,对我来说你永远都会跟它发生一个关系。
梁文道:我常常听到有一种讲法说音乐也是在讲故事,你觉得你后来的音乐创作跟你当年编故事,虽然完全两种不同的媒介,中间是不是还有某些层面上有关联?
张亚东:音乐更抽象一点点,好像它没有那么明确,在我看来更容易。因为文字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觉得它太过准确了,非常难以把握。当然,有好多文字我完全可以理解,并且受到文字的冲击,但是想要去做的时候觉得还是退回到音乐里,因为音乐相对来说会模糊一些。我们变成从文字里获得很多灵感,尝试用自己的音乐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张亚东
写八股作文得到高分会被嘲笑
梁文道:我想跟杨照聊一聊,我们都在台湾念书,我们中学的时候除了作文,平常还有一个场合也考验到你用文字的写作,那就是周记。写那个周记是很无聊的,因为周记里面已经分好了大概的格式,比如说本周国际大事、本周社会大事,本周校园记事、本周我的生活。我记得在本周大事写的都是笑话,我自己瞎编的。老师看了哈哈大笑很高兴,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给我改分。所以每次给我改的那个分数都是在及格线左右。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周记还要改分吗?简直是荒谬。我想问杨照,你中学的作文跟你的文学写作有任何关联吗?
杨照:周记很无聊,第一是比较容易抄,因为就是国际大事、国内大事,为了让学生方便写周记,几乎每家报纸都有这个小栏目。接下来还有生活感言之类的,还要用小楷毛笔写。
我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读现代诗,我就抄诗。我那时候开始抄余光中的诗。我也不写说这是余光中的诗,我就抄,抄完之后交给老师。发现老师没有反对,老师还给我成绩,而且“很厉害”、“不错”,我就继续抄。
我印象非常深刻,余光中的一首长诗叫做《火浴》,我可以抄好几个礼拜。抄到有一天,我突然想说我不要抄了,我自己写一首诗好了。我就自己写了一首诗交出去。但是糗的地方是,那天我们老师上完课突然走过来叫了我说,这个礼拜周记上的那首诗是你自己写的吗?我吓了一跳,点点头。之后就开始了我的文学生涯——因为我的导师把我那首诗抄下来,拿去当时的学生杂志《本市青年》上面投稿,那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其实不是为了要发表,可是从一个角度来看也是表示说,那个小孩子的心情,我以为老师看不出来抄的诗跟我自己写的诗的分别。可他一看就看得出来这个写得蛮烂的,应该是自己写的。
后面讲到高中时候写作文,我在高中的时候开始进入校刊社,后来又当了主编。但是我们一群人每次写作文的时候就会设定非常清楚的目标,如果你在作文课得到很高的分数,我们就会嘲笑他。因为作文就是让我们写八股文,那时候作文评语,说一定要有结构,一定要有中心思想,那都是套装的。你如果套装套得很好才能得到很高的分数。
那时候我们喜欢文学,喜欢读诗,所以就很看不起这种东西。可是如果你拿到很低的分数也不会得到敬重,你就有一种特别追求的目标,我们希望写完作文之后,发回来的时候上面是老师用红字写的“到办公室来找我”。老师不知道怎么打分数,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挑战老师。
可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因为今天讲到高考作文,还是有点帮助的。我大概是用这种负面的方式在学习什么叫做中心思想,什么叫做核心的结构。等到我去考高考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收掉所有这些当时挑战他的东西,乖乖地写一篇文章。
但是的的确确我当时的心情是文道刚刚所说的,我希望写完这个再也不需要写这种作文了。
杨照
文字可以变成一个魔术
梁文道:西川老师您年轻时候的创作,是到了什么时候让你觉得我是一个诗人了,我把自己真的当成是一个创作者?因为很多人,比如写诗,每个年轻人,每个少年,或多或少都写过一点诗,或者至少有过写诗的冲动。
西川:我中学就开始写点诗,写古体诗。到大学我一开始也不想当个诗人,我自己的梦想是当个画家。学校搞朗诵会,我有机会登台,结果读完以后掌声雷动,我一辈子都没听过这么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所以我就有点下不来了。你的兴趣、你的兴奋点就移到这边来了。
而且年轻人干事,是一帮人一帮人的。你写的时候边上一定也有人在写,那些人还表扬你,有时候挤对你。但是气氛特别好,热闹,你又出风头,你就觉得身上充满了创造力。
梁文道: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其实有时候这是一个群体关系。一个人如果没有碰上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身边没有志同道合或者一个圈里的人一起砥砺做一些事,其实很困难。这也跟我们做这个文学奖有一点关联。
甘露,你年轻的时候开始写作,写到什么时候开始认为我是一个做文学创作的人,我是一个作家?以前你有过这种自觉吗?
孙甘露:这个是青少年时期了,写作首先是从阅读来的,你读了很多书,受这些作品的影响,渐渐的有一种想要表达的愿望。实际上,我好像直到今天都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职业的写作者。写作这个事情跟你的感情、跟你的感受这些东西维系在一起,我很难把它看成是上班。反过来讲,可能在青少年时期你的创作还是很初级的,或者说很不成熟的时期,你的心里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当然我也写过一点诗,觉得自己是一个诗人。这个感受并不是以你写作的成熟度、完成度来衡量的,而是你心里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来衡量的。
梁文道:苏童,我们能够看到你很早就开始出版作品,你是不是在正式出版之前就已经觉得自己投入写作,只是写的东西没有发表?
苏童:当然有。我估计很少有人真的特别幸运,刚刚开始写作一下就能成功,我的案例都是大多数人的案例。青少年时期,认识到文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好像它是可以变魔术——因为文字的组合,因为造句的功能,让文字可以变成诗、变成散文、变成小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初中时期的一个班主任有一天写了一首散文诗。散文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特别新鲜,特别刺激。我就坐在黑板面前研究他的诗,首先我认定诗写得很臭,什么课堂桌椅明亮之类的,但是这个变魔术的光彩我看到了,文字可以变成一个魔术。
苏童
数学老师都写小说的奇特环境
梁文道:杨照,你也是很年轻就开始创作,你怎么回头看你年轻写的东西?你觉得对你后来的创作或者后来的人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杨照:当然。刚刚西川老师讲的我很有同感,年轻时候写作文,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是同伴,另外一个是成就感。因为有这样的同伴,所以我到了高中的时候开始编校刊。我们这群朋友当中,彼此有各种不同的讯息,彼此互相帮助,慢慢形成了一个标准。那时候我们虽然功课很烂,在学校一天到晚不断翘课,可是自己觉得好像高人一等。所谓高人一等是说,我们编校刊,可是我们要证明我们的文章不是只能登在校刊上。
我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写诗,那时候会有一个自信心。那三年当中大概写了将近两百首诗,花费很大的是邮票钱,寄给各式各样的诗刊。发现绝大部分的诗,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十五六岁孩子写的,大部分都被刊出来了。这时候就会感觉到,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被证明,我是能够写诗的人。
当然后面印象最深刻的,是到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写小说。为什么写小说?因为写诗很难负担,因为要付邮费,但是没有稿费。可是写小说,尤其是可以在报纸上登小说的话就有稿费。我的第一篇小说刊登在当时蔡文甫编的《中华日报》副刊上,而且是我爸爸特别帮我领稿费,我到现在永远不会忘掉,因为太有成就感了。我当时领了2400块钱台币的稿费。
文道可能还记得,那时候在台湾我们最大的开销就是买书,一本书不过四十块钱、五十块钱,我可以拿2400块钱的稿费,当然很有成就感。而且你认为你自己通过了那个门槛,没有人因为你十六七岁说你这是学生习作。你觉得我跟大人平起平坐,这对于我这样成长期的小孩非常重要,因为我很讨厌大人们来支使我干什么干什么。我好像突然之间证明说,在写小说和写诗这件事情上,我比我的老师厉害。不过我们当时的环境真的非常奇特,写小说或者文学创作好像是一件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连数学老师都写小说。
我刚开始的时候写诗,本来是有一点信心的。后来为什么改成以小说为主?一个比较早的原因,是到了高一认识班上的一个同学。我必须承认这是我这个人的一点点好处,就是我还是有一个最基本的相对客观的对文学的理解跟评断的标准。我遇到这个同学是我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清楚知道他写得比我好太多了,我觉得我写诗一点前途都没有。我继续写诗有意义吗?连在自己的班上都不是最好的,那你写什么呢。所以我后来相当程度上比较多的力气放在小说上。当时台湾的那个气氛,对于我在成长过程当中跟文学的接近是很重要的。
小说比较多需要一点时间
梁文道:西川老师,我想跟您请教,您有没有在意过有人常说这么一句话——诗是属于年轻人的。尤其诗人越年轻,写的诗越好。就好像数学家,很多人说数学家要有成就都是很年轻就有成就出来。我们看历史上一些大诗人,像兰波,他所有的诗都是在二十来岁之前已经全写完了。
西川:兰波的诗是16岁到19岁。19岁以后就不写了,去非洲撒哈拉沙漠里面去贩卖军火了。人家觉得写诗是一件非常不体面的事。但是杜甫的最高成就都是50多岁的时候。庞德写《诗章》大概也是47岁以后。所以年轻人写年轻人的东西,中年人写中年人的东西,老年人可能也有老年人的活法吧,我觉得这个不一样。
为什么说诗是年轻人的事?在中国尤其有这个说法,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五四”运动的尾浪里面。“五四”运动是年轻人搞的,所以“五四”运动形成了这么一个说法,诗是年轻人的。你要是在国外参加朗诵会,年轻听众大概三分之一,很多是中年人,也有老年人。
梁文道:我们先甩开这种特殊国情不讲。您有没有读过一些作家年轻时候的创作,印象特别深的?
西川:叶芝。叶芝的诗比较唯美,我们一般知道他的“当你老了,炉火旁打盹”,写茅德冈的,这是他相对年轻时候的作品。《驶向拜占庭》都是后来的东西。年轻人写年轻人的东西,他的经验、他的趣味、他的见识、他的激情。
西川
杨照:我是认为诗,尤其现代诗,年轻人可以写得好,但是不见得只有年轻人可以写好。相对于小说,诗可以靠直觉,你甚至不必要有很多的文法,你可以靠非常丰沛的感情跟直觉写出很好的诗。在台湾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像痖弦,32岁之前把所有的诗写完了。郑愁予最好的诗基本都是二十几岁写的。台湾的很多诗人年轻时候爆发式地把诗写完了,也写出很好的诗。
可是我真的觉得,相对于诗歌,小说比较需要多一点点时间,包括在技巧上面。你没有那个功夫,年轻的时候还是可以写出好的诗来。可是小说不是这么回事,小说里面很多东西,包括从叙事的声音,包括到结构,包括到思想,包括小说前后的关系等等,有很多需要通过时间进行练习,不太可能单纯只是天才,天才也许可以写到一篇、两篇好的小说,像苏童那么早开始写小说。一路写下来你会知道小说需要很多的历练跟琢磨,这是我觉得这两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也喜欢被束缚,不想要那个简单的热情
梁文道:亚东,你作为一个音乐人,你怎么回头看最早,你很年轻时候的音乐创作跟实践?你觉得那些创作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张亚东:在我小的时候,上世纪七十年代,获得知识的途径非常少。小的时候,比如我看一本书,或者我听一个音乐,我只是渴望成为那个人,成为他的文字、成为他的音乐。所谓创作的冲动就是,我大概想要变成那样,并没有想过结果是什么,只是自己会有想要去到那个地方或者更接近那个地方的那种感觉。
现在回过头看小时候的东西,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意义,就是觉得敢做。我们后来来北京,这些年,我终于打开了眼界,可以了解整个艺术世界带来的冲击,反而是胆小不敢下手。很多时候我觉得,知道越多给自己的束缚也越来越多,所以变成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发自内心的、特别单纯的。
其实很难讲好或者不好,我更喜欢现在,哪怕是受束缚,我也喜欢被束缚,我不想要那个简单的热情。可是有的时候回看,只是觉得年轻时候真有劲,特别有那个冲动,现在觉得收敛很多。
梁文道:你有没有关注到年轻一代的写作?
张亚东:我们没有想到有一天想到作曲家、想到贝多芬,不再只是紧锁眉头拿一只鹅毛笔的那个形象了。现在已经是不需要有笔也可以写作,年轻人有更多手段。还有多数人,在我看到的不管是文字的作家也好音乐的作家也好,可能到一定年纪都皈依到某种风格流派里。
在当下来说,可能需要更多技术手段来帮助你做很多东西,音乐是这样的。就音乐来说,我觉得传统的东西是没有任何可能超越的,所以只能想其他的办法,在那个基础上有效地用现在科技的、技术的手段,去怎么让那个东西为你所用,同时又能保留你自己身上非常单纯、非常简单的那个情感世界。我觉得年轻就是单纯,就是敏感,他有最好的礼物,就是激情。可是过后,那个东西会变得非常理性,而且难以逾越。
整理/雨驿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