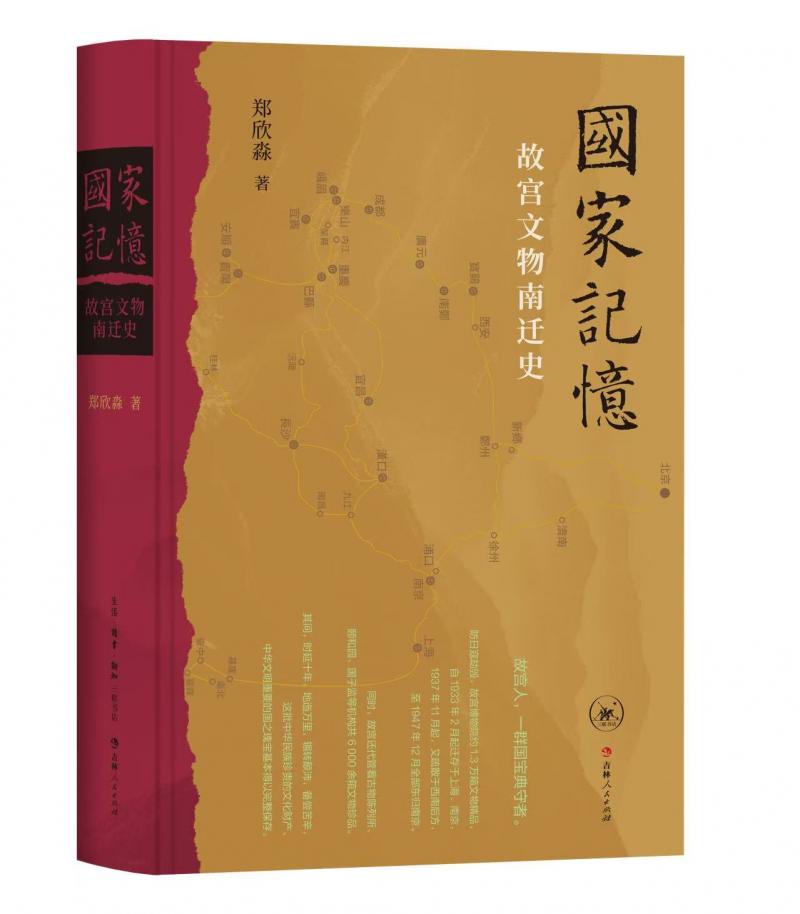近日,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故宫学”首倡人郑欣淼历时四年撰写的新著《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
本书依托大量首次披露的档案、日记、书信与影像,以六个篇章、四十二万余字的篇幅巨细靡遗地重现了1933年至1947年间故宫文物南迁这场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的文化大迁徙。作者还以史家的严谨、文学的温度,刻画了易培基、马衡、那志良、庄严等一代故宫人如何在国运衰微之际,以“人在文物在”的典守精神,完成一场静默而壮烈的护宝行动和文化抗战。
烽火中的“文化长征”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年份,一部厚重而深情的著作《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再次将我们带回那段风雨如晦、山河破碎的岁月,讲述了鲜为人知却又惊天动地的文化保卫战——故宫文物南迁。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搬迁,而是一次跨越十年、行程万里、涉及上万箱国宝的“文化长征”。从1933年2月起,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珍贵文物自北平启运,先后迁往上海、南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又紧急疏散至四川、贵州、湖南等地,辗转于西南崇山峻岭之间;直至1947年才东归南京。
这段历史曾长期被遮蔽在抗战宏大的战争叙事之外,公众对其知之甚少。然而,《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以详实的档案资料、珍贵的图片、清晰的时间脉络和生动的人物刻画,为我们揭开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书中不仅记录了文物如何装箱、运输、保管,更展现了在民族危亡之际,一群知识分子与普通职员如何以血肉之躯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作者指出:“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保护中华文脉的一场壮举。”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人用生命践行的誓言。当时,每一口木箱都承载着千年文化的重量,每一次转移都冒着遭遇炮火与翻车的风险。在长沙凿洞藏宝,在峨眉山寺庙中避难,在重庆雾都里点查清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令人动容。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迁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华民族集体抗战精神的缩影。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
血肉之躯铸就的“典守精神”
《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最打动人心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部宏观史书,更是一部充满人性温度的“微观史诗”。它通过一个个具体人物、一封封来函密呈、一次次激烈争论,还原了故宫文物南迁中的真实历史图景。
书中详细记载了南迁决策前的激烈争论。当时社会上有强烈反对的声音,认为“故宫不可一日无物”,担心一旦文物南迁,北平将失去文化中心地位,甚至有人指责此举是“逃跑主义”。但也有像多奇云这样来自石家庄的普通市民,致信故宫博物院与古物保管委员会,疾呼:“中华文化之精品,更为世界之奇珍……纵不能一举迁避,亦宜先后施行!”这封信虽出自平民之手,却道出了深沉的家国情怀。
正是在这种舆论压力与现实危机交织下,故宫理事会最终做出艰难决定:择精装箱,秘密南迁。时任院长易培基、后来主持工作的马衡等人,顶住重重阻力,组织专家精选文物,制定严密包装流程,确保每一件器物都能安全抵达目的地。书中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为了防潮抗震,工作人员用棉花、稻草、纸屑层层包裹文物,再放入特制木箱,仅包装一项就耗时数月。而运输过程中,押运人员不仅要面对日军空袭、道路塌方,还要应对盗贼觊觎。
更令人动容的是,许多故宫员工举家随行,妻子儿女跟随车队跋涉千里,住在简陋客栈或乡间庙宇。“家随国宝”,成为那个年代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他们在战火中坚持点收、审查、展览,哪怕条件艰苦,仍不忘向世人展示中华文化的辉煌。例如,1935年赴英国伦敦伯灵顿厅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了近800件故宫珍品,轰动欧洲。这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对外文化交流,极大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而支撑这一切的,是背后无数无名英雄的默默付出。
《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让我们看到,守护文明的,不只是高官显贵,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他们是学者、警卫、司机、文书、家属……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共同铸就了“典守精神”——那种把国宝看得比生命还重的责任感。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值得传承。当我们在博物馆惊叹于《清明上河图》的细腻笔触,或凝视着乾隆御笔的题跋时,请不要忘记:这些瑰宝之所以能完好留存,是因为曾经有一群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做出了拿命来守护国宝的无私抉择。
值得提及的是,本书制作精良,装帧设计考究。语言平实而富有温度,既有大历史的叙述,又有丰富的历史细节,呈现了故宫文物南迁在烽火十余年中、守护文物的故宫人群像。书中配有300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献档案等,其中有许多为首次面世。这些图片资料增强了可读性与历史的现场感,起到了更好的延伸阅读之效。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 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