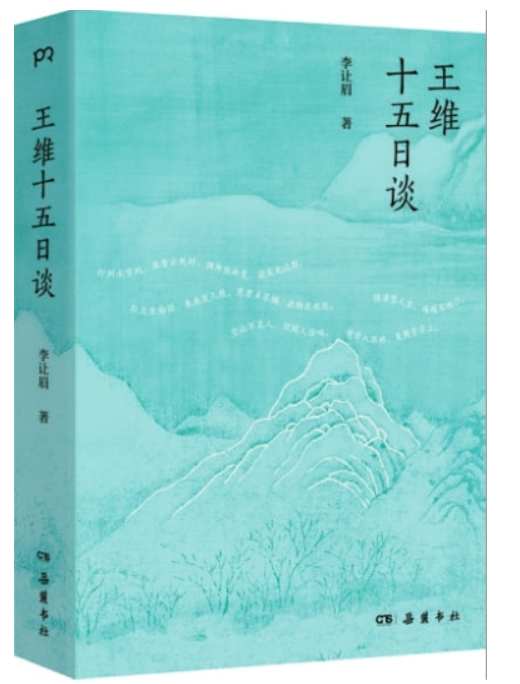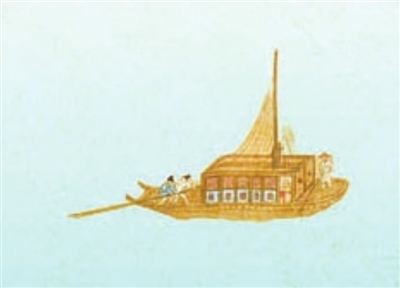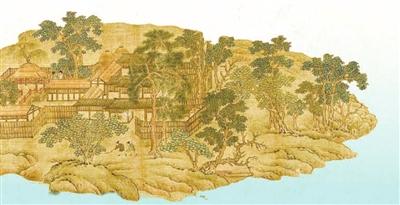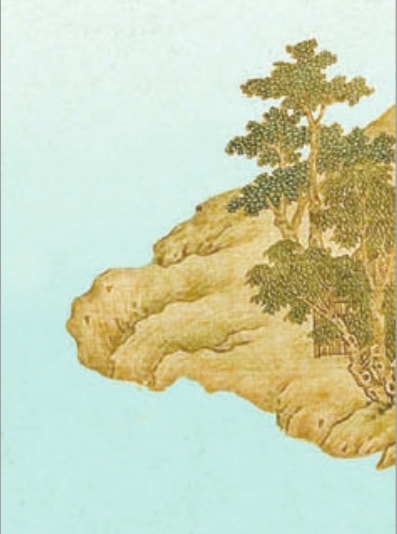“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是李让眉的微信签名,她想以王维的这句诗表达自己的心境。“虽然‘我心’与‘清川’间没有必然的关联,但是二者的状态又无意形成了一组平和的呼应。我觉得我们需要像王维一样,和天地建立起这样的关系。”
李让眉是青年诗人、作家、诗词研究者,著有《所思不远:清代诗词家生平品述》《李商隐十五日谈》《香尘灭:宋词与宋人》。据李让眉介绍,“十五日谈”系列的写作初衷是以诗人的身份去面对另一位诗人,用平视的视角与一位投契的古人展开一场深入而有诗性的交流。近日,她的新作《王维十五日谈》出版,李让眉细述了王维的生平、时代、亲交、情感、宗教、绘画、音乐、诗艺,还原王维的人生境遇与精神世界,破除既有标签。秋末,李让眉在北京图书大厦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除了沉浸在王维的诗歌世界之中,李让眉也畅谈了自己创作古诗词的心路历程。
自六岁尝试写诗 创作指引着我去赏析和研究古诗词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同大多数孩子的开蒙方式一样,儿时的李让眉在母亲的陪伴下背诵古诗词,完成了对诗的第一次邂逅。
至六岁时,源于心中一次偶然的冲动,李让眉依样画葫芦地写出了一首童谣般的七绝诗,被父母贴上了“会写诗”的标签。“孩子们都不缺创作冲动,他们见到很多事物时都会想去表达,并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去讲述自己,而我恰好选择了古诗——一种和日常生活有些距离的表达方式。”李让眉解释道。在父母的鼓励下,她一直用诗书写生活。至十岁,李让眉跟随家人前往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家中拜访,这位老师对她的诗进行了评点,并给她讲了些诗词的格律要求,此后,李让眉认为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便慢慢有些像诗了”。
不过,一直与诗打交道的李让眉,大学却选择了理科,这一选择只因与同学的一次赌气。当时,高中要分文理班的时候,李让眉的同学都认为她一定会选择文科,“她文科强,如果学理科肯定不行”。李让眉一听便生了气,“谁说我学不了理科”,于是报名了理科班,经过努力,也渐渐能名列前茅。到高考填报志愿时,才发觉理科生无法报考文学专业,于是她就读了金融专业。
在大学期间,李让眉没有放弃过文学,在学校创立了诗社,还跨院担任了人文学院的院刊主编。2007年,在大学接触网络之后,她看到有一大批网友仍在用古诗词的形式表达内心,忆起当时网络诗歌的创作,李让眉称自己赶上了当代最后一次文言诗歌的盛会。“在现当代文学史中,它通常被称为‘网络诗坛黄金十年’(注:2000年至2010年前后)。我开始进行一些诗学思考,比如我究竟是什么样的诗人?我能写出什么类型的诗?虽然当时没有找到答案,但这是个可贵的过程。”
直至今日,李让眉认为自己能够坚持研究诗词,与持续不断的创作有着紧密关联。“什么样的表达是好的”“哪一次的表达与自己的感受最为匹配”“怎样才能写得更好”……这些问题在创作的过程中生发出来,让李让眉产生探索的向往。她开始从古人的诗词中寻找答案,并尝试进入“赏析”或“批评”的领域,站在创作者的立场去思考一首诗词为什么好,如何“从自己的诗走向别人的诗”。
在这一过程中,李让眉也慢慢对古代诗人祛魅,她解释道:“带着这样的视角去读诗词,有时会觉得有些诗我也可以写出来。诗人有自己的创作惯性,文学手感相近的诗人,会在某些瞬间感应到对方。所以有时看到一些诗人写出的上一句,捂上后文我也大概能猜出他下一句的方向。当然,也有每次都猜不中的,比如李贺这种天才。但总而言之,创作的思维会为诗学批评与相关研究带来新的方向,二者交叠,一步步拉着我往更深的领域探索。”
李让眉的创作是随时随地的,有时看到一些生活中的画面,想到一些字句,就会写下来。比如她创作的《蝶恋花·通勤口占》就记录了当代人地铁通勤的画面。“白月空天潜自驻,衢底终风,地铁过无数。诸我错肩门一阻,晨昏心气春冬絮。漂泊浮身尘里语,幻码方生,打闸人潮去。遮面已迷回望处,上楼去会苍生苦。”诗人胡桑评价道:“当代打工人的通勤体验在‘词’这一古典体式中被裁剪、形塑、安放,同时‘词’的形式潜能也得以激活。比如‘地铁’‘幻码’‘打闸’诸多语汇的嵌入,分明是在邀约当代人的生活进入古典的书写形式。”
以诗识人 与我金融分析的工作有相似性
2017年,初为人母的李让眉感受到时间的紧迫,常觉焦虑,“和同道交流的时间少了,很多想法来不及留下来”。
工作的忙碌与母职的辛苦,促使李让眉尝试将自己的思考落实在写作中。她认为单纯的无功利化写作给自己带来了很多新的灵感,同时,写作本身也可以有“自我”的存在感。写诗,李让眉利用的是生活中的碎片时间,而研究性质的大部头文章,李让眉则会在黑夜里书写,孩子们入睡后,才是独属于她的时间。对她而言,写作是更恒久的快乐之源,在创作的过程中可以把一些稍纵即逝的想法落实,也会引导她更开阔、更积极地看待生活。
每研究一位诗人,李让眉都会尽可能广泛地读诗人的作品,甚至是去读全集。“当读的诗足够多,我们就会发现诗人在处理同类意象时,会有自己的文学惯性。但是,如果他某次创作脱离了这种惯性,或者忽然选择用一种不常见的手法,我便会立刻察觉到其中的异常。”这一研究技法,可见于她创作的《所思不远:清代诗词家生平品述》《李商隐十五日谈》《香尘灭:宋词与宋人》。她从诗人的创作逻辑入手,一点点找到他们不愿说出的话,并沿着这个方向,去还原诗人的面貌和精神世界。
关于她从诗中找到研究的“线头”,她进一步解释道:“还有一种诗人习惯将一组同样的意象放在一起,尽管他不一定讲明这首诗在针对哪一件事,但当我们看到熟悉的一组意象团出现,这段描写很有可能就是对同一件事的复现。因为这是记忆的逻辑,而不是单纯的创作逻辑。比如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是一种单纯的文学构建,他第二次再去表达类似的情感,就不会把这些意象组织在同一个句子;但如果是针对记忆的创作,他则会在意象上反复地扣合。我就在李商隐的很多‘无题诗’中找到了这种回响。同时,他在不同时期的创作对某种意象团都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和表达尺度,从中又可以看到他在某件事情中的情感变化的脉络,我们由此可以有更多的发现。”
不论是以诗识人,还是以诗证史,李让眉认为这一研究路径与她的日常工作有相似性。她的日常工作是金融分析,面对需要研判的公司时,也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去熟悉对方的叙事惯性,针对获取的数据和事实进行系统分析,后期逐步将分析过程形成结论,再落实到自己供职单位的投资偏好中。
“这一过程与我分析诗歌的过程是类似的。一方面要有前期充足的准备,另一方面要有后期严密的分析。同时,我要把对方自洽或不自洽的东西梳理出来。只不过,在研究诗词时,我没有办法对诗人进行访谈,只能依托他作品中留下的蛛丝马迹进行分析。”李让眉讲道。
“淡人”王维并不淡漠 他重情义也重道德
2022年,王维成为李让眉想要书写的诗人。她开始用闲暇时光阅读王维全集,王维的诗让她找到了一种安放感,甚至起到了疗愈的作用。
当李让眉更深入了解王维,去探寻他的经历时,她发觉“王维似乎深不见底”,而他的诗具有一种“叙事者淡出”的特性。在李让眉看来,王维本质上不是会为某个事件写诗的人,相较于叙事和说理,他注重的是当下的感受,有些表达也就不完全遵循语言的逻辑,“生命感受对他来说是高于语言的”。因此,在写王维时,李让眉有着完全不同的写作状态。“研究王维不能用我刚刚提到的方式去做,因为他的诗不是对事件的复盘,传导链是散碎的,所以无法用以诗证史的方法。他启发我跳出诗去看诗,在这个过程中,我获益很多。”
李让眉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一句为例,她认为“不见人”恰如现代摄影师常用的长曝光,当曝光时间拉得足够长,每个时点的光不断叠加,最终会令出现过的所有人影全部虚化消失,在无限的时间面前他们都是“空”的;但同时,王维会提醒大家仍有“人语响”,他们也都真的存在过,这是一种空与有的辩证。“这种写法的妙处并不在于诗学技巧,而来自他被佛教塑造过的世界观。这也就让我们这些试图通过技术接近他的人只好望洋兴叹了。”
在《王维十五日谈》中,李让眉在“第一日”便提出了世人对王维的误解。“读诗时,我们要始终记得,王维是个擅长自我疗愈的诗人,这意味着他本身很容易受到伤害。他的诗作,也正是在失序中追寻平衡的产物。”李让眉讲述了王维的生平,比如王维作为家中长子,年少时便要尽最大努力去谋求功名,以此撑起整个家庭,帮助弟弟们在长安立足。因此,他当时的处境不允许自己视功名如云烟,也不论自己是否愿意,王维都必须在各个方面努力学习,以便融入上流社会。在王维的诗集中,李让眉读到“独在异乡为异客”时,常感心疼,此诗下的注脚为“年十七”,而诗中的“每逢”则表明这不是王维第一次在异乡独自过节。李让眉写道:“人们常叹服于王维在上流社交圈中展现出的交际能力,也就往往不会设想一个中级官僚家庭出身的十几岁的孩子要经历怎样的努力,才能如此从容地游走周旋于长安众多名流之中。事实上,王维后来的仕途是配不起他年少时的声名的……”
对于大家常给王维贴上“淡人”“佛系”“情感淡漠”等标签,或是常提到他“半官半隐”“从未给妻子写情诗”等事,在李让眉看来,王维并不像他的诗学人格那样淡漠,相反他是一个重情义也重道德的人。“他深爱母亲与弟弟妹妹,这都有传世文本证明,而三十岁丧偶无嗣却终身不再续娶,本身已是比文本更长久的表白。王维很少为痛楚哀鸣,但他一直在忠实地用诗记录每一场失去后的自我痊愈过程。”
学习古琴和绘画 在动态中走进王维的艺术世界
王维能让李让眉“跳出诗去看诗”,不仅是因为王维在心灵层面给了李让眉诸多慰藉,而且王维用多元的艺术探索启发着她的许多思考。因此,在书写王维时,她也希望读者能感受到王维的宁静,并被他疗愈。
2024年9月,在写完“王维的艺术世界:音乐”一章之后,李让眉开始对乐律学感兴趣,尤其看到王维在中晚年时开始弹奏古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她很好奇王维后期选择的古琴与他早年擅弹琵琶到底有何区别,于是报名学习了古琴,直至今年六月在古琴初级班毕业。
本来就会弹琵琶的李让眉在学习古琴之后,发现了两种乐器截然不同的风格。琵琶的旋律主要通过高频触弦的弹音去实现,“上一个音还未彻底消散,下一个音就立刻跟上来了”,因为指法繁复,表现力强,琵琶对余音应用不多,它不愿放弃右手,如古琴那样有耐心地只靠左手去做线形表达。提及古琴的弹奏方法,李让眉用双手在桌面上演示着,她用右手弹了一个音之后便停止,左手开始在琴弦上挪移,处理着主音在消散过程中的余音,“古琴的核心美感在余音,手接触琴弦之后,直到琴弦震动彻底消亡,古琴主要的表达都保留在这一过程中。”
在学习古琴的过程中,李让眉不单对王维有了新感受,也对“词”有了不同的感知。比如读过《凤凰台上忆吹箫》的琴谱后,她开始明白李清照在《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中的“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一句中的衬字的考究。“我也写词,但之前我会认为其中的‘念’只不过是一个领字,它可以被替换成‘忆’‘恨’‘记’等动词,也并不影响后面‘武陵人远,烟锁秦楼’的句意。可是,当弹奏演唱时,我发现‘念’字与‘武陵人远’是有音韵呼应的,如果能与‘远’字用同一韵,演唱效果会好得多。尽管琴歌中不会对此有明确要求,词谱也没有强调,没有人会意识到这里的呼应关系,但是当词作回到音乐里,我们会发现原来李清照会把这样的细节都照顾得如此讲究。比如,我们如果把它改成‘恨’,就根本唱不顺。”
《王维十五日谈》的乐论部分,写于李让眉动念学琴前,这让她稍显遗憾,她坦言:“如换现在再去写,或许会有更多的生发。不过写作与写作者,本就是这样在遗憾中互相促进的。”
此外,李让眉在去年还上了关于绘画的网络课程,以没骨画为主。“没骨是工笔与写意的中间态,所谓兼工带写,如果我们想了解文人画,就要去了解它与书法的笔墨之间的关系——毕竟王维是后人认定的文人画鼻祖。”在这一课程中,令李让眉感叹的更多是颜料的质感。她为此专门查询了许多关于古人如何制作颜料的资料,也专门去博物馆实地感受了这些颜料的质地。
对古代颜料有了实际感知后,李让眉再去读王维的诗,才发现他对色彩的选择非常讲究。比如“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中的“白”,让李让眉感叹王维写得很妙,她解释道:“白通常用来点缀,蛤粉很昂贵,也很难调和。平涂时,要用大量的水去稀释珍珠白。因此,王维把这种氤氲的‘白’用在了‘江湖’,而非‘山林’,虽然日落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会失去色感,但是只有‘湿润’的事物,才配得上‘白’。试着从艺术体验看他的诗歌,才能感觉到其中的独特。”
“当我们真的站在诗的面前,会意识到此时的王维不是一位操控语言的诗人,只是一位虔诚的画师。”李让眉认为,王维许多绘景名篇的创作思维都很接近于用绘画的视角去欣赏造物主的作品,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她以绘画的视角赏析说:“当王维看到大漠上这一道孤烟时,他意识到‘直’对这个画面是多么重要——稍偏一点,美学平衡会立刻打破;此外,若画过雪月风竹,我们也会明白用留白托出的月亮若不够‘圆’,会对整幅画面产生怎样的冲击。”
李让眉介绍,目前针对王维的研究,限于学科的理念而就诗论诗。比如诗归于古典文学,音乐归于乐律学,绘画归于美术史……“每个领域都有高手,但大部分研究成果没能被聚拢、回归到一个人身上。《王维十五日谈》试图在这个方向多走一步——看看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是怎样通过调和不同门类艺术来确认自我的。”
供图/浦睿文化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韩世容
编辑/ 李涛